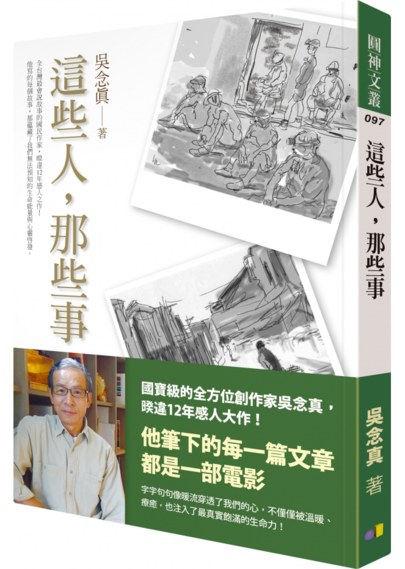記得有個古老的傳言是這樣說的,說早年有人綁架了小孩,如果無法確定肉票行情的話,通常在勒贖之前會先蒸一條魚給孩子配飯當試探。
孩子先動筷子的部位要是魚肉比較厚實的魚背,那綁匪大概就要虧了,因為這孩子要不出身貧寒,最多也不過是平常人家的子弟。
如果那小孩最先挾的是魚肚,甚或只挑魚頭頰部那一丁點嫩肉的話,綁匪可就樂了,因為這孩子肯定來自有錢人家!
有個朋友甚至還曾經說過一個更誇張的故事,說他祖輩的族人家道中落之前,只要桃子的產季一到,傭人就得先做好一些蔴糬備用,然而這些蔴糬可不是拿來吃的,而是孩子們要吃桃子之前用來沾掉桃子上的細毛,以免傷腸胃的「工具」而已!
這些傳說和故事的結論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富過三代,方知衣食。或許身邊「富過三代」的朋友不多,因此談到難忘的「美食」無非就是故鄉小吃或家常飯菜,因此每回說到最後,對鄉情、鄉愁、親人、舊友的緬懷和思念,好像比食物本身的氣味和滋味都來得濃烈、來得多。記得多年前也是這樣的冬天,陰雨連綿,和朋友們說起九份山區老家的印象,說那裡的冬季經常白霧瀰漫,有時甚至五尺之外的景物就無法分辨。說霧裡經常有遠處送葬的嗩吶聲隱約的哀傷。
說屋裡的溼氣,石頭牆壁泛著水光,泥巴地面黏到連木屐都穿不住,說寒假的雨天孩子們無處可去,十坪不到的屋子塞滿七、八個從兩歲到十二歲幾乎無法控管的幼獸,每當媽媽和姑媽都瀕臨崩潰邊緣的時候,經常會冒出一句話:「我們晚上煎『蕃薯粿』!」
然後這群小孩就會一哄而散,開心地各司其職,選蕃薯的選蕃薯,削蕃薯的削蕃薯,大一點的孩子則穿起雨衣跑出去砍筆筒樹,於是屋裡至少就會有兩小時以上的安寧⋯⋯
「幹嘛砍筆筒樹?」
「做磨板把蕃薯磨成泥啊!」
「磨板跟筆筒樹有什麼關係?」
「筆筒樹的葉梗有堅硬、密集的刺啊!」
⋯⋯
最後發現,我甚至必須動用圖解的方式,讓他們搞懂「筆筒樹磨板」製作過程的時間往往比蕃薯粿如何煎煮還要來得長,而且朋友們對當時礦村生活的情景以及孩子們後來一個個的去處和發展的好奇和興致,好像也比蕃薯粿本身熱切得多。然後許多人似乎也感觸良多地紛紛說起自己難忘的食物、過往的生活,以及遺忘已久的親人、舊友。
「為什麼不寫下來呢?」他們說:「至少可以提醒我們也有自己的時光和生活啊!儘管和你的不同。」
這句話似乎就是寫下這些文字的最大動力。
因為始終相信這世間每個人的人生必然都是一本書,都是累積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因為最平凡的永遠最真實。
三餐飯菜尋常過,但特別記得的必然伴隨著難忘的人物、難得的時光、難捨的情誼或情義,如果沒有這些,即便是米其林星級的「美食」,對許多人來說可能也都只是一場應酬、交際,或者裝神弄鬼、虛無矯飾的印象而已。
而這本集子寫的就是這些:平凡的飯菜、特別的際遇。
謝謝《今周刊》給我的專欄,若非有時間限制和壓力,這些記憶大概永遠無法變成文字。
謝謝圓神出版社的賴真真小姐和編輯們,是你們不斷的鼓勵讓我在專欄結束的三年之後,才敢讓這些文字和大家見面。
而最要感謝的是文字裡被我提及的所有人,每一個你對我來說,都是可以重複閱讀、重複回味的一本書,是你們豐富了我貧乏的人生。感激。鞠躬。
--本文為《念念時光真味》作者吳念真自序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