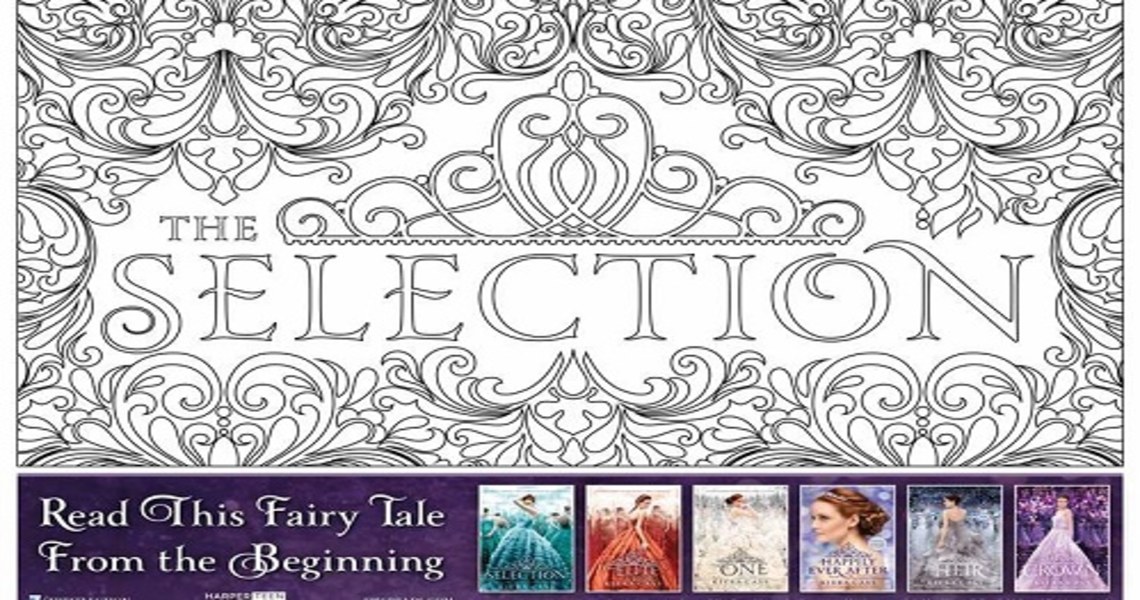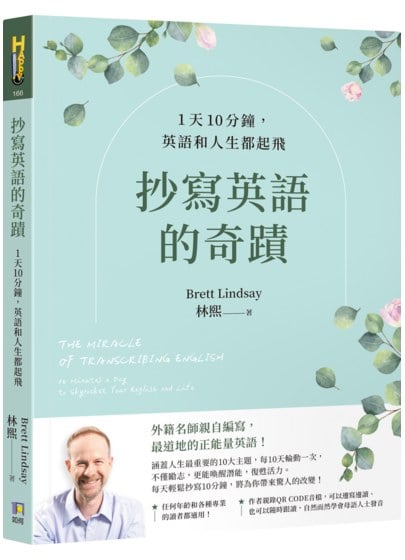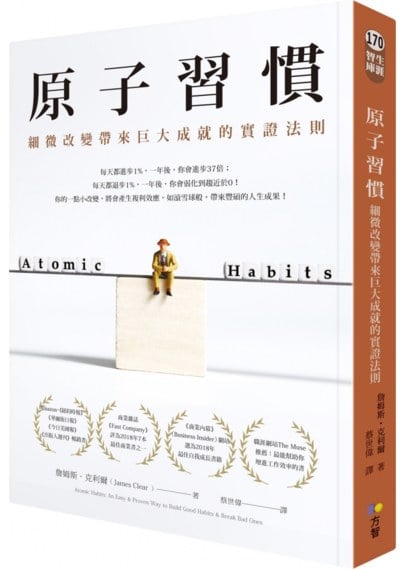1
沒人能在柵欄外存活下來,至少小時候父親是這麼說的。但我已經不再是個小女孩,也不相信父親所說的話了。他跟我說過,領導一家人殘酷又該死,還說我別無選擇,只能殺死所愛之人。許多事情他都說錯了,所以他認為我無法活下來,鐵定也是誤判。
若想活命,我必須遠離柵欄,往河邊前進。可是實際動身後,我的手指依然不斷握緊鐵網又放開,彷彿在找尋那份心安的熟悉感覺。回想起來昨晚真是幸運,畢竟我受了傷又昏倒在柵欄外,隨時可能遭遇不測。或許會有動物或其他人接近我。接下來不能再仰賴運氣了。我必須在太陽下山前過河,飲水解渴,找個遮蔽處度過這一晚。
河不遠,但路程感覺有好幾個小時。我呼吸急促,身體痛到不時停下來休息,思緒很遲緩,暈眩的感受緊緊跟在我頭頂上盤旋,等我示弱。昨晚頭部的撞擊可能導致腦震盪,但我不記得這種傷勢該如何處理。喉頭哽著一陣笑意,好不容易硬擠出聲音,聽起來卻像陷入瘋癲、喪失理智,於是我緊緊閉上雙唇。
走路很辛苦,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西洛的事也同樣辛苦。但我暫時把回憶拋在腦後。在柵欄外,要是渴望再也不屬於我的事物,只會讓我陷入軟弱、自取滅亡。於是我專注在一步步往前走的動作上,讓一小部分的自己遺落在後頭,留在無法打破的柵欄後方。
終於來到河邊,我發現這裡不像畢夏帶我去過的池邊那麼平靜。這條河很寬,雖稱不上急流,卻相當強勁。午後陽光照射下,水流激起河底泥沙,呈現淡淡褐色。我跪在岸邊用雙手捧起河水,看見水其實相當清澈,於是急忙用雙手將水送入口中,咕嚕咕嚕喝下。舌頭嘗到第一滴水,才意識到自己真的好渴。
我將水潑到臉上,脫下毛衣放在河岸,捧水輕輕擦臉、擦脖子,並檢查傷口。把我丟出柵欄的守衛想必相當粗魯,我下唇腫脹刺痛,後腦勺一摸就痛,我忍不住咬牙,深深從齒縫吸氣。我的雙臂有十幾道交錯的刮傷,傷口很深。我把手泡進河中搓洗,洗去血跡,也努力刷去指縫間的泥土。
太陽開始西沉,薄薄一道光線劃過樹林,在我的婚戒上反光。我在水面下伸直左手,看著金戒閃耀,光線變換。還記得畢夏為我套上婚戒那天,記得我發抖著手想取下戒指。當時戒身的觸感是多麼陌生而令人窒息,此刻我卻花了好長的時間才取下戒指。沒了戒指,手指留下一道痕跡,一圈柔軟的皮膚,感覺好赤裸。這枚戒指讓我想起自己失去的一切。我再也無法戴上它了。我輕輕握住戒指,張開手,讓河流將它帶走。
* * *
除了之前在柵欄旁的小孩子,我沒看見其他人,也不覺得有人在監視我,但還是感覺毫無防備。若是有人前來,我根本無法自衛。我原以為要撐幾個小時才能睡著,但疲憊的身體卻另作他想,閉上眼立刻墜入黑暗之中。
* * *
醒來的時候很難推測時間,不曉得是早上或下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十二或二十小時。天色陰沉,烏雲從西方翻騰而來,雷聲隆隆,看來暴風雨將至。我感覺這場睡眠像是失去意識,醒來時完全沒有放鬆,反而痠痛僵硬、視線模糊,彷彿透過一片髒玻璃看世界。我用手撐著地面起身,深深吸氣,腦袋傳來刺痛感。
我得在暴雨來臨前找個更合適的遮蔽處。氣溫雖暖,我卻擔心全身溼透、體溫下降會有什麼後果。我不想離開河邊,只好安慰自己不會離開太遠,只在近處尋覓地點。我餓到胃抽筋,於是出發前先跪在河邊,捧著水大口喝下,緩解胃痛。
我從河邊朝正東方出發,尋找能遮雨的地點。起初除了大片荒地什麼也沒看到。
轟隆一聲,雷聲又近了一些。凜冽的風將頭髮颳到面前。我爬到地勢略高處,看見不遠的地方有輛生鏽的車。我小心翼翼地靠近,看來起碼有數十年沒人碰過這輛車了。粉碎的輪胎潰不成形,駕駛側兩扇車門都拆了,擋風玻璃也碎了,車內還傳來淡淡腐臭,但它是眼前最合適的遮蔽。我爬進後座,躺在斑駁龜裂的皮椅套上。
幾分鐘後暴雨來襲,雨水猛烈沖刷車身,從兩側灌進來,我只好窩在中間以免淋溼。我很感激有地方避雨,但坐在車上沒有任何事物能讓我分散注意力,思緒忍不住又回到西洛,想起家人,還有畢夏。我對他的渴望成了真切的痛,彷彿胸口被緊緊捏著,陣陣抽痛。我咬住臉頰內側,不讓自己哭出來,雙手壓緊閉上的眼睛。要忘記一個認識不深的人不應該如此困難。畢夏不過出現在我的人生中幾個月,卻不知為何留下了深深刻印,而這完全與我們相處時間的長短無關。
我把手放下,睜開眼睛,看著雨水猛烈沖刷車外的長長野草,努力清空腦中思緒。或許我必須讓自己成為一片空白,假裝生命從昨天才開始,在此之前一無所有,唯有如此才能生存。我眼皮沉重,呼吸隨著雨聲愈發深沉,漸漸放鬆下來,頭靠著滿是灰塵的車窗。
* * *
一開始,我以為自己夢見咬過我的狗,後來被凱莉用狗鍊勒死的那隻。我聽見低吼聲,聞到溼溼的毛皮味和腐臭氣息,一轉身卻什麼也沒打到,手擊中了滑滑硬硬的東西。我猛然睜開眼,發現自己在車內,手放在皮椅套上。腦袋還沒意識到此刻的情況,身體已經先往後躲,避開眼前的威脅─車門邊有一隻滴著口水的郊狼,牠糾結的淺褐色毛皮黏滿泥土。郊狼對我露出黃牙,喉頭發出低吼。我從沒見過活生生的郊狼,只聽父親說過牠們在柵欄外集體行動。眼前只有一隻,但牠的同伴可能就在附近。
「走開!」我大喊,用腳踢狼。恐慌的情緒在血管裡流動,我一方面知道自己必須冷靜下來思考對策,另一方面卻嚇得只想逃。我踢中郊狼頭部,牠退開,但沒過幾秒鐘立刻折返,這次還把前爪搭上後座,以狩獵者的眼神打量我。我不知道郊狼的力量是否足以致命,但絕對能讓我身受重傷。
我抽回腳再踢一次,這次郊狼猛衝上來用力一咬,卻落了個空,距離我穿著帆布鞋的腳趾只差幾毫米。我尖叫著揮舞雙臂往後躲,搜尋車內能充當武器的物品。我狂亂的目光落在破碎的擋風玻璃上,看見有一段金屬窗框往內伸,尖端裂成兩頭。我一邊看著郊狼,一邊往前移動。我不敢再踢牠,因為一旦腳被咬住,牠幾秒之內就會將我完全扯碎。我深呼吸跳到前座,接著郊狼衝進車裡,我放聲尖叫,牠呼出的灼熱氣息拂過我頸間。
我聽見郊狼在後座狂亂低吼,橫衝直撞,但我沒有往後看,只是伸手從窗框拔下鬆脫的金屬框,手指隱約傳來割傷的感覺。我轉身高舉金屬棍,在郊狼撲上來之際刺穿牠。尖銳的金屬深深刺入牠眼裡,狼與我同時放聲大吼,滿身鮮血。
郊狼摔到後座腳踏墊上,猛烈搖頭想甩掉金屬棍,溫熱的血液滴落在我手臂。我費力爬出車外開始奔跑,沒回頭看。我的手指似乎正在大量出血。我把手握在胸前,奮力跑了一分鐘就不得不停下來,因為頭暈得天旋地轉,胃也在翻攪。我用沒受傷的手擦嘴,一邊回頭張望,視線在長草之間搜尋,不過毫無動靜。
等我回到河邊,前臂血如泉湧,從手肘滴下。我跪在河邊,首次仔細查看傷勢。右手四指接近掌根處都割傷了,無名指的傷口最深,垂著鬆鬆的皮,露出白骨。我抬頭不看,深呼吸,直到胃部平息下來。
我脫下正面沾滿鮮血的毛衣丟在一旁,用牙齒和手設法咬下背心一角,以布條緊壓手指,希望能止血。
在柵欄外才一天就已經吃了敗仗。我既訝異自己竟然沒哭、沒有怕得發抖,卻也明白這道傷口或許只是個起頭。未來將面對更多的傷痛與考驗,我沒有本錢每次都崩潰。
鮮血浸透了布條,血也快止住了。我再度用牙齒咬起纏在指間的血淋淋布條,打一個結。不曉得有沒有用,至少能對傷口加壓吧。
我在河岸彎下腰,用沒受傷的手潑水到臉上,捧水喝了一把。雨停了,撥雲見日,正是日落時分。我看不清自己在河面上的倒影,或許算是好事吧。我只看見頭頸部的輪廓和身後樹木的線條。
還看見身後有男人的倒影。
我猛轉過身,蹲在河岸草皮上的雙腿打了滑,趕緊伸手支撐。受傷的手插進土中,又開始流血,但我管不了那麼多。昏沉天色之下,我的呼吸急促而粗重。
起初看不出是誰,只知道是個男人,暮色模糊了他的臉孔。但是當他往前走,我便看見他的藍眼睛,那雙再熟悉不過的藍眼睛。
「嗨,漂亮女孩。」馬克微笑著對我打招呼。
2
我和馬克互相瞪視,持續了彷彿永無止境的一段時間,周遭只有沉默。直覺告訴我不能讓他看出我有多害怕,不能讓他知道我害怕到胃部揪成一團、後頸毛髮因為即將發生壞事的預感而顫動。自從跟蹤畢夏走到柵欄外那天之後,我再也沒見過馬克,但我早已明白這一刻終究會來。
「嗨,馬克。」我的口氣聽起來很正常,連自己都感到意外。
他歪頭看我,笑意從飽滿的臉頰上消失。即使我知道他的底細,此刻他那張圓臉和發亮的藍色眼眸看起來卻是一派天真。他靠近一步,我推著地面打算起身。我站起來比他高幾公分,身勢壓過他總好過受他壓制。但我尚未起身,他便抬腳踩住我腳踝,雖然力氣沒大到會讓我骨折,可能受傷的威脅卻懸在我倆之間,像是醜惡的預告。
「最好別起身。看樣子妳經歷了不少啊。」他非常緩慢地蹲下來,彷彿擁有全世界的時間可以揮霍。他蹲在我旁邊,移開腳掌,改用手輕輕扣住我腳踝。
「我沒事。」我的聲音聽起來微微發抖。我清楚看見馬克一聽見我的聲音,眼神就變得黑暗,一臉飢渴。我的直覺沒錯,他喜歡用別人的恐懼餵養自己。我告誡自己別去想他傷害過的九歲女童,在他病態、變態的雙耳聽來,她的哭喊或許如同樂音。「請放手。」我試探性扭動腿部,他卻收緊了手,緊緊扣住我的阿基里斯腱。
「妳怎麼了?」他問,一副沒聽到我說話的樣子,「被流放了?」
我點頭。他看著我放聲大笑,我不禁打了冷顫。「為什麼呢?」
我猶豫著,在心中衡量眼前的選項,決定這麼回答:「我圖謀殺害領導之子。」
馬克搖頭,「妳騙人,我看過妳望著他的眼神。」見我一臉驚嚇,他得意地笑了,「他來施捨那一天,以為我沒看到妳嗎?」他食指伸進我牛仔褲褲管,像蛇一般摸索我的皮膚,我像觸了電似的往後一縮,可是無處可躲。我已經落入他手中了。「我知道妳的身分,也知道他是誰。」
「我什麼身分都沒有了。」說出這難過的事實令我心痛。「我是孤身一人來到柵欄外,和你一樣。」無論在什麼處境下,把自己和他相提並論都讓我忍不住想尖叫。但我打算誘導他繼續說話,不讓他分心去做別的事。我問他:「你有沒有遇到其他人?流放者有沒有安全的去處?」或許他會把我視為夥伴,不傷害我。
可是他根本聽不進我的話,直接伸出另一隻手,親暱地撫摸我的臉頰。我奮力別開頭,急促地呼吸,吸氣時彷彿要灼傷似的,「不准碰我!」
「臉上有血呢。」他語調放軟,我聽了握緊拳頭,指甲陷入肉裡。「可憐的小臉蛋。」他手指滑過我嘴唇,我「啪」一聲撥開他的手。
「我說不、准、碰、我。」
他抓住我後頸用力一掐,拇指按壓我被守衛打過的舊傷。我放聲大喊,雙手拉扯他手臂,一陣痛楚有如閃電劈過頭部,眼前冒出金星。
「妳不准……絕對不准告訴我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他齜牙咧嘴地咆哮,「愚蠢的賤人!」
他戲演夠了,絲毫不願再對我裝出親切的模樣。恐懼湧現心頭,來得疾速又充滿惡意,我的心臟彷彿要爆開了。稍早的疲累瞬間消失,體內所有細胞突然振作起來,準備迎戰。
馬克把我往後一推,雙手抓住我手腕,壓到我身上。我腿向上踢,狂亂抵抗,急著甩開他。若是站著,我還能利用身高與他抗衡,但平躺在地,他的重量占盡優勢。要是被壓制住,我就完了。
我膝蓋勾住他側身,他悶哼一聲,在我臉上吐出又熱又臭的氣息。我沒有浪費力氣尖叫,反正也沒人會來幫我。此刻只聽見兩人呼吸粗啞,激烈吐氣,堅硬的骨頭碰撞柔軟肌肉。他用力往我臉上攻擊,揍得我頭昏眼花,眼睛彷彿要從眼眶掉了出來。我掙脫一隻手,用指甲在他側臉抓出三道血痕。我一聽他喊痛便力氣大增,奮力翻過身,背對他爬開,手肘像活塞一般支撐自己匍匐前進。
才爬了兩公尺左右,他又撲上來了。他抓住我臀部跨坐上來,將我的臉壓倒在地。泥沙掩住我的口鼻,氣息吸不上來,滿臉都是鼻涕口水。他再度將我的臉重擊地面,我的嘴唇似乎裂了。他放開我的頭,抓住我右手臂,往後扭到接近脖子的位置。
「很好玩吧,」他在我頭上喘氣,「打打架也不錯,但現在開始照我的方式來!」他用另一隻手扭我受傷的手指,我尖叫。「哎呀,這裡是怎麼啦?」他的口氣一派輕鬆,像在討論天氣。
我懶得回答,他放開我手指,繼續在手臂施壓。我肩膀和心臟一起抽痛,稍微移動就痛到無法忍受。「放手,」我氣喘吁吁,「放手,我不會再抵抗。」
「是嗎?」我能聽出他語氣中的笑意,「妳這該死的騙子。但是妳聽好了,我這就放開,因為我太善良了。」
「什麼?」我還沒問他是什麼意思,他突然用力一扭,我手臂脫臼,一股熱辣的劇痛襲來。我長而尖銳的大喊穿透夜晚天空,眼前蒙上一片有如烏鴉翅膀的黑暗。
我氣若游絲,馬克心滿意足地哼了一聲,對自己的傑作非常驕傲。我依然處於驚嚇狀態,又身負重傷,然而在恐懼與疼痛之下,有一股不請自來的怒火意外沸騰起來。我氣馬克,氣父親、氣凱莉、氣領導、氣母親,甚至連畢夏都讓我生氣。怒火在體內攪動,翻騰著一片鮮紅的純粹惡意。有一部分的我意志堅決,知道若是對黑暗投降就再也醒不過來。馬克會對我為所欲為,讓我曝屍河岸。我經歷了這麼多,絕不會讓此人就這樣終結我的生命。
正當眼前差點一黑,視線邊緣開始暗下來之際,我奮力咬舌,嚐到了鮮血鹹味滑過齒間。黑暗漸漸消退,但還未完全散去,於是我再次咬下舌頭同一處,尖銳的刺痛逼迫我專心掃去黑暗。
馬克從我身上移開,自信滿滿地認為他已將我拿下。我伸直左手放在草地上,小心翼翼往旁邊移動,抓到一顆石頭,緊緊握住。
「這不是好多了?」馬克聽來像在自言自語,「轉過來,我要看妳的臉。」
他把我翻過來,完全不顧我脫臼的手。我咬著舌頭忍住不叫出聲,逼迫自己順從地躺著,半閉著眼。表面上我依然保持不動,卻是耗盡了全身力氣才能不去抵抗。我提醒自己,此刻或許是這輩子最需要思考、而非行動的時刻。他傾身靠近我,我繼續等待,知道機會只有一次。
「喂,妳是被嚇到了嗎?醒醒啊。」他打我一巴掌,我只是偏過頭。「喂!」他又喊了一聲,靠得更近,那雙藍眼距離我只有幾公分。我迅速抬手,死命往他頭側砸。他沒有如我預期般陷入昏迷,但顯然嚇壞了,四肢著地,垂著頭搖搖晃晃。我沒受傷的左手依然拿著石頭,同時撐著地面坐起來,對準他後腦勺再次砸落。馬克手一軟,趴在我腿上倒了下來。我踢開他,從喉嚨後方發出尖銳的哭嚎。他還有意識,想趁我起身時抓住我的腿,但手指滑開了。我砸他第三次,正中太陽穴,他雙眼上吊。
我跨在他身上喘氣,想哭卻哭不出來,緊緊握住石頭的手指傳來痛楚。明知道應該再砸一次,但我抬起手卻砸不下去。
腦中聽見凱莉喊我:「殺了他啊,可惡,妳還在等什麼?」連畢夏也在我耳邊低語,催促我終結馬克的性命。雖然誰也不能擔保未來會發生什麼事,起碼我不必再擔心馬克或任何人會來傷害我。我知道畢夏不希望看到我猶豫。
但我下不了手。如同我不希望他殺我,我也不希望他讓我變成殺人兇手。石頭從我麻木的指間落下,我彎腰脫去他的鞋子。我只剩下一隻手能動作,因此花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時間。脫到第二隻鞋的時候,我備感挫折,開始痛哭流涕。我轉身把鞋子丟進河裡,看它們順著黑色水流漂走。
天色幾乎全黑,太陽早已消失,還好今天是滿月。我看到地上有個之前沒注意到的袋子,想必是馬克遇見我之際暫時丟下的。我撿起來,沒看內容物就斜揹在身上,背帶碰到傷處又忍不住落淚。
我從地上拿起毛衣,頭也不回地往南方前進。我得找個不會被急流沖走的地方過河。每走一步肩膀都隱隱作痛,雖然痛楚從未消失,感覺卻很疏離,像是看著別人受苦,而非親身經歷。再過不久,等到驚嚇或腎上腺素消退,疼痛就會真正發作了吧。我必須在那之前遠離馬克。
走了起碼十五分鐘,河床才開始變窄,橫跨河床的岩石裸露出來。看來無論如何都要打溼身子過河,希望我不會掉進河裡或被水沖走。從任何地方過河都不好走,石頭滑溜不平,我無法以右手保持平衡,結果失去重心,半途腳一滑,差一點栽跟斗摔進河裡。我跪在岩石上,頭髮垂在臉上,肩膀痛得不得了,受傷的右手又開始滴血。我深吸一口氣,氣息不穩。剛才助我擊敗馬克的怒氣已經消散,有如風中煙霧。我身上只剩下疲憊,從來沒有這樣累到骨子裡,累到靈魂裡。我究竟想要放棄,還是繼續?要活?要死?多戰鬥一天,還是舉白旗讓河水將我帶走?我警告自己,這可是最後一次問這種問題了。不管答案是什麼,這都是最後一次了。
起來,艾薇,妳做得到。對我說這句話的不是自己,而是畢夏。我想像他在我身旁,他會直視我的雙眼,要我堅持下去。他一直那麼相信我,到頭來我卻逼著他放棄對我的信任,面對苦澀而醜陋的結局。如果他在這裡,一定會扶我起來,帶我一起過河。遇上滑溜的岩石,我們會攙扶對方。因為有了彼此在身旁,我們總是表現得更好,更堅強。
我明白,想念他只是自溺,我沒有資格沉淪。等到早晨熾烈的陽光灑下,我可能會後悔此刻的軟弱。但眼前只有冷淡的銀月看著我,我暫時允許自己假裝畢夏就在身邊,伸出溫暖的手讓我牽著,藉此安慰自己。
接著我起身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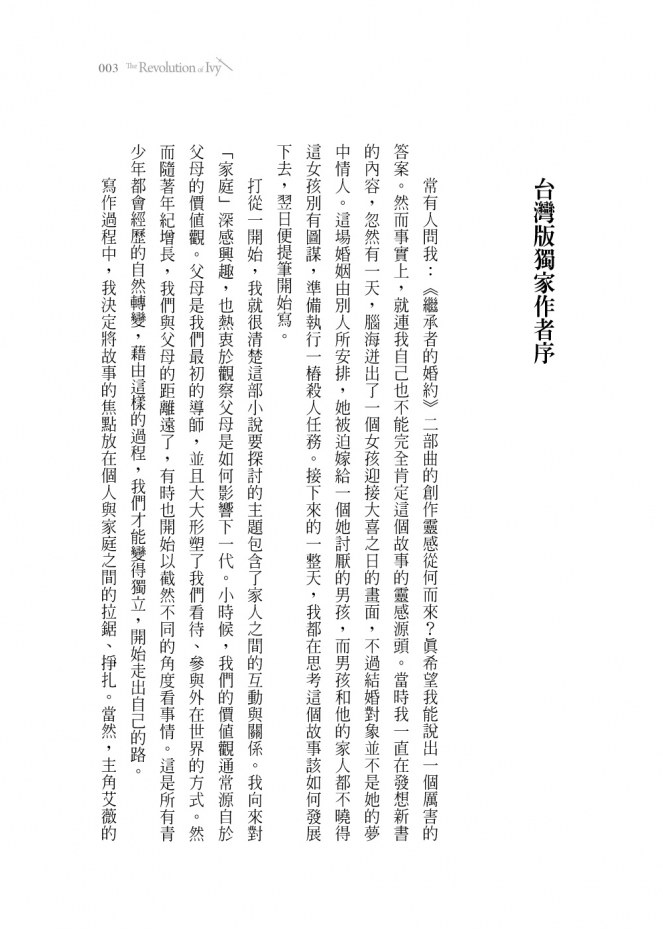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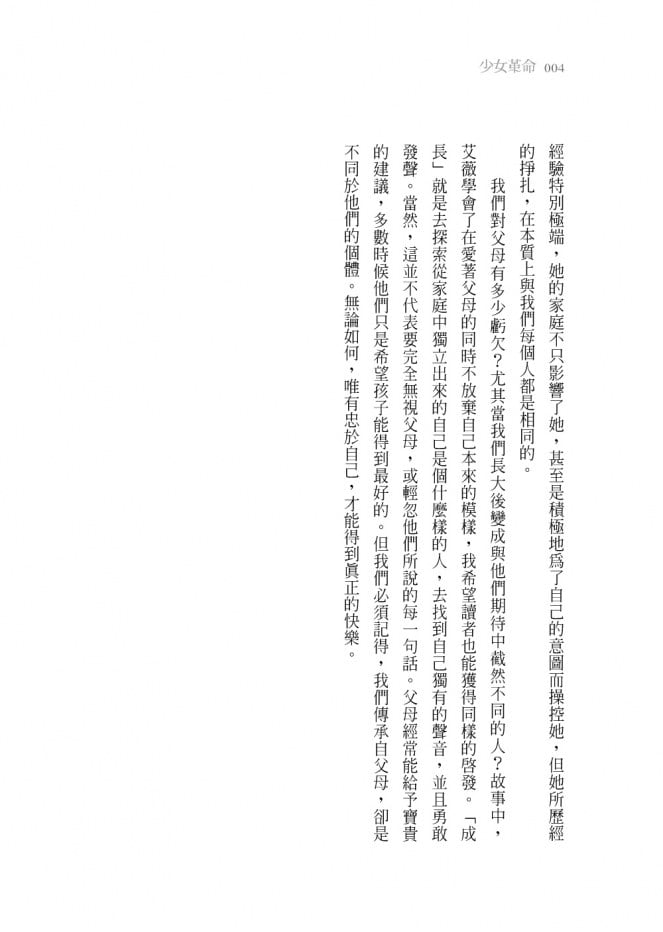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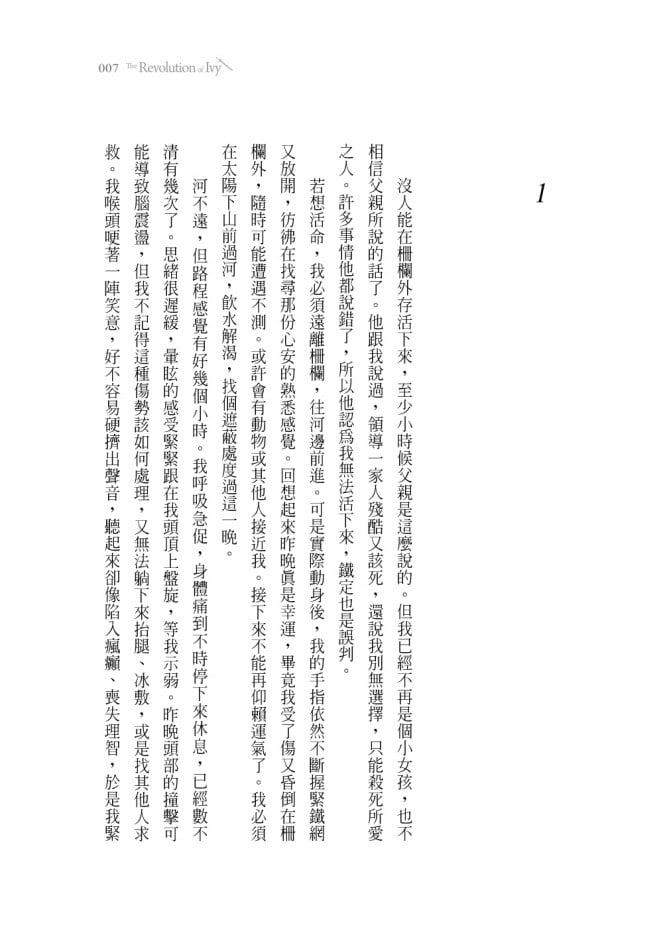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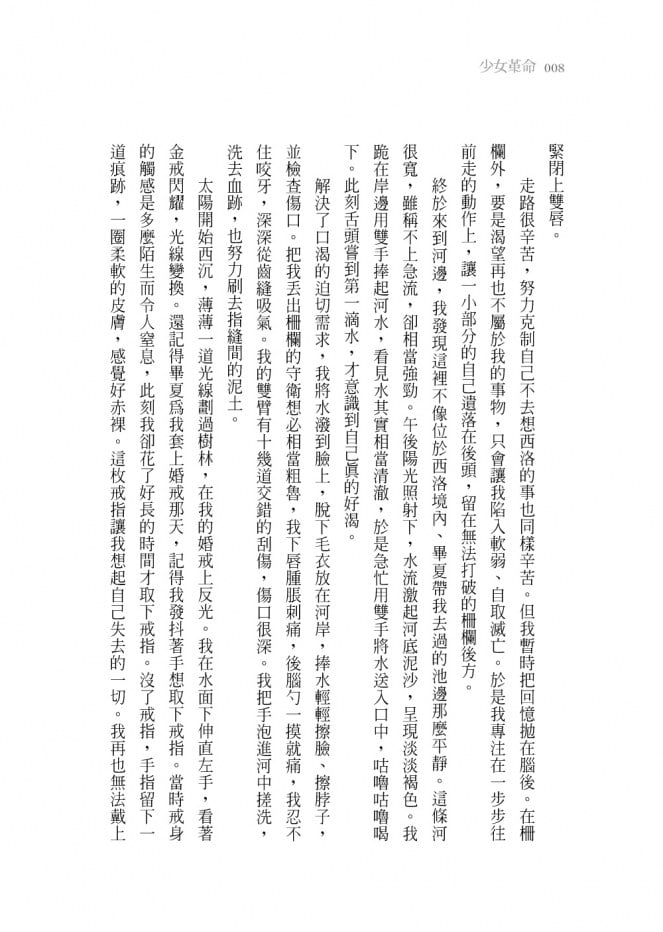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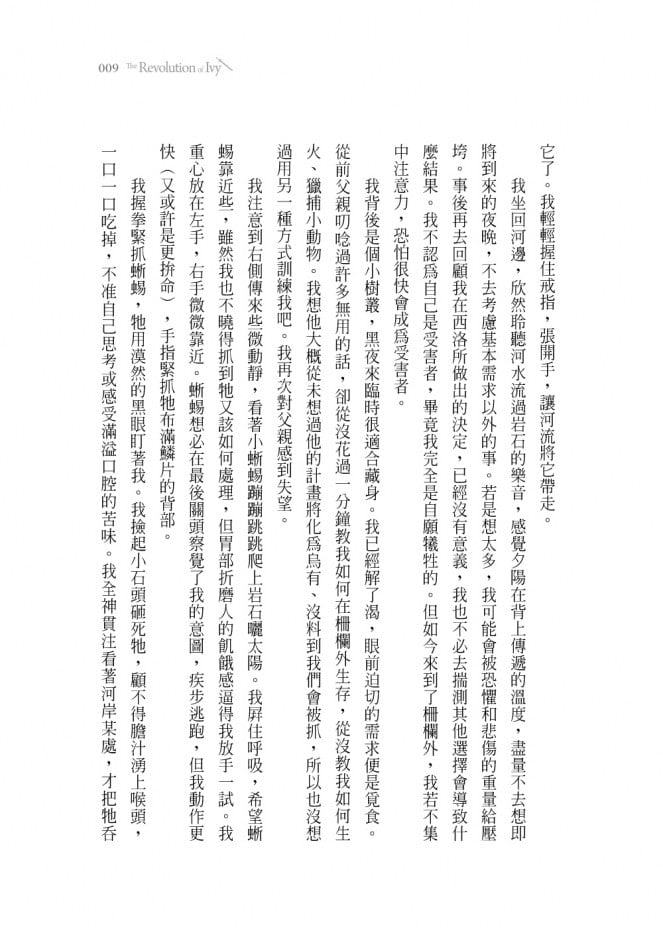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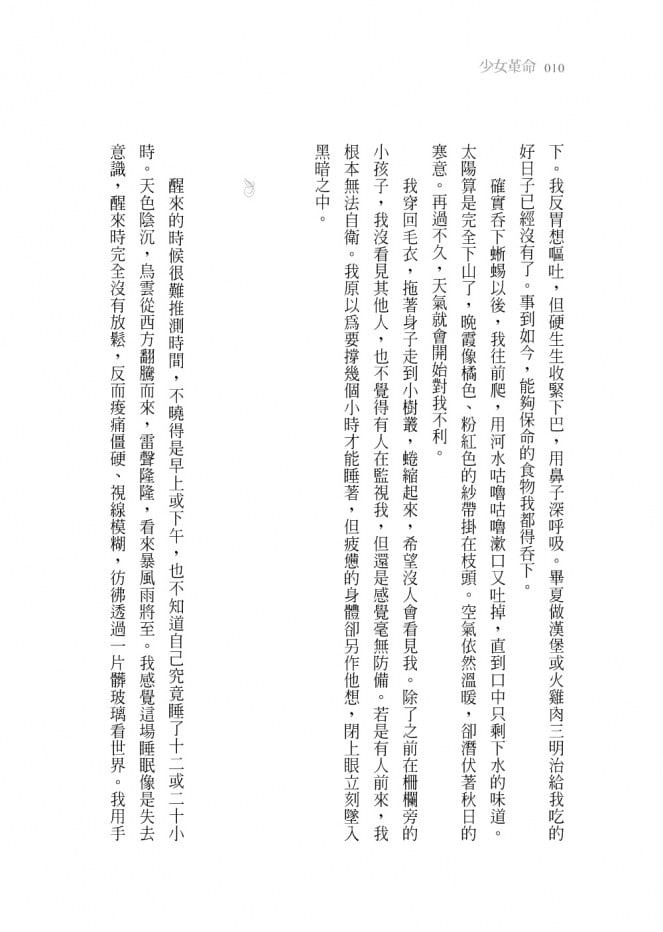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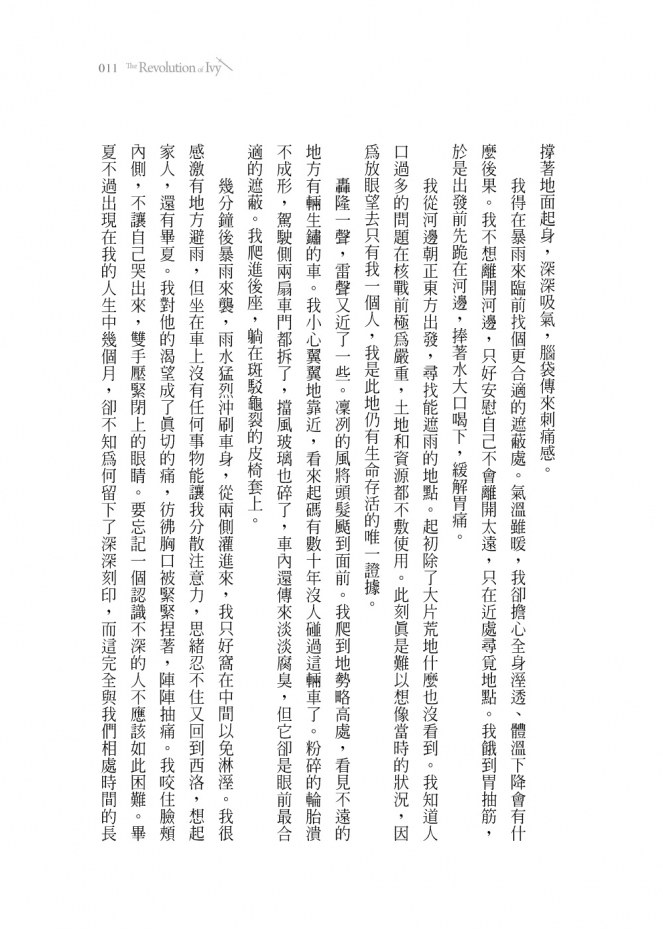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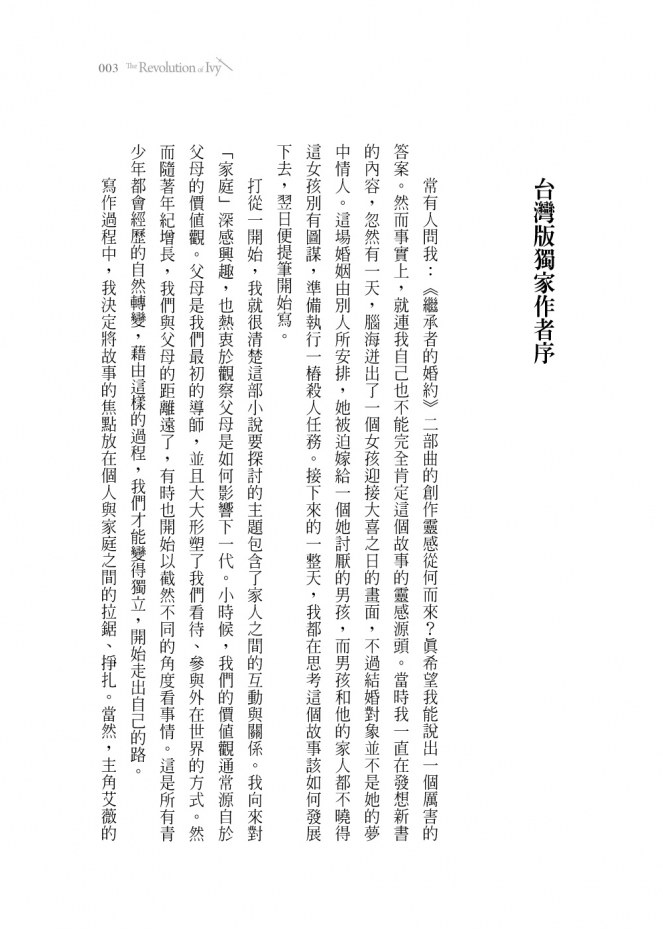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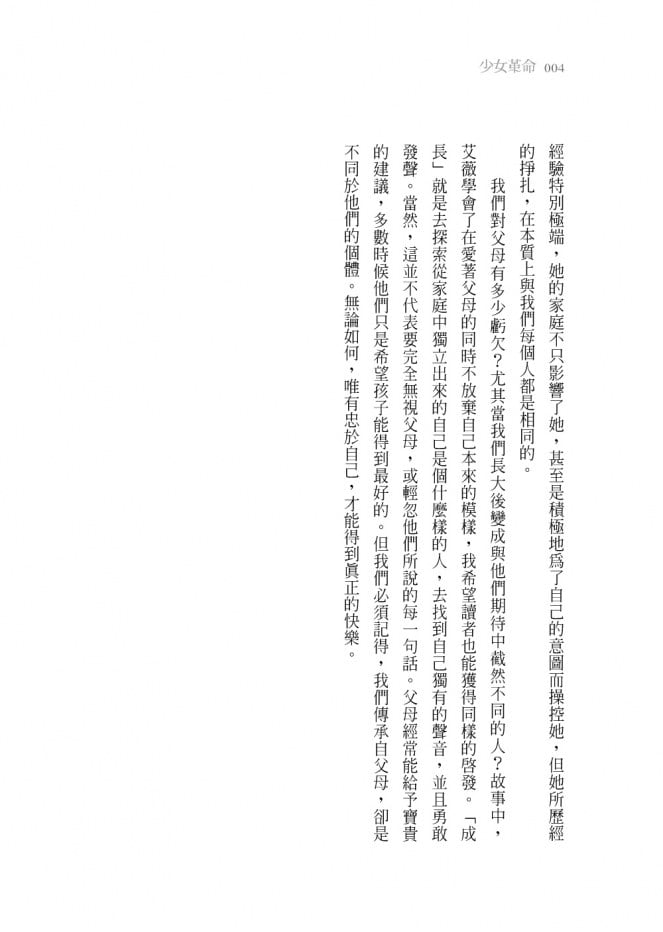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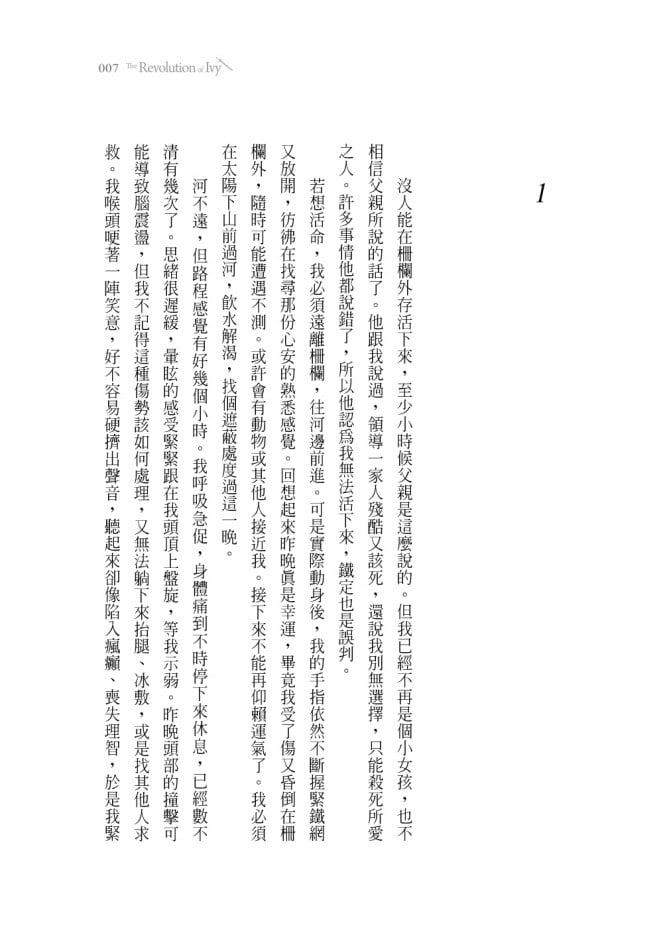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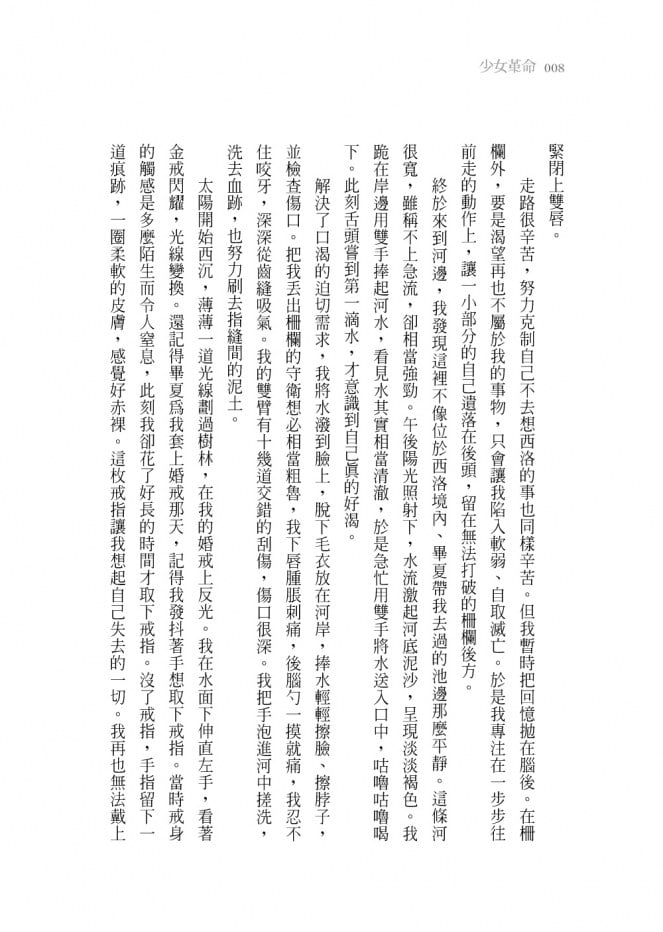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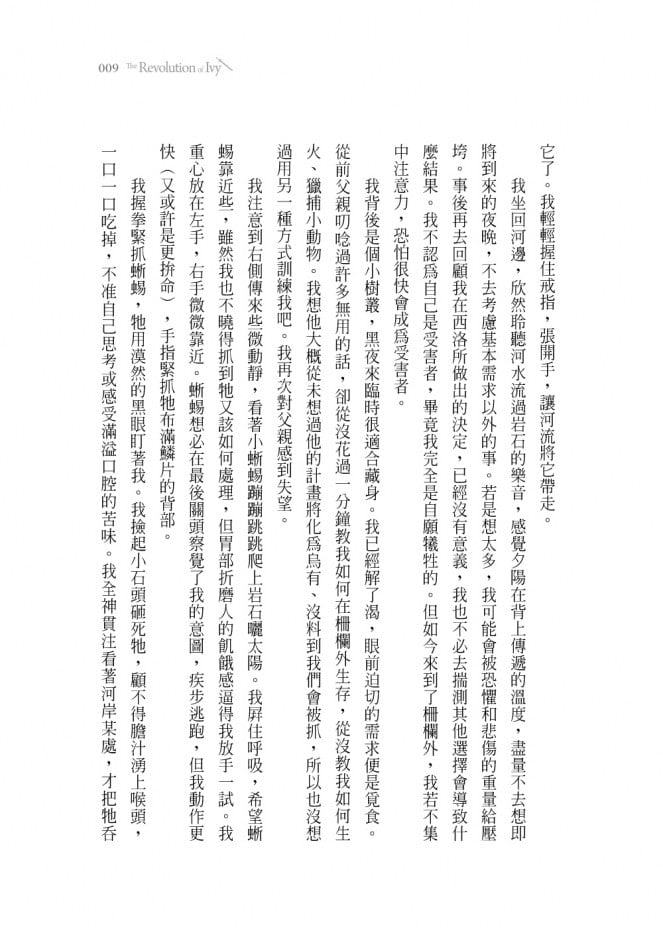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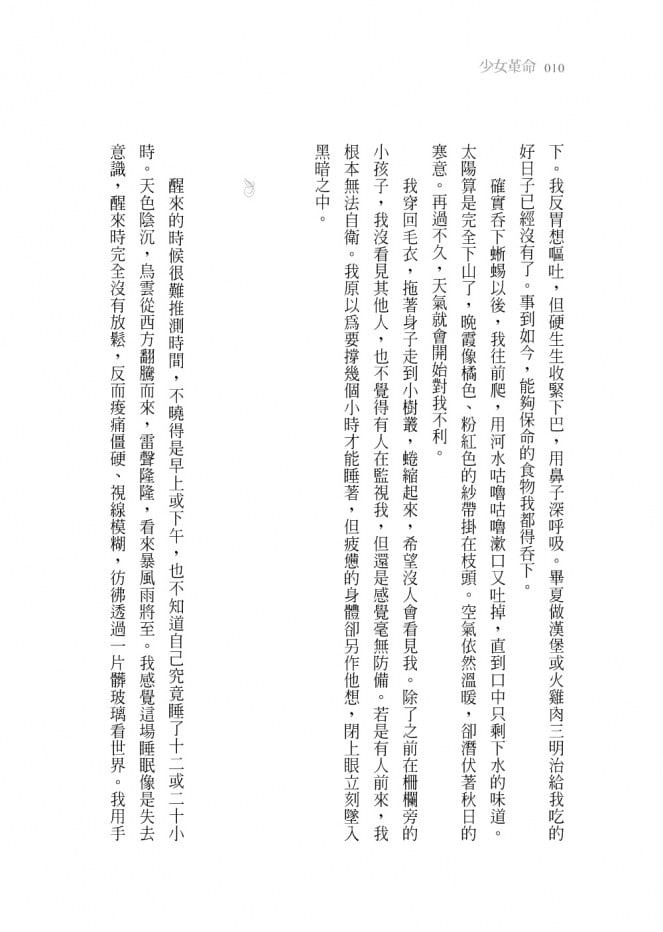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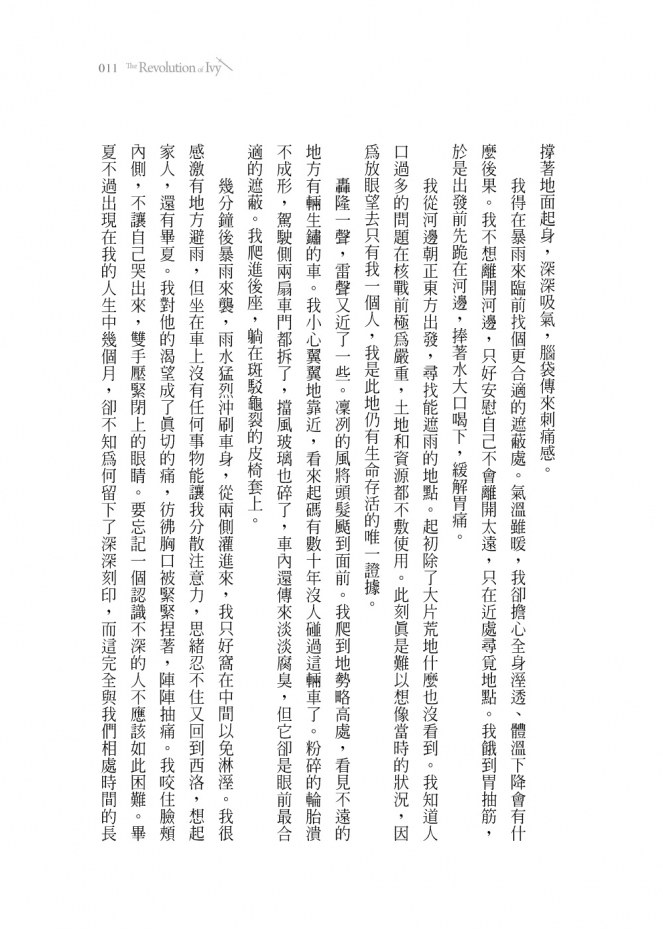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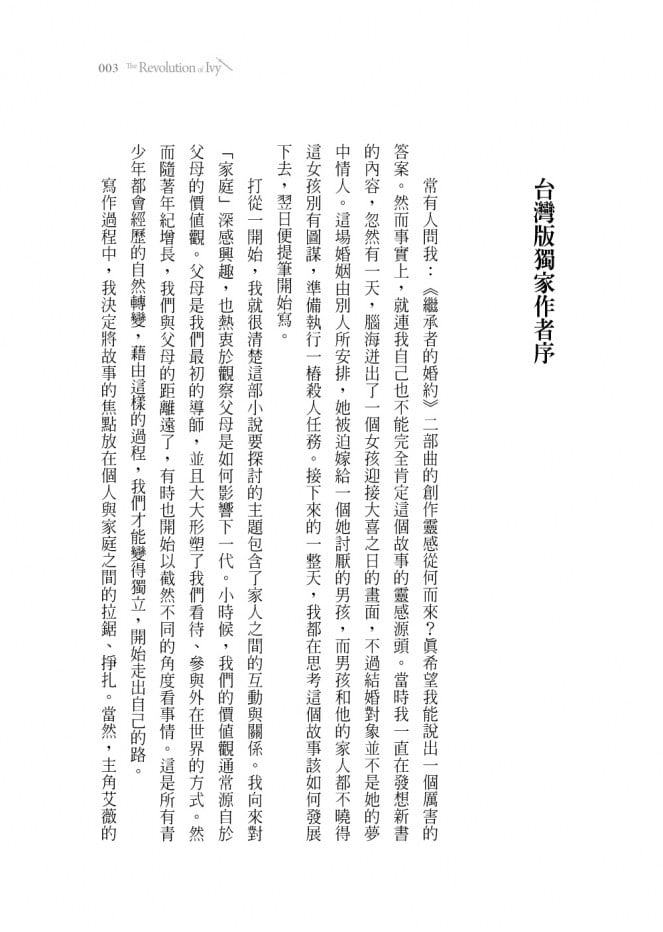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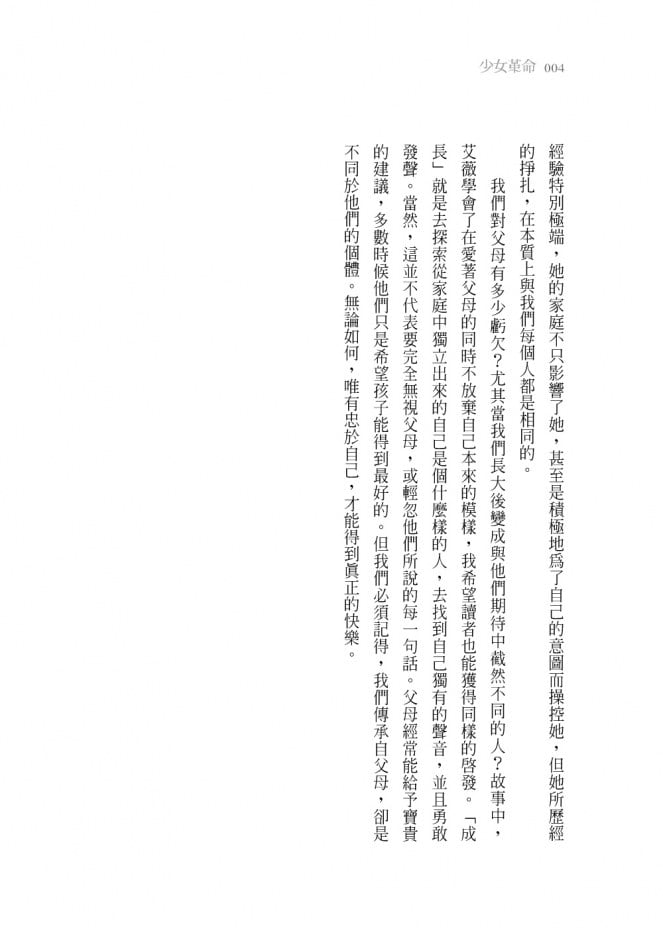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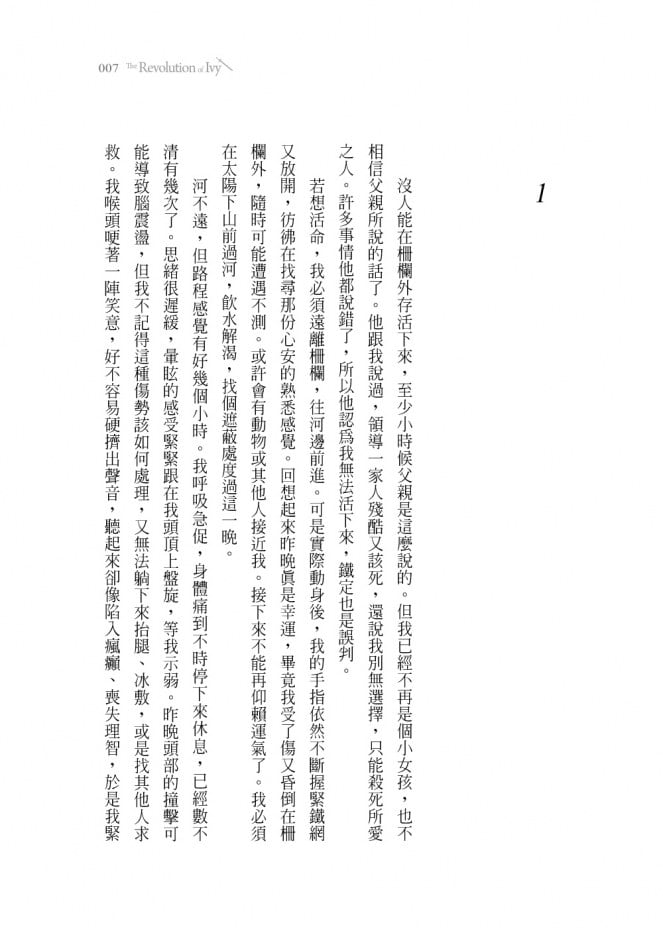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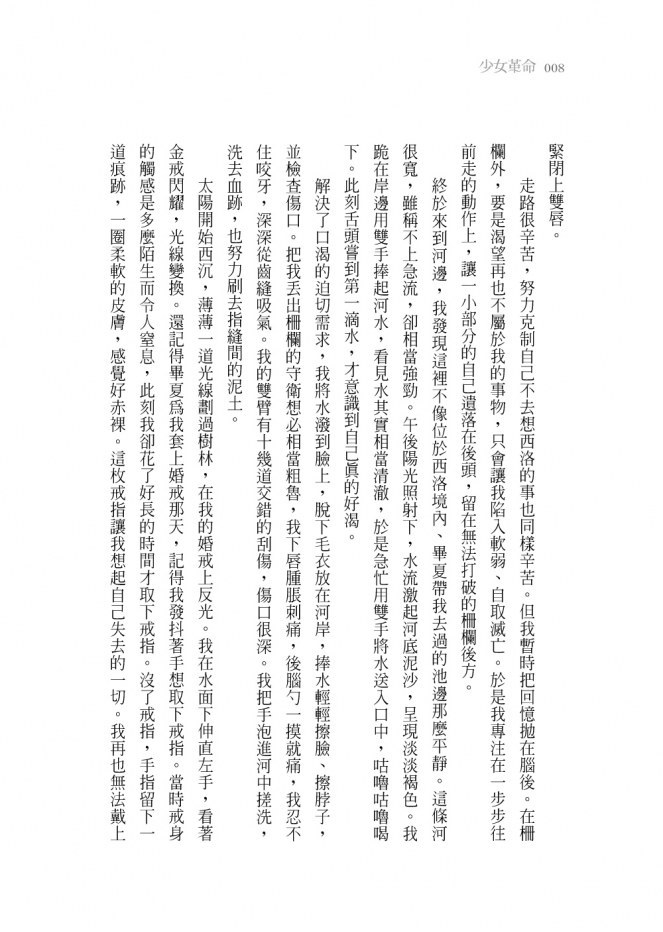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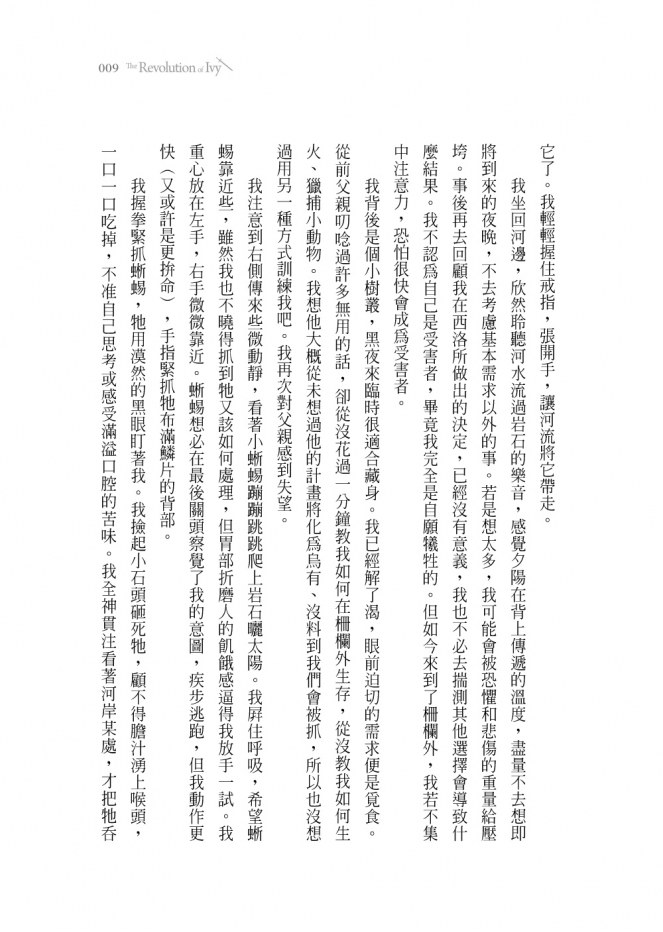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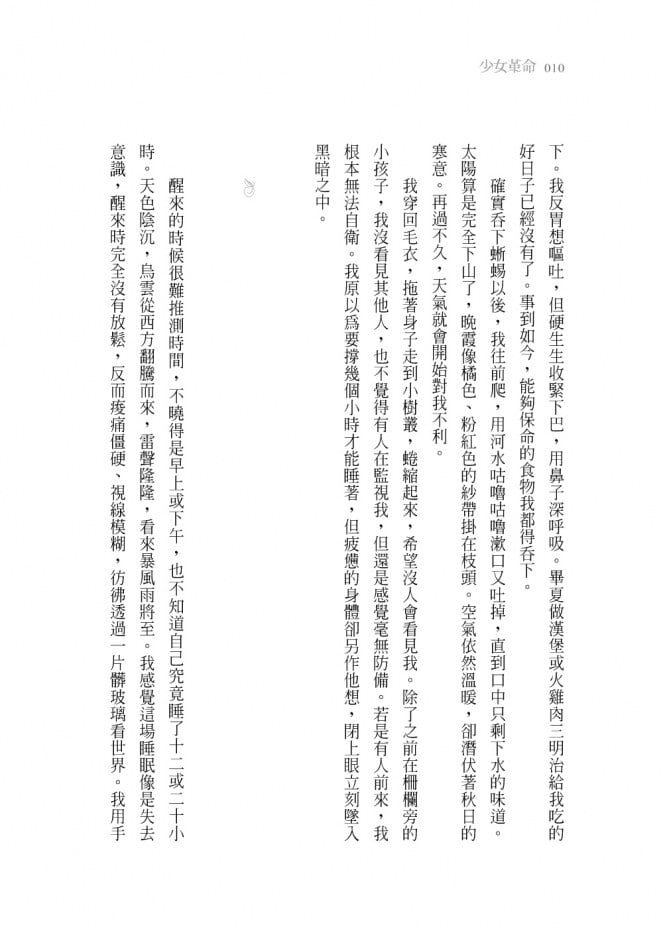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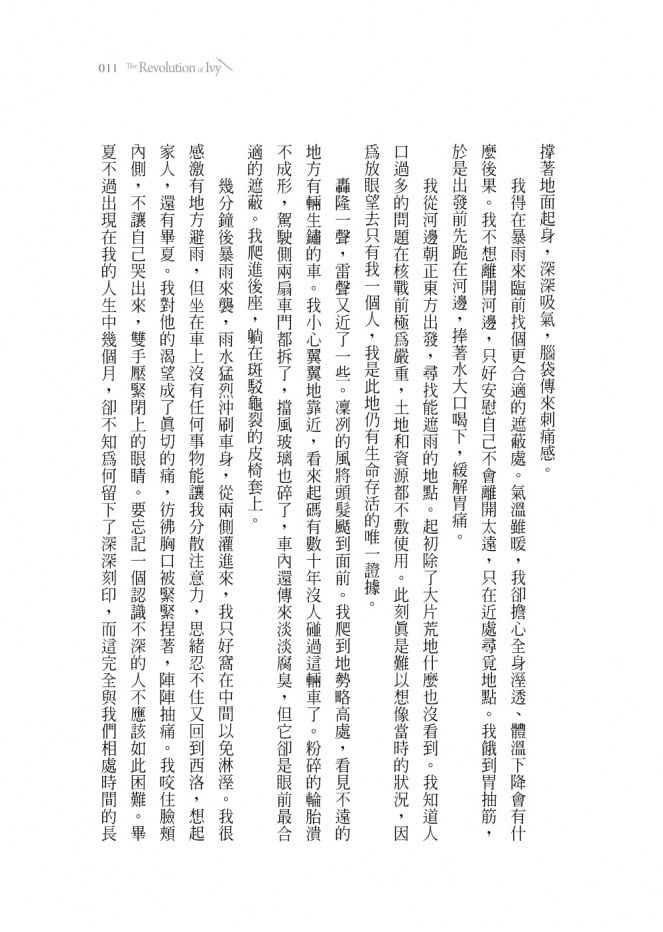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