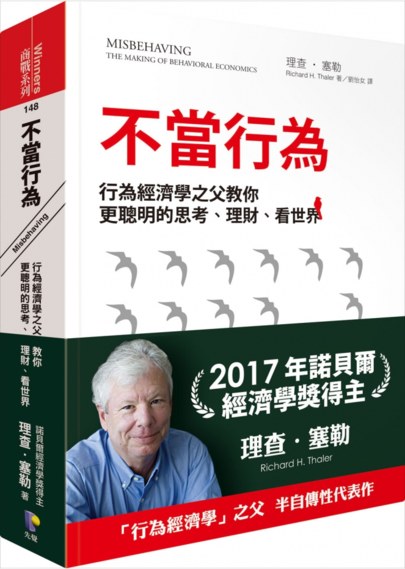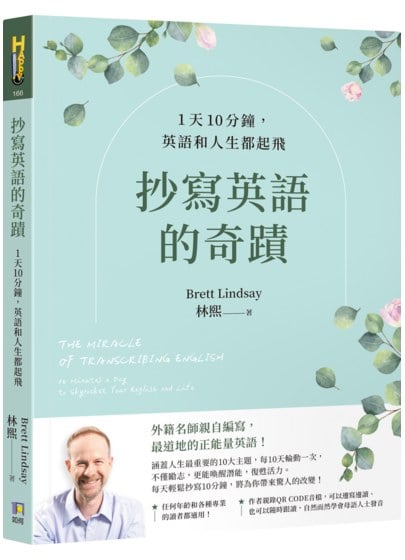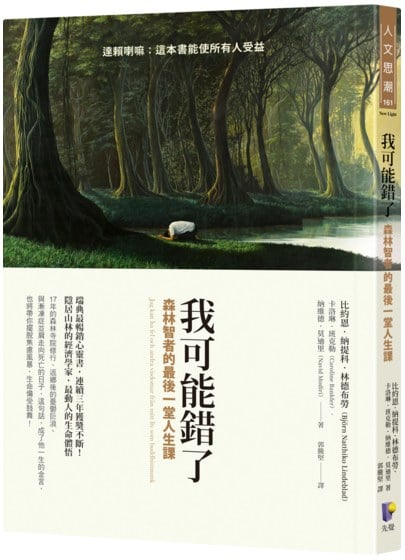內容簡介
★德國出版史上最暢銷的翻譯文學作品!僅托爾金的《魔戒》可與媲美!
★德語版雄踞榜首,暢銷破100萬冊!橫掃歐美書市的慢熟經典小說!
★名列「20世紀西班牙文百大經典小說」,已擄獲全球近30個國家200萬讀者的心!
★德國重量級書評家‧萊赫藍尼基讚嘆:「馬利亞斯是當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如果有誰值得和他相提並論,那只有馬奎斯了。」
★榮獲西班牙國家評論獎/IMPAC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紐約公立圖書館1996年度全美最重要的25本書之一
★國際媒體齊聲讚譽:
‧本書作者堪稱當代西班牙文學領域最敏銳、最具天賦的作家! ──《波士頓環球報》
‧開啟文學新視野的不同凡響之作。 ──《法國世界報》
‧曲折的情節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是一部娛樂與機智兼具的小說。 ──《華盛頓郵報》
‧當我們得知這位生活在當代,談話間卻充滿復古風韻的作家,藉由異國文化歷史帶來格外豐富的閱讀內涵,同時又透徹了解我們的文化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多麼珍罕的禮物啊!
──《紐約時報》溫蒂.萊瑟
‧這位當代知名作家的著作相當優秀──兩個文明交織著複雜情感的婚姻,令人想起亨利.詹姆斯引人入勝又錯綜複雜的風格。──《時代雜誌》英國版/詹姆斯.伍道
★鄧惠文、貴婦奈奈、范湲(《風之影》譯者) 熱愛推薦
是什麼樣的秘密,讓美麗的她在蜜月之後舉槍自盡?
如果最親近的他開始讓你覺得陌生,會是什麼情景……
「她剛從蜜月旅行回家後不久,便走進浴室,對著鏡子,敞開襯衫,脫下胸罩,拿著她父親的手槍指著自己的心臟……」
一名剛從蜜月旅行回來的國際會議專業口譯,亟欲找尋多年前那顆被抵在槍口下的心,究竟藏了什麼秘密──同樣也是剛度完蜜月,何以如此冷絕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想解開謎團,因為死去的是他阿姨,也是他父親的前妻……
看似被淡忘的陳年舊事,其實是暗藏在每個人內心角落的秘密。作者馬利亞斯替我們述說了心底最幽微的感受:誰不是守著秘密、戴著面具過日子?自己的秘密,愛人的秘密,家族的秘密,日復一日地積累。本書就像一長排的稜鏡,映出了各種人生風景,或許你會在其中看見自己過往的海市蜃樓。
作者介紹
哈維爾.馬利亞斯(Javier Marías)
‧1951年生於馬德里,父親是哲學家,母親是西班牙文教授。佛朗哥執政時期,馬利亞斯的父親因政治立場與當局相左,被當時的西班牙學術界孤立在外,只好舉家赴美講學。父母在衛斯理學院任教期間,樓上住的正是俄國小說家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多年後,將納博可夫名作《羅麗泰》譯成西班牙文的,正是馬利亞斯。
‧19歲時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是譯介英國文學的重要旗手,並獲得西班牙國家翻譯獎。曾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美國衛斯理學院,以及西班牙馬德里大學。1994年婉拒出任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卻加入才成立不久的國際作家協會。
‧已出版多本長、短篇小說,以及散文、書評、翻譯等。不僅在西班牙當代文壇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最具國際知名度的作家。
榮獲多項國際獎項肯定
1989年,《靈魂之歌》(Todas las almas)獲巴塞隆納城市文學獎。
1993年,《如此蒼白的心》(Corazón tan blanco)獲西班牙國家評論獎。
1995年,《明日戰場上,勿忘我》(Mañana en la batalla piensa en mí)獲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的「法斯登拉獎」。
1996年,《明日戰場上,勿忘我》獲法國費米納獎最佳外語文學。
1997年,《如此蒼白的心》獲重要的IMPAC都柏林國際文學獎。
1998年,《明日戰場上,勿忘我》獲義大利巴勒摩國際文學獎。
2000年,獲義大利多項文學獎肯定,包括七月以《敏感的男人》(El hombre sentimental)獲Ennio Flaiano文學獎;十月因傑出文學成就,在杜林獲頒Grinzane Cavour獎;十一月在羅馬領取Alberto Moravia國際文學獎。同月,榮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金質騎士獎章。
<關於譯者>戴毓芬
台灣嘉義人。淡江西班牙語文學系畢業,西班牙拿瓦拉(Navarra)大學文學碩士,巴塞隆納自治大學(UAB)翻譯理論博士。
譯有:《在妳的名字裡失序》(圓神出版)《金龍王國》(與張淑英合譯)《冰冷肌膚》。
規格
ISBN:9789861332758
頁數:336,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789861332758
各界推薦
每當與文學同好們聊起《如此蒼白的心》(Corazón tan blanco)時,我總是熱切地建議他們務必去讀讀這本小說。此時此刻,為文推薦一本文字如此敏銳、巧妙的傑作,卻驚覺此事知易行難。
就怕這本小說沒得到它應得的注目!
目前已經退休的德國重量級書評家萊赫藍尼基(Marce Reich-Ranicki)在他著名的電視書評節目中,曾將哈維爾.馬利亞斯(Javier Marías)的小說《如此蒼白的心》評為當代文學無可比擬的傑作,他在節目中直言:「哈維爾.馬利亞斯是當今在世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如果有誰值得和他相提並論,那只有馬奎斯了。」萊赫藍尼基名重一方,難得如此盛讚作品,於是,《如此蒼白的心》德文版直接衝上暢銷榜榜首,數月之間暢銷二十萬冊,截至目前為止,這本小說已在德國、奧地利及瑞士等德語國家締造了超過百萬冊的銷售佳績。德文版《如此蒼白的心》問世當時,號稱與托爾金的《魔戒》並列為德國出版史上最暢銷的翻譯文學作品。
《如此蒼白的心》在國際間受到的矚目和肯定是「慢熟型」的。此書一九九二年在西班牙出版,隔年獲「西班牙國家評論獎」肯定,但直到一九九七年才獲舉世矚目的IMPAC國際都柏林文學獎,同年,紐約公立圖書館將本書列為一九九六年度全美出版品中,最重要的二十五本書之一。馬利亞斯因《如此蒼白的心》揚名國際,西班牙《世界報》(El Mundo)並於千禧年將此書選為「二十世紀西班牙文百大經典小說」之一。
先聊聊馬利亞斯這個人吧!
馬利亞斯一九五一年生於馬德里的顯赫書香世家,父親是西班牙當代哲學名家兼皇家學院院士胡立安‧馬利亞斯(Julián Marías),母親是西班牙文教授。佛朗哥掌權之後,馬利亞斯的父親因政治立場與執政當局相左而被孤立在學術圈外,只好舉家赴美講學。當時,馬利亞斯還不到一歲。其後數年,馬利亞斯父母在美國東岸名校衛斯理學院任教期間,馬家寄居在西班牙當代詩人巨擘吉岩(Jorge Guillén)的住所,樓上住的則是當時也在衛斯理授課的俄國小說家納伯可夫(Vladimir Nabokov),兩家往來密切,多年後,首先將納伯可夫名作《羅麗塔》(Lolita)譯成西班牙文的,正是馬利亞斯。
因為家世的關係,馬利亞斯從小就有機會親炙大師風範,包括在世的和已經作古的,其中,對他的文學生涯多所提攜並且影響甚鉅的是西班牙當代小說巨擘貝內特(Juan Benet)。從小博覽經典名著,經過豐富且飽滿的文字薰陶之後,馬利亞斯從十二歲開始模仿心儀的名家寫短篇小說,十九歲時,在貝內特的引薦之下出版了第一本長篇小說。隔年出版了第二本小說之後,接下來,隔了六年才推出第三部作品。不過,暫停創作這段期間,他繳出了亮麗的翻譯成績,許多外國經典名作,如莎士比亞、康拉德、福克納和吉卜齡等大師作品,皆是由他譯介給西班牙文讀者,曾以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史坦恩(Laurence Sterne)的《崔斯川‧項迪》(Tristram Shandy)西班牙文譯本獲得西班牙國家翻譯獎,獲此殊榮的當時,馬利亞斯年僅二十八歲。
馬利亞斯英文造詣極佳,曾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美國衛斯理學院以及西班牙馬德里大學。雖然在學術界頗受敬重,但才子不耐學術圈的枯燥、僵化,一九九四年竟婉拒出任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卻加入甫成立的國際作家協會。不過,馬利亞斯二○○六年再獲提名,這一回他終於點頭,皇家學院終於如願網羅了這位傑出而耀眼的院士。
回憶,一首弔詭歌謠
《如此蒼白的心》第一人稱的主述者是個國際會議的專業口譯,剛剛從哈瓦那度完蜜月回到馬德里家中,正值新婚的他,就從父親當年的新婚慘劇開始聊起,由此帶出生命中不同階段的私密,當然也包括專業領域的私密。焦慮,則是主述者並不自知的私密。哈瓦那蜜月期間在下榻旅館聽見隔壁房裡傳來的對話,牽扯出他不願面對(或不願知曉)的家族私密,焦慮,在記憶的角落肆無忌憚地蔓延著…。傾聽,非常危險的動作,聽見了秘密,尤其是沉重的負擔;許多時候,我們選擇(或希望)「寧可不知道」,就像小說裡裡的主述者一樣,然而,我們總是忍不住拉長了耳朶傾聽所有的聲響和對話,更糟糕的是,我們通常會以自己的邏輯去解讀。
風動?幡動?到頭來是自己的心思莫名所以的攪動。
而且,人心比我們想像的更執著。有時候,不管我們願不願意,「聽到了,就記得了,從此難忘。」童年時期不經意從外祖母口中聽到的古巴歌謠,就這樣烙印在記憶裡,而且別無選擇。回憶,看似如此遙遠,但隨時可以近在咫尺。而且,可能銳利如刀鋒…。
文字,揪出千思萬緒
《如此蒼白的心》沒有高潮迭起,亦無香豔刺激。我說的是實話(至少我是這麼認為),但你如果就這樣略過這本小說,那你就被騙了(不是我騙你,而是你的邏輯騙了你)。
馬利亞斯駕馭文字的天份異常驚人,許多書評家認為,數十年來的西語文壇無人能出其右。《如此蒼白的心》一行行文字敘述,看來平靜無波,實則驚心動魄;字裡行間隱匿著充滿爆發力的意象,彷彿時有一張張鬼臉探出頭來,或捉弄你,或驚嚇你。許多生命的苦悶和無奈,就像遊魂似的在文句間飄蕩著。好長好長的句子──句點遙遙無期,逗點數不勝數,破折號和括弧讓讀者的思緒不時在蜿蜒曲徑中跋涉著……馬利亞斯有個教人讚嘆的本事,他的標點經常擺在出人意表的位置,由此營造出超凡的文字趣味,讓人讀著就忘了句子很長那回事。
《如此蒼白的心》主角是誰?擔任口譯的主述者?作者本人?還是電動遊戲般令人眼花撩亂的語言文字?讓你揪心是針針見血的剖析婚姻?還是奇詭扭曲的口譯生態和美術品交易?《如此蒼白的心》就像一長排的稜鏡,映出了各種人生風景,或許,你會在其中看見自己過往的海市蜃樓。
二○○八年十二月
奧地利薩爾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