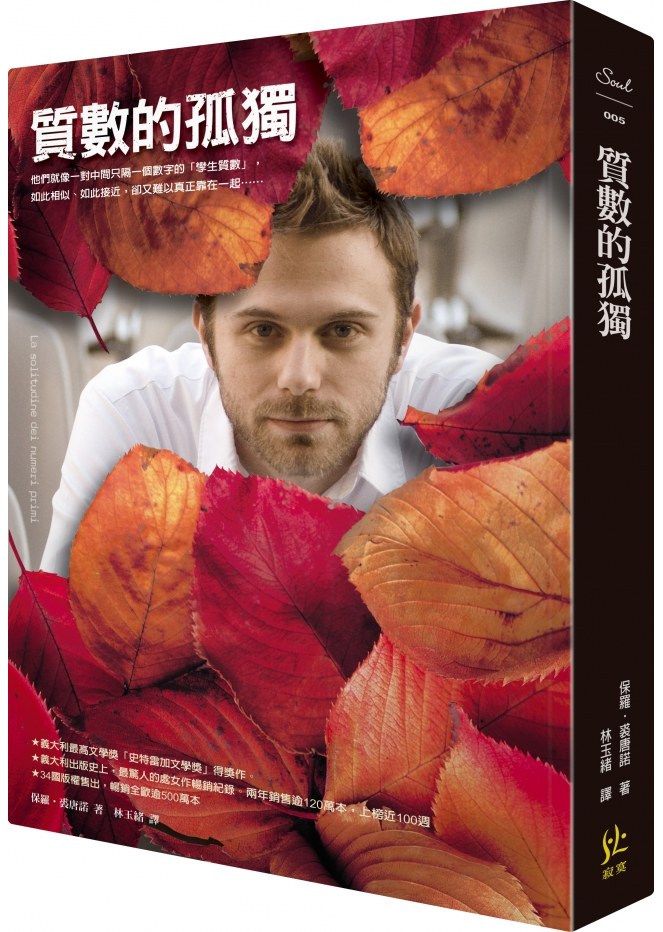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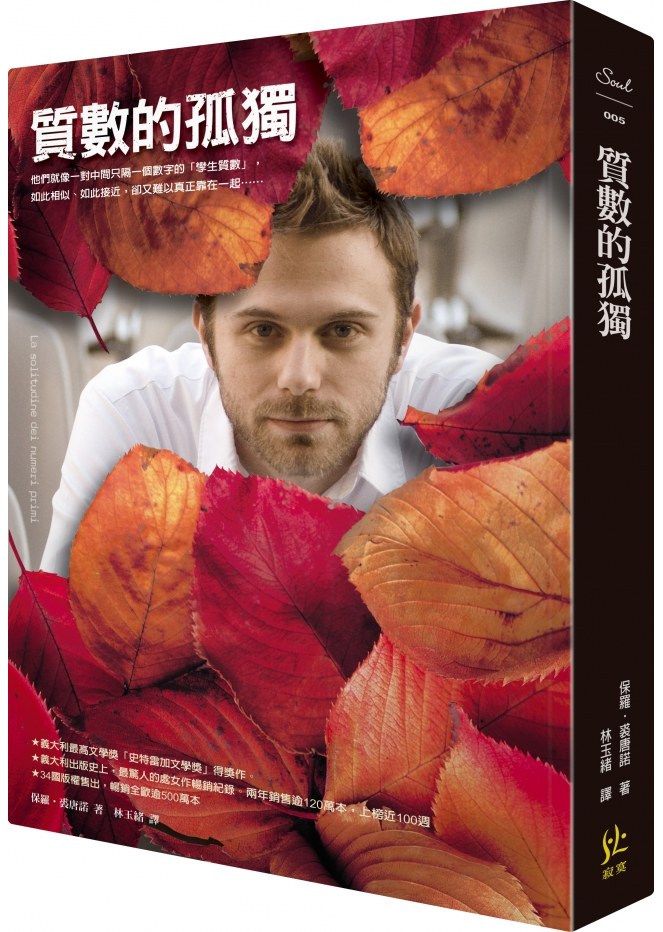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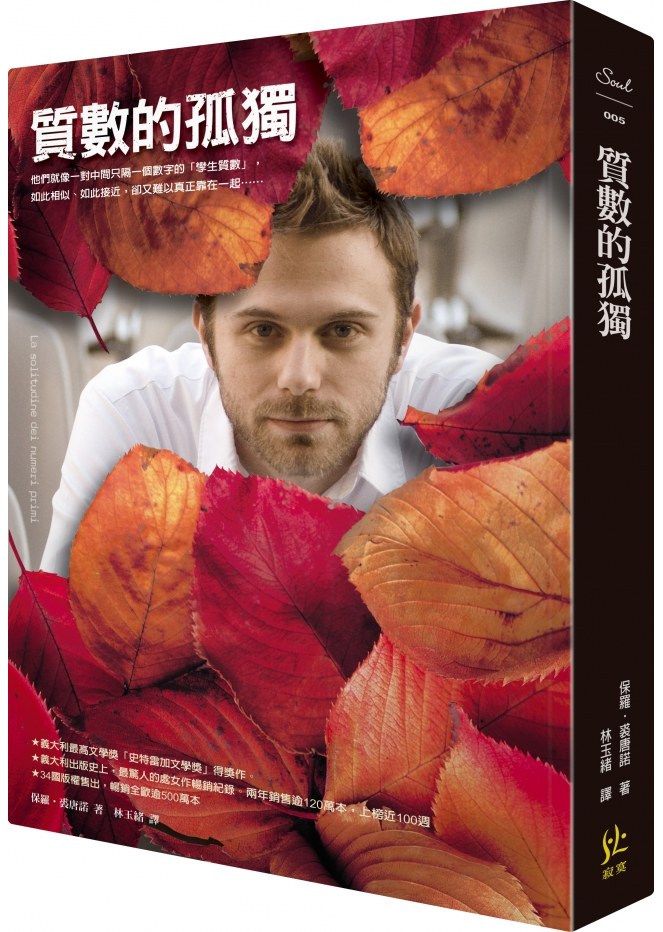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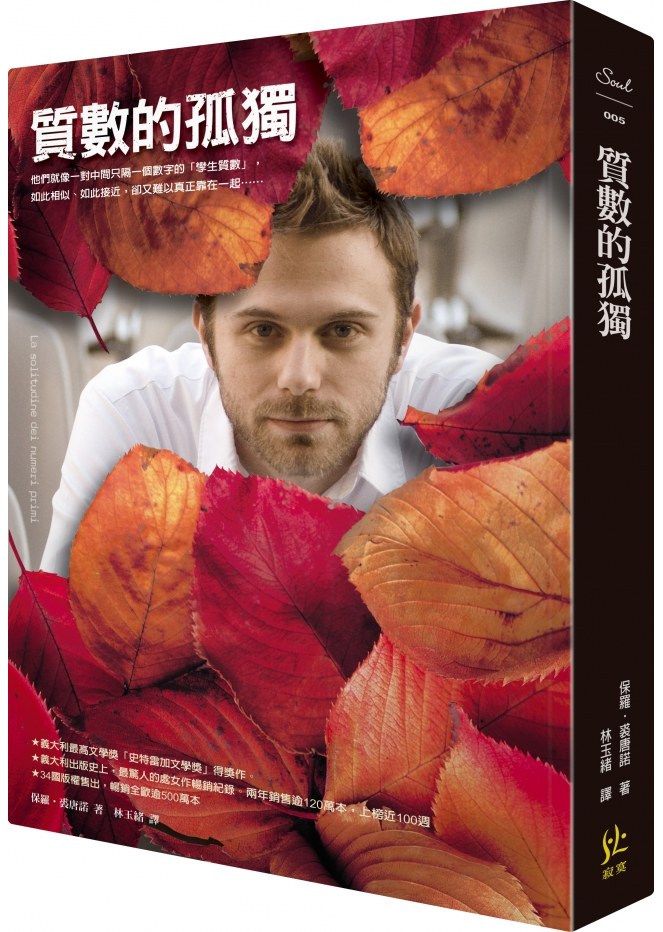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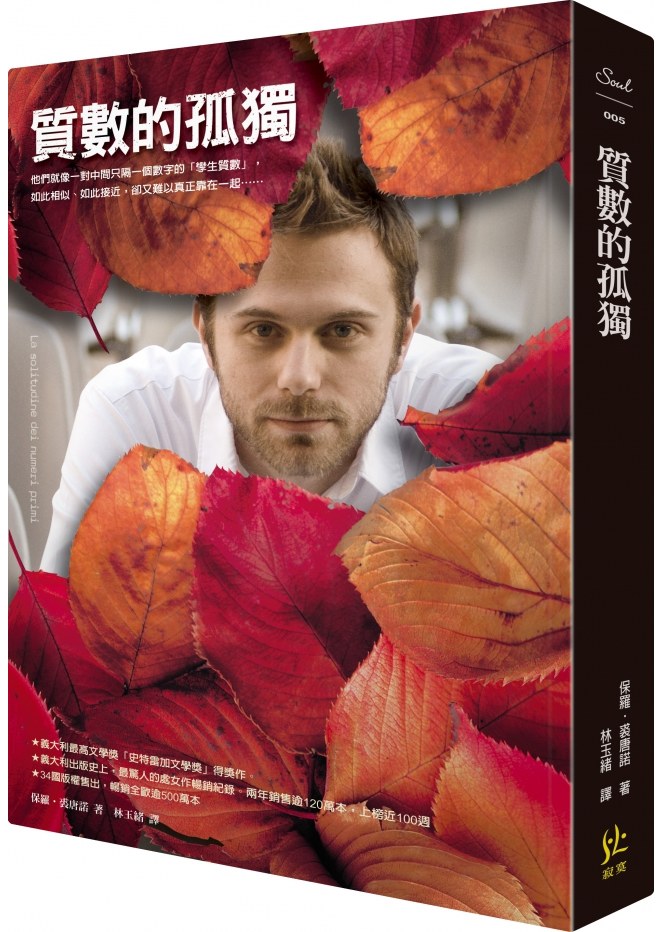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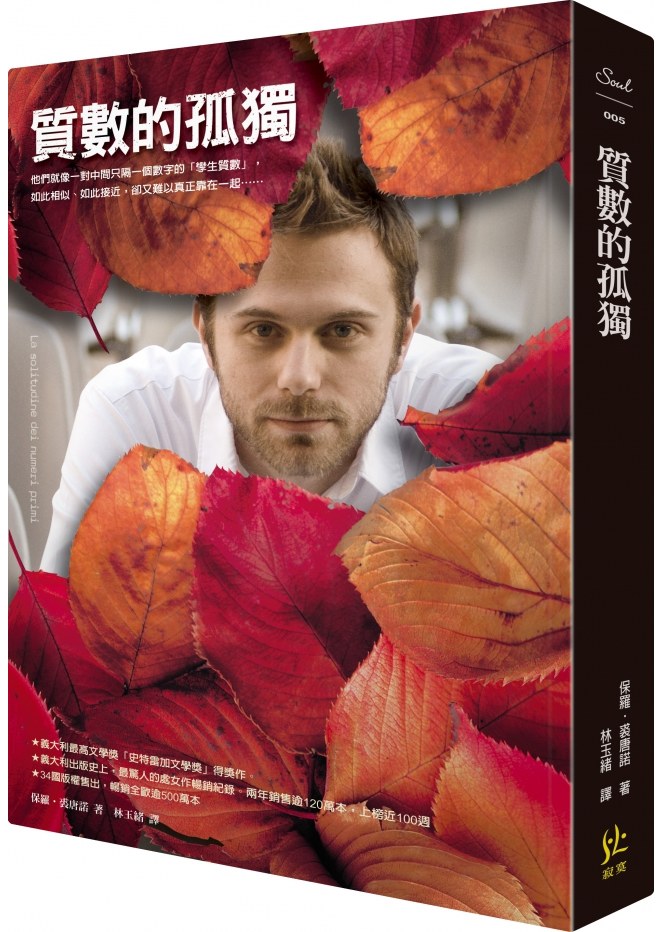
內容簡介
★2010 博客來Top50,翻譯文學類Top15。
金石堂文學類Top50。
誠品No.16,翻譯文學類No.6。
國中暑假推薦書單
「哪樣比較孤獨?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誰也不愛;還是心裡愛著一個人,卻始終無法向愛靠近?」
☆ 誠品蟬連數月Top10、金石堂博客來暢銷榜
☆義大利出版史上,最驚人的處女作暢銷紀錄。兩年銷售逾120萬本,上榜近100週
☆ 34國版權售出,暢銷全歐逾500萬本,在西班牙成為唯一超越《龍紋身的女孩》與《暮光之城》的小說
☆ 義大利最高文學獎「史特雷加文學獎」得獎作
☆ 於義大利掀起三十世代讀者的迷戀狂潮,書迷們甚至在城市各角落塗鴉書中佳句。
☆ 《聽說》電影導演╱鄭芬芬、名主持人╱蔡康永、旅歐作家╱韓良憶、作家╱彭樹君、作家╱鍾文音、作家╱郝譽翔 ◎驚豔推薦
★ 這是一部精緻、同時卻又非常可怕的傑作。 ──義大利IBS網路書店
他們就像一對中間只隔一個數字的「孿生質數」,如此相似、如此接近,卻又永遠無法真正靠在一起……
兩個質數,代表兩個不幸的小孩、兩個孤獨的青少年、兩個脆弱的大人。
艾莉契討厭滑雪,卻在父親的逼迫下不得不去上滑雪課,因此遭逢了生命中最大的意外。
馬提亞有一個智能不足的雙胞胎妹妹,父母卻總是硬將他們綁在一起。當終於有同學願意邀請他們去參加生日餐會的那天,馬提亞做出了讓他一生懊悔的抉擇。
兩個人生曾經面臨缺憾的青少年,在另外一場生日會上相遇了……他們如此相像,卻又如此不同;如此接近,卻又難以真實碰觸,像兩個「孿生質數」,緊密卻又非獨自存在不可。他們,究竟會面對怎樣的未來?
這是個關於童年經驗、孤單與愛的動人故事。看完之後你會想問:當你愛上另一個人時,是否還能保有自己的完整性?為何越是相愛的人,卻越是無法彼此靠近?
26歲便和安伯托.艾可同樣榮獲義大利最高文學獎的裘唐諾知道,生命,是由殘缺不全卻極為珍貴的片段所組成的。而這一切的不完美,讓我們不得不陷落在整個故事中無法自拔。
作者介紹
保羅‧裘唐諾(Paolo Giordano)
生於1982年,目前正在攻讀粒子物理學博士學位。2008年1月於義大利出版處女作《質數的孤獨》,兩年內售出逾34國版權,全歐暢銷逾500萬冊,贏得五座文學獎,包括義大利最重要的史特雷加文學獎,成為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主。得過該獎項的都是義大利重量級小說家,包括安伯托.艾可、《週期表》作者普利摩‧李維等人。
◆ 譯者簡介 / 林玉緒
政大統計系畢。七年半的公務員生涯之後,辭職前往義大利中部語言大學就讀,選修文化組;之後,又考上翡冷翠大學,選讀義大利近代文學。旅居義大利近九年。曾為特約記者,現為自由文字工作者。
規格
ISBN:9789868461468
頁數:312,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789868461468
試閱
阿基米德定律╱1984年
2
這對雙胞胎還小的時候,米格拉就是其中比較會闖禍的一個,像是坐在學步車裡直接衝下樓梯,或是把一顆青豆仁塞進鼻孔裡,然後就得把她送到急診處,用專門的鑷子夾出來。他們的父親總是對先出生的馬提亞說,媽媽的子宮太小,裝不下他們兩個。
「天知道你們在媽媽肚子裡是怎麼胡鬧的,」他說,「我猜你一定曾經用力踢你妹妹,對她造成一些嚴重的傷害。」
然後父親就笑了,即使沒有什麼好笑的地方。他把米格拉高舉到空中,然後將她軟軟的臉頰深深埋入自己濃密的鬍子裡。
馬提亞從底下看著這一幕,也跟著笑,他並沒有真正了解爸爸這些話的含義,只是任由它們滲透到自己的內心裡。他讓這些話留存在胃的底部,形成厚厚黏黏的一層,就像那些陳年葡萄酒所產生的沉澱物一樣。
當米格拉二十七個月大了,還無法說出一個完整的字的時候,爸爸原本的大笑變成了一種勉強的微笑。她甚至連「媽媽」、「大大」、「睡覺覺」或「汪汪」都不會說。她那些含糊不清的喊叫聲,彷彿來自一個非常孤獨又荒涼的地方,每一次都讓父親聽了不寒而慄。
米格拉五歲半的時候,一位戴著厚眼鏡的語言專家在她面前放了一個三夾板做成的立方體,上面挖出了星形、圓形、正方形和三角形四種不同形狀的洞,還有一些與這些洞形狀一致、用來塞進這些洞裡的彩色玩具。
米格拉驚訝地盯著這個東西。
「星星要擺到哪裡呢,米格拉?」語言專家問道。
米格拉往下看著那些玩具,卻什麼也沒碰。醫生把星星放到她手裡。
「這個東西要放在哪裡呢,米格拉?」她問。
米格拉茫然地四處張望,接著把那個黃色五角星星其中的一個尖角塞進嘴巴裡,開始咬了起來。語言專家把她的手從口中拉出來,又重複問了第三次。
「天呀!米格拉,照醫生的話去做!」她的父親咆哮道,他再也忍不住了,無法再待在人家要他坐著的位子上。
「巴羅西諾先生,拜託您。」醫生用安撫的聲音說,「小孩子們需要多一點時間慢慢來。」
米格拉用了她的時間,整整一分鐘之久。然後她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這可能是非常高興、也可能是非常絕望的聲音,她堅定地把星星放到正方形的洞裡。
彷彿惟恐馬提亞還不明白他的妹妹不正常似的,他的同班同學總是毫不遲疑地替他點明。就拿席蒙娜‧瓦特拉為例,一年級時,老師跟她說:「席蒙娜,這個月妳坐到米格拉旁邊。」她馬上反對,手臂交叉胸前,並且回答:「我不要坐在那個人旁邊。」
馬提亞任憑席蒙娜和老師吵了一會兒,然後才跟老師說:「我可以和米格拉坐在一起。」這時大家全都鬆了一口氣,包括那個人、席蒙娜和老師。每個人都是,除了馬提亞之外。
這對雙胞胎坐在第一排。米格拉整天都在印好的圖案上著色,小心翼翼地不塗到線條外面,並且任意選擇顏色。所以圖中的小朋友皮膚是藍色的,天空是紅色的,而樹木全是黃色的。她像握著一支肉鎚一樣緊抓住鉛筆,用力地在紙上塗著,幾乎一次要撕裂三張紙。
坐在她旁邊的馬提亞,則是學習著讀和寫。他學會了數學的四則運算,而且是班上第一個學會做進位長除法的學生。他的頭腦就像是一具完美又精確的齒輪裝置,如同他妹妹那個如此殘缺的頭腦一般令人費解。
到了小學三年級,這對雙胞胎還沒有受到班上任何同學的邀請,去參加他們的生日會。媽媽察覺到了,於是想到可以替雙胞胎安排一場生日慶祝會,來解決這個問題。在餐桌上,巴羅西諾先生否決了這個提議,他說:「阿德蕾,看在老天的分上,現在這樣已經夠尷尬了!」馬提亞鬆了一口氣,而米格拉則是第十次弄掉了她的叉子。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
然後,在一月的某一天早上,那個有著一頭紅髮、嘴唇厚得像狒狒的男孩里卡多‧佩羅帝,走近馬提亞的座位。
「喂,我媽媽說你可以來參加我的生日會。」他一口氣說完,眼睛望向黑板。
「還有她。」他指指米格拉,又加上這一句。她正小心翼翼地撫平桌面,好像那是一張床單似的。
馬提亞的臉因激動而發麻。他連忙回答說謝謝,但如釋重負的里卡多,早就走開了。
雙胞胎的母親馬上就興奮起來,帶著兩個小孩到班尼頓去買新衣服。他們逛了三家玩具店,但是每一次阿德蕾都無法做出決定。
「里卡多有什麼興趣?這個他會喜歡嗎?」她問馬提亞,一邊打量著一盒一千五百片的拼圖。
「我怎麼知道?」她兒子回答。
「無論如何,他是你的朋友啊!你應該很清楚他喜歡什麼樣的玩具。」
馬提亞並不認為里卡多是他的朋友,這件事他無法向母親解釋。他只是聳聳肩。
最後阿德蕾決定買一個樂高的宇宙飛船,那是玩具部門最大也最貴的商品。
「媽媽,那太大了啦!」兒子抗議道。
「胡說!而且你們是兩個人,你們不想給人留下壞印象吧!」
馬提亞非常清楚,不管有沒有樂高玩具,他們一定會給人留下壞印象的。和米格拉在一起,根本不可能扭轉印象。他知道里卡多會邀請他們去參加生日會,只因為那是他媽媽強迫他這麼做的。到時候米格拉一定會一直黏著他,還會把橘子汁打翻在身上,然後開始啜泣,就像平常她累的時候那樣。
馬提亞第一次認為待在家裡可能會好一點。
或者應該說,他覺得最好是把米格拉留在家裡。
「媽媽,」他猶豫地開口說。
阿德蕾正在皮包內找錢包。
「什麼事?」
馬提亞吸了一口氣。
「米格拉一定得去生日會嗎?」
阿德蕾突然僵住不動,直盯著兒子的眼睛。收銀員事不關己地看著這一幕,一隻手伸在輸送帶上方等著收錢;米格拉則正在把展示架上的糖果盒亂放一通。
馬提亞兩頰通紅,心裡已準備好要挨一記耳光,但卻沒有發生。
「她當然要去。」他的母親只說了這麼一句,問題就結束了。
到里卡多家的路上,馬提亞的思緒被樂高玩具的組合小方塊所發出的沙沙聲不停打斷,它們在有著小把手可提的紙盒中晃來晃去,撞擊著紙板。米格拉則走在他背後幾公尺的地方,搖搖晃晃地試著跟上他的腳步,小腳在那些黏在柏油路面上的落葉爛泥裡拖行著。空氣沉滯而寒冷。
她一定會把洋芋片灑滿一地的,馬提亞這麼想。
她一定會抓住球,而且不會把球交還給任何人,就像在學校一樣,馬提亞想著。
他看著他的雙胞胎妹妹,她有著和自己一模一樣的眼睛、鼻子、同樣顏色的頭髮,卻有一顆應該丟掉的腦袋。這是他第一次真正感覺到恨意。他牽著妹妹的手一起過馬路,因為那裡車子開得很快。就在穿越馬路的同時,他腦中浮現了一個想法。
他放開妹妹那隻戴著毛手套的小手,緊接著又想:這麼做是不對的!
然後,當他們沿著公園走的時候,他的想法又變了,他說服自己沒有人會發現的。
只不過幾個鐘頭而已,他想。而且只此一次。
他猛然改變方向,抓住後方米格拉的手臂,走進公園。那片綠地上的草皮由於前一晚結霜,所以還很潮濕。米格拉在他背後小跑步地跟著,她那雙全新的白色麂皮小靴被汙泥弄得髒兮兮。
公園裡一個人也沒有,這麼冷的天氣,沒有人會想來此散步的。這對雙胞胎來到樹木林立的區域,那裡架設了三張木桌和一具烤肉架。
「米奇,聽好,」馬提亞說,「妳有在聽我說話嗎?」
和米格拉說話,必須要時時確定她那條窄窄的溝通管道是打開的。馬提亞等妹妹點了一下頭。
「很好。那麼,我現在要離開一下下,好嗎?不過我不會離開很久,只有半個鐘頭而已。」他解釋著。
他根本毋須說實話,因為對米格拉而言,半個鐘頭或是一整天,差別並不大。醫生曾經說過,她對時空概念的發展狀況停留在前意識的階段,而馬提亞非常清楚那是什麼意思。
「妳坐在這裡等我。」他對雙胞胎妹妹說。
米格拉認真地看著哥哥,什麼也沒回答,因為她根本不會回答。她完全沒有表現出真正了解的樣子,不過她的眼睛有一度亮了起來。之後終其一生,馬提亞想起那個眼神時,都會想到恐懼。
他走離開妹妹幾步,面向著她倒退著走,以確定她沒有跟上來。「只有蝦子才會這樣走路!」有一次媽媽就是這樣吼他的,而他總是在撞到某樣東西時才會停下來。
大約走了十五公尺左右,米格拉就已經不再看他了,轉而全神貫注地想要拔掉毛衣外套上的一顆鈕釦。
馬提亞轉身,開始快跑,手裡緊抓著裝有禮物的袋子。紙盒裡兩百多個塑膠小方塊互相碰撞著,似乎想要說些什麼。
「你好,馬提亞!」里卡多的媽媽開門歡迎他,「你妹妹呢?」
「她有點發燒。」馬提亞撒謊道。
「喔,真可惜。」這位太太說道,然而卻一點也看不出遺憾的樣子。她往旁邊跨了一步好讓馬提亞進去。
「里奇,你的朋友馬提亞來了,過來和人家打招呼!」她轉過身去對著走廊的方向喊道。
里卡多滑著地板走出來,表情不太高興。他站了一秒鐘看看馬提亞,並尋找那個弱智女孩的蹤影。然後他鬆了一口氣,說了聲:「嗨。」
馬提亞把裝著禮物的袋子舉到那位太太的鼻子底下。
「這個要放在哪裡?」他問。
「那是什麼?」里卡多懷疑地問道。
「樂高玩具。」
「啊!」
里卡多一把抓去那個袋子,消失在走廊裡。
「和他一起去吧!」這位太太說,同時推著馬提亞走,「生日會在那裡。」
佩羅帝家的客廳裝飾著一串串氣球,鋪著紅色紙桌巾的餐桌上,擺著許多盆爆米花和洋芋片、烤盤上有一大片切成許多四方塊的乾披薩,還有一排尚未打開、各種顏色的氣泡飲料。馬提亞班上的幾位同學已經到了,他們站在房間的中央,看守著那一桌食物。
馬提亞朝那些人走了幾步,然後在距離兩公尺的地方停了下來,好像一顆不想占據天空太多位置的人造衛星。沒有人注意到他。
當這個房間擠滿了小朋友的時候,一個大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戴著紅色的塑膠鼻子和一頂小丑的高頂禮帽,帶領他們玩起蒙住眼睛去找驢尾巴的遊戲,它的規則是把你的眼睛蒙起來,然後你必須把一條尾巴貼在紙上一隻沒有尾巴的驢子上。
接著,當外面的天色暗下來之後,做小丑打扮的年輕人關掉電燈,教大家圍成圓圈坐下來,開始說一個鬼故事。他還在下巴處舉著一個手電筒打燈。
馬提亞覺得那個故事並不怎麼嚇人,反倒是用那種方法把燈光打在臉上還比較可怕。光線從底下往上照,讓那張臉變得紅紅的,還顯現出一些令人害怕的陰影。馬提亞望著窗外好讓目光避開那個小丑,他還想起了米格拉。其實他沒有一刻忘記她,不過這時他才第一次想到她獨自一人還在樹林中等著他,可能正用戴著白色手套的小手摩擦著小臉,好讓自己溫暖一點。
里卡多的媽媽捧著插滿點燃蠟燭的蛋糕走進這間沒有點燈的房間,每個人都鼓起掌來,一半是因為那個鬼故事、一半是因為這個大蛋糕。就在這個時候,馬提亞忽然站了起來。
「我必須走了。」他說道,甚至不等她將蛋糕擺到桌子上。
「現在嗎?可是要吃蛋糕了耶!」
「是的,就是現在,我必須回去了。」
里卡多的媽媽從蠟燭上望著他,在那種光線照射之下,連她的臉也充滿駭人的陰影。其餘受邀的小朋友全都安靜下來。
「好吧,」這位女士猶豫地說,「里奇,送你的朋友出去。」
「可是我得吹蠟燭呀!」壽星抗議著說。
「照我的話去做!」他母親命令他,目光卻沒有離開馬提亞。
「馬提亞,你很討厭耶!」
有些小朋友開始笑出來。馬提亞跟著里卡多走到大門口,從一堆外套底下拿出自己的大衣,然後說了謝謝與再見。里卡多什麼也沒回答,很快地在馬提亞身後關上大門,就衝回他的蛋糕那裡去了。
從里卡多家公寓的中庭,馬提亞回頭看了那扇亮著燈的窗戶一眼,同學們被阻隔的歡呼聲從窗子的縫隙傳到他耳中,聽起來就像媽媽晚上將他和米格拉送上床睡覺以後,客廳電視機所傳來令人心安的嗡嗡聲。鐵柵欄門在他身後「喀拉」一聲關上後,他開始跑了起來。
他進入公園,但只走了十幾步,路燈微弱的光線就令他無法辨識出那條鋪著鵝卵石的小路。他留下米格拉的那片樹林,只見光禿禿的樹枝在漆黑夜空中呈現出略暗的塗鴉陰影。即使從這麼遠的地方看過去,馬提亞心中已充滿一種清楚又無法解釋的確定感──他妹妹已經不在那裡了。
他在離長條椅只有幾公尺的地方停了下來,幾個鐘頭之前米格拉還坐在那裡,忙著弄壞自己的外套。他站著不動,側耳傾聽,直到重新恢復呼吸,並期待著妹妹會在某個時刻突然間從樹後面跳出來嚇他,然後歪歪扭扭地朝他跑過來。
馬提亞呼喊著米格拉,卻被自己的聲音嚇到。他降低聲音再次叫她,一邊走近那些木桌子,把一隻手放在米格拉曾經坐著的地方,感覺就像其他東西一樣冰冷。
她可能是覺得很無聊,回家去了,他想。
可是如果她不曉得回家的路呢?而且她自己一個人也不會過馬路。
馬提亞看著眼前這片已陷入黑暗之中的公園。他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他不想繼續往前走,但是他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他踮著腳尖走路,不想把腳底下的落葉踩得沙沙響。他不斷地左右轉頭張望,希望能發現米格拉蹲在某棵樹後,準備偷襲一隻甲蟲或什麼其他的怪東西。
他找到走回小徑的路,現在只是一條由來此散步的家庭在土堆上所踏出的一條痕跡而已。他順著小路走了整整十分鐘,直到不知自己身在何方。這時他開始哭了起來,同時還咳個不停。
「米奇,妳真是個傻瓜!」他輕聲地說,「一個弱智的傻瓜!媽媽跟妳解釋過幾千次了,要是迷路的時候就留在原地呀……可是妳什麼都不懂……一點都不懂!」
他爬上一座小斜坡,發現自己正面對著那條把公園分成兩部分的河流。父親曾告訴過他這條河的名字很多次,但馬提亞就是記不起來。河水反射著不知從何處傳來的光源,在他充滿淚水的眼睛裡似乎不停顫抖著。
他走近河岸,感覺米格拉應該來過這裡,因為她喜歡水。媽媽總是告訴他,他們小時候兩個一起洗澡時,米格拉總是像個瘋子似地大聲尖叫,因為她不想起來,即使水都變冷了也一樣。有一個週日,父親帶他們到河邊,可能正是現在他所站的地方,教他如何用扁平的石頭打水漂。就在爸爸跟他示範如何利用手腕的力量讓石頭旋轉的時候,米格拉已經傾身向前,掉進水深及腰的河裡,剛好被父親及時拉住手臂。爸爸摑了她一記耳光,米格拉就開始哭泣,然後三個人不發一語,拉長著臉回到家。
米格拉拿著一根小樹枝去撥弄自己映在水面上的倒影,然後像一袋馬鈴薯般地滾進河裡的影像,如一道強烈的電流般閃過馬提亞的腦海。
他在距離河邊約半公尺的地方坐了下來,感覺筋疲力竭。他轉頭看向自己身後,望著這股還要持續好幾個鐘頭的黑暗。
他開始盯著河流黑色水面上的微微閃光,又試著想記起它的名字,但還是一樣想不起來。他把手插進冰冷的土中,河畔的水氣讓土壤變得柔軟。他發現一塊瓶子的碎片,那是某個狂歡夜所遺留下來的尖銳物品。當他第一次把它刺進手裡的時候,並不覺得痛,或許他根本沒有察覺到。接著他開始把玻璃碎片往肉裡旋轉,讓它插得更深,但他的目光沒有離開河水。他等待著米格拉可能會在某一刻浮出水面,同時納悶著為什麼有些東西會浮起來,有些東西卻不會。
7
隔天十點鐘下課時,她們就在學校裡到處繞,要為艾莉契找個男朋友。薇歐拉驅走佳達和其他幾個夥伴,說她和艾莉契有事要辦,然後她們就眼睜睜地看著薇歐拉和她的新朋友手牽手地走出教室。
她已經安排好一切,事情在她下週六的生日會中應該會成功,只要找到那個對的男孩。她們走過走廊,薇歐拉指著這個男生或另一個男生,對艾莉契說看看他的屁股,長得還不賴,他一定會做「那件事」。
艾莉契緊張地笑著,不知道如何做決定。她在腦海中清楚又不安地想像著當一名男孩把手伸進她毛衣底下的那一刻,這個男孩將會發現,在那些把她的身體遮掩得如此完美的衣服底下,只有一堆肥肉和鬆弛的肌膚。
現在她們正倚在三樓那道防火梯的欄杆上,看著那些在中庭踢足球的男生,不過那顆黃色的球似乎快沒氣了。
「特利維羅怎樣?」薇歐拉問她。
「我不曉得他是誰。」
「妳竟然不知道他是誰?他現在念五年級,曾和我姊姊一起划過船。大家說了許多關於他的趣事。」
「什麼趣事?」
薇歐拉比了一個手勢,表示「那個東西」的長度,然後大笑起來,享受著自己這種暗示所帶給別人的不安感。艾莉契羞怯得面紅耳赤,同時驚訝又確定地感覺到,她的孤獨歲月真的結束了。
她們下到一樓,經過點心與飲料的販賣機前。學生們凌亂地排成一條隊伍,有些人還把牛仔褲口袋裡的錢幣弄得叮噹響。
「總之,妳必須做出決定。」薇歐拉說。
艾莉契用腳跟轉了一圈,漫無目的地看著周遭。
「那邊那個男生,看來不錯。」她說,同時指著遠處兩個靠在窗戶旁的男孩。那兩個人站得很近,但沒有講話,也沒有看著對方。
「哪一個?」薇歐拉問,「那個包著繃帶的?還是另外一個?」
「包著繃帶的那個。」
薇歐拉看著她,那雙閃閃發亮的眼睛睜大得像兩片汪洋。
「妳瘋了!」她說,「妳知道那個男生做了什麼嗎?」
艾莉契搖搖頭。
「他用一把刀刺進自己手裡,而且是故意的,就在學校裡面。」
艾莉契聳聳肩。
「我倒覺得很有意思。」她說。
「有意思?根本是心理變態!和這種人在一起,妳會被切成一塊塊地,放在冰櫃裡。」
艾莉契笑笑,卻繼續看著那個手上包著繃帶的男生。在他那種把頭垂得低低的姿態中,隱含著某種孤單,讓她好想走過去,抬起他的下巴,然後告訴他:「看著我,我在這裡!」
「妳真的確定?」薇歐拉問她。
「對!」艾莉契回答。
薇歐拉聳聳肩。
「好吧,我們走!」她說。
她牽起艾莉契的手,拉著她向那兩個站在窗戶邊的男生走過去。
在皮膚之上與皮膚之下╱1991年
15
馬提亞和艾莉契在很多年以後才知道這件事,反倒是其他人先察覺到了。他們手牽著手走進客廳,臉上並沒有笑容,而且目光還看著不同的方向,但是透過手臂與手指的接觸,他們的身體卻似乎不斷地彼此牽動著。
這兩個人的外觀有明顯的對比:艾莉契有一頭金髮,柔順地服貼在非常蒼白的臉龐兩側;馬提亞則是一頭黑髮,蓬鬆地散落在前額上,遮住了那雙黑眼睛,看起來就像是消失在那道細長的眉骨所形成的眼窩裡。不過他們之間有一塊共有的空間,這塊空間的界線沒有清楚的劃分,在那裡似乎什麼都不缺,而且空氣似乎是停滯的、不受干擾的。
艾莉契走在馬提亞前面約一步的距離,輕輕地拉著馬提亞的舉動,平衡了她那不穩的步伐,並抹去了她那條有缺陷的腿的不完美。馬提亞則任由自己被人牽著走,那雙腳踩在地磚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響;他的疤痕在她的手中被隱藏得很好。
他們在廚房門口停了下來,離那群女生和丹尼斯有點距離,想要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兩個人臉上有一種夢幻般的神情,彷彿他們來自一個只有他們倆才知道的遙遠地方。
他看著馬提亞,想在對方的表情中搜尋他一直害怕的那件事的蛛絲馬跡,他覺得馬提亞一定和艾莉契說了些什麼,而這些話他永遠也無法知道。想到這裡,他體內的血液整個衝上腦門。
他跑到廚房外面,肩膀故意去撞馬提亞,想要破壞那兩人之間那種令他痛恨的平衡。有一瞬間,馬提亞的目光和丹尼斯那雙又紅又慌亂的眼神交會,不知為何,這讓他想起了那天下午在公園裡米格拉那雙無助的眼睛。這些年來,那雙眼睛早已在他的記憶深處化成了一種單一的、無法抹滅的恐懼。
他放開艾莉契的手,然而他的神經末梢似乎全都集中在那個點上,當他與那個點分離時,他覺得自己的手臂彷彿迸出了火花,好像被剝除了防護圈的電纜。
「對不起!」他低聲說道,然後離開廚房去追丹尼斯。
在水面載浮載沉╱1998年
21
質數只能被一和本身整除。它們在自然數的無盡序列中,乖乖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跟其他數字一樣擠在另外兩個數字之間,但彼此的距離又比其他數字更遠一步。這些懸疑又孤獨的數字,讓馬提亞覺得非常神奇。有時候他認為它們是被錯置在那個序列當中,就像被困在一條項鍊中的小珍珠;有些時候,他則懷疑這些質數其實也很希望跟其他數字一樣,當個普通的數字,但卻由於某種原因,它們沒有這個能力。第二種想法經常會在夜晚浮現,當他的內心太軟弱而無法對自己說謊時,這種想法就會混亂地穿插在睡前的胡思亂想之間。
在大學的第一年,馬提亞發現在質數當中還有一些更特別的數字,數學家稱之為「孿生質數」。它們是一對彼此非常接近的質數,幾乎是緊緊相鄰,但它們之間總是會存在著一個偶數,讓它們無法真正地碰在一起,例如十一和十三、十七和十九、四十一和四十三這些數字。如果有耐性地一直數下去,將會發現這種孿生質數變得越來越少見,越來越常碰到的是孤立的質數,迷失在全是由數字所組成的安靜、整齊的空間裡。接著你會很痛苦地意識到,孿生質數一直要等到意外事件發生的時候才會碰在一起,而他們真正的宿命是註定一輩子孤獨。然後,當你正準備要放棄、不想再繼續算下去的時候,卻又碰上了另外一對孿生質數,它們緊緊地抓住對方。於是在數學家之間有一種共同的信念,就是盡量地往前數,總是會遇上另外一對孿生質數,雖然沒有人知道它們何時會出現,但一定會碰到的。
馬提亞認為他和艾莉契就是如此,他們就是一對「孿生質數」,既孤獨又迷惘,彼此非常接近,卻又不夠近到能夠真正地碰觸到對方。他不曾對她說過這件事。當他想像對她告白這些事情時,他手上一層薄薄的汗水就會完全蒸發,接著就會有整整十分鐘的時間,他無法去碰觸任何東西。
冬季的某一天,他在她家度過整個下午之後,剛剛回到家。在她家的時候他們什麼事也沒做,只是把電視的頻道轉來轉去。馬提亞沒有去注意電視裡的話語和影像。艾莉契的右腳放在客廳的茶几上,入侵到他的視線範圍裡,像一條毒蛇的頭似地從左邊鑽進來。艾莉契用一種催眠的規律不斷地伸直又彎曲腳趾頭,那重複的動作讓他的胃裡產生一種堅硬又不安的感覺,他只能掙扎著盡可能把目光放在最遠的地方,如此視覺範圍裡的東西才不會改變。
回到家裡,他從活頁夾裡拿出一疊空白紙張,厚度足以讓筆在紙上輕輕地書寫,而不會刮到堅硬的桌面。他用手把這疊白紙的四邊靠整齊,首先是上下、然後是左右兩側。他挑了書桌上墨水最多的那枝筆,打開筆蓋,把它套在尾端,免得弄丟了。然後連紙張的面積都毋須計算,就精確地從它的正中央開始寫起東西來。
二七六○八八九九六六六四九。他把筆蓋蓋上,擺在紙張的旁邊。「兩兆七千六百零八億八千九百九十六萬六千六百四十九!」他大聲地念出來。然後又小聲地再念一遍,好像要讓自己把這個「繞口令」念得更順一點。他決定把這個數字當成自己的。他很確定在這個世界上、甚至是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人曾經停下來仔細思考過這個數字。很可能直到這個時候為止,沒有任何人曾在一張紙上寫下這個數字,更別說是大聲地念出來了。
在遲疑了一會兒之後,他在下面隔了兩行的地方寫下二七六○八八九九六六六五一。這是她的數字,他心想。在他腦海裡,這個數字呈現的是艾莉契腳丫子的青灰色,在電視機的藍色閃光前形成明顯的輪廓。
它們也可能是兩個孿生的質數,馬提亞如此想過。如果它們真是孿生質數的話……
殘餘╱2007年
40
艾莉契走進聖母救助醫院的中庭,並沒有回想起她和法比歐曾在同一條小徑上散步的情景。她覺得自己像一個沒有過去的人,彷彿置身在那個地方,卻不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她好累,是一種唯有空虛能帶來的疲累。
她緊握著扶手爬上階梯,停在門口。她只想走到那裡,讓醫院這個部門的自動門打開,等個幾分鐘,讓她有足夠的時間恢復體力,然後離開。這是為「機會」增加一點小小助力的方法,她也只能這樣,出現在法比歐工作的地方,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她不會照著克羅札的話去做,她不會聽從任何人,她甚至也不會對自己承認,她真的希望能找到他。
結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自動門打開了,當艾莉契往後跨一步,門又重新關上。
「妳在期待什麼呢?」她自問。
她想要坐在那裡一會兒,希望他會經過。她的身體在對她做出要求,每一根神經都在對她呼喊,但是她不想聽。
當她再次聽到大門電流啟動的沙沙聲時,正要轉過頭去。出於本能反應,她抬起眼睛,相信這次就會真的發現她的丈夫出現在面前。
電動門又打開了,卻沒有法比歐的身影。然而,大門的另一邊卻站著一個年輕女孩。雖然自動門感應到她,但她並沒有走出來。她站在原地,用手把裙子撫平。最後她模仿起艾莉契剛才的動作,往後移動一步,於是大門又自動關上。
艾莉契對她的動作很好奇,於是仔細觀察她。她發現這個女孩並不是非常年輕,很可能跟自己的年紀差不多。女孩的上半身微微向前彎曲,兩肩向後縮得緊緊的,彷彿周遭的空間不夠大似的。
艾莉契心想,這個女孩有某種熟悉的味道,可能是臉部那個表情吧!不過她一時想不起來像誰。她的思緒正自我封閉,徒然空轉著。
然後這女孩又做了那個動作,往前走,雙腳併攏,站了幾秒鐘之後又往後退。
就在那一刻,那女孩抬起頭來,從玻璃門的另一邊對著艾莉契微笑。
一股電流一節接著一節地通過艾莉契的脊椎,甚至延伸到她那條瘸腿裡去。她屏住呼吸。
她認識另一個人,也是用那種方式微笑,只有翹起上唇,稍稍露出兩顆門牙,嘴巴其餘的部分則完全不動。
「不會吧?」她心想。
她走過去想要看得更清楚一點,門於是一直開著。那女孩看起來似乎很失望,用疑問的眼神盯著她。艾莉契明白了,於是往後退,讓對方繼續玩她的遊戲。女孩繼續玩,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
那女孩有著同樣烏黑的頭髮,非常濃密,而且髮根是捲的,艾莉契只有極少數的幾次機會摸過那樣的頭髮。女孩的顴骨有點突出,遮蔽了那雙黑色的眼睛;但是看著它們,艾莉契認出了那與馬提亞的雙眼同樣的眼漩、同樣模糊的閃光……這些曾讓她在好多個夜裡難以成眠。
「是她!」她想,一種近似恐怖的感覺緊掐住她的喉嚨。
她本能地伸手到包包裡找相機,但是她甚至連一台傻瓜相機也沒帶。
她繼續看著那個女孩,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轉著頭望著她,視線不時模糊,好像眼睛的水晶體無法找到正確的彎曲弧度。她用乾澀的雙唇說出:「米格拉」,但是從嘴巴吐出的音量似乎不夠大。
那個女孩似乎永遠都不會累,像個小孩一樣跟那扇自動門玩個不停。現在她往前往後地跳來跳去,好像想看看自動門會不會出錯,好當場逮住它。
一位老太太從大樓內出來,走近那個女孩。從她的包包裡伸出一個長方形的黃色大信封袋,可能是X光的檢查報告。她什麼話也沒說,便抓著女孩的手臂,帶她走到外面。
女孩沒有抗拒,當她經過艾莉契身旁時,轉過頭去看了自動門一會兒,似乎在感謝它把自己逗得這麼開心。她離艾莉契是如此地近,艾莉契都能感覺到她身體移動所產生的氣流。艾莉契只要伸出一隻手就能摸到她,但是她卻像麻痺了一樣動彈不得。
她用目光跟著那兩個慢慢走著、逐漸遠離的女人。
現在又有人在進進出出,自動門不停地開開關關,那種令人昏昏欲睡的節奏充斥在艾莉契的腦子裡。
彷彿突然間恢復了知覺似的,她叫道:「米格拉!」這一次喊得很大聲。
那個女孩沒有轉頭,她身旁的老婦人也沒有回頭。她們一點也沒有改變行進的速度,彷彿這個名字和她們毫無關連。
41
馬提亞用跑的爬上三樓。在一樓和二樓之間的階梯,他碰到了一名學生,對方試著要攔下他,請教幾個問題。他越過那名學生,跟對方說:「很抱歉,我趕時間!」而在他試圖避開對方的時候,還差一點跌倒。來到入口門廳,他突然間放慢速度,想恢復鎮定,不過步伐還是很快。黑色的大理石地板非常光亮,像平靜的水面所形成的一片明鏡,映照著上面的東西與在其上行走的人們。馬提亞向門房點了一下頭、打聲招呼,就出去了。
寒冷的空氣突然間壟罩著他,他問自己:「你在幹什麼呀?」
如今他就坐在大門對面的矮牆上,思忖著為何自己的反應會是如此?似乎這些年來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等待一個信號,讓自己回去。
他再次看著艾莉契寄來給他的照片。他們兩個一起,就在她父母那張大床前,穿著聞起來有樟腦丸味的結婚禮服。馬提亞看來很溫順,而她則是在笑,一隻手還抱著他的腰,另一隻手因為要舉起相機而有部分沒有出現在鏡頭裡,彷彿她正把這隻手伸向已經變成大人的他,想要撫摸他。
在照片的背後,艾莉契只寫了一行字,然後在底下簽名:
你必須回來一趟
艾莉
馬提亞想要替這個簡短的訊息尋找一個解釋,更想弄清楚自己這種混亂的反應是什麼原因。他想像著自己走進機場的入境大廳,發現艾莉契和法比歐在欄杆外面等他,然後和她打招呼、親吻她的臉頰,接著和她的丈夫握手、彼此自我介紹一番。他們會假裝爭著誰應該來拖行李箱,在要走到車子的路程中,還會努力地描述各自的生活狀況,那真是毫無意義,好像人生真的可以用短短的幾句話就說完似的。馬提亞坐在後座,他們夫妻則是坐在前座,三個陌生人假裝彼此有某些共通點,並說著一些無關痛癢的場面話,只為了避免沉默的尷尬。
「這沒有任何意義。」他對自己說。
這個清晰的想法讓他感到有點鬆了一口氣,彷彿在短暫的迷惑之後,他正在重新恢復自己的理智。他用食指在那張照片上敲了敲,心裡已經決定要把它拋開,然後回到阿貝多那裡,繼續他們的工作。
就在他仍沉浸在這股思緒中的時刻,克斯頓•歌邦走了過來,她是一個從德勒斯登來的博士後研究生,馬提亞最近和她一起發表了幾篇文章。她俯身偷瞄著那張照片。
「你太太嗎?」她指著艾莉契,神情非常愉快地問他。
馬提亞彎著脖子抬頭看克斯頓。他本想把照片藏起來,但又覺得這麼做很沒禮貌。克斯頓那張長方型的臉,看來好像有人曾用力地把她的下巴往下拉似的。她曾在羅馬念過兩年書,會說一點義大利文,不過她的「O」卻帶著濃濃的鼻音。
「嗨,」馬提亞遲疑地說,「不,她不是我太太,只是……一個朋友。」
克斯頓咯咯地笑著,不曉得什麼原因那麼開心,她從拿在手中的紙杯裡啜飲了一小口咖啡。
「她很可愛。」她評論著。
馬提亞盯著她看了一下,有點不自在,然後又回去看著那張照片。是啊,她確實很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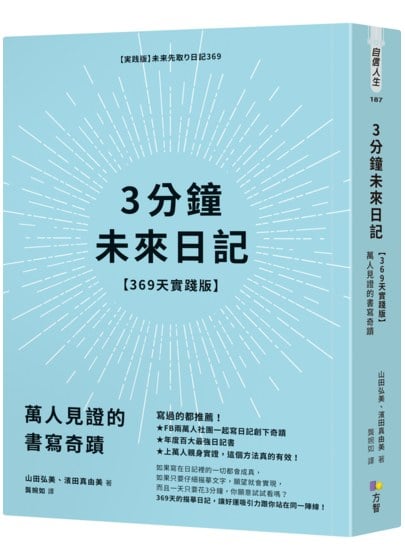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