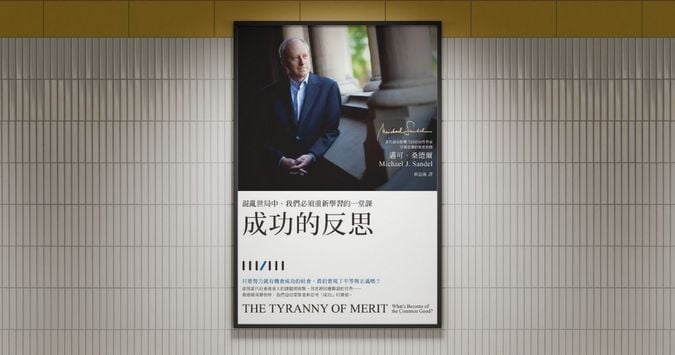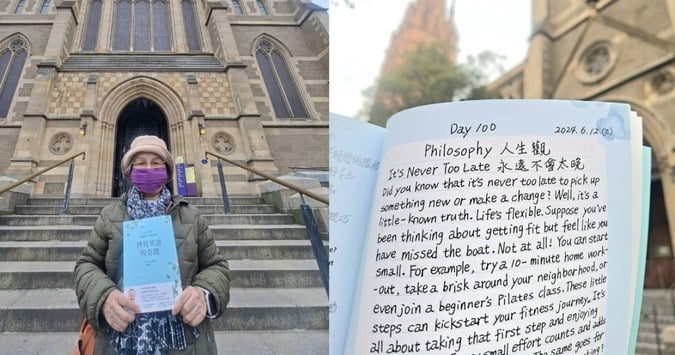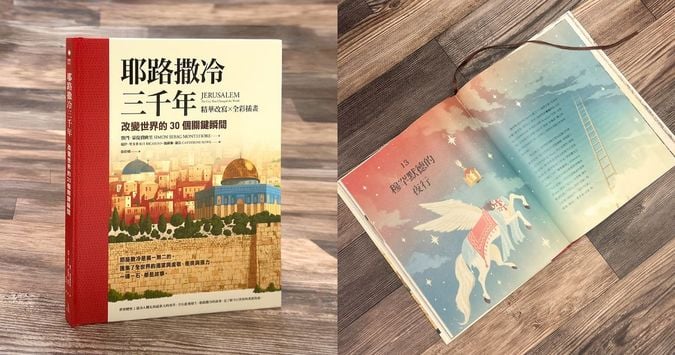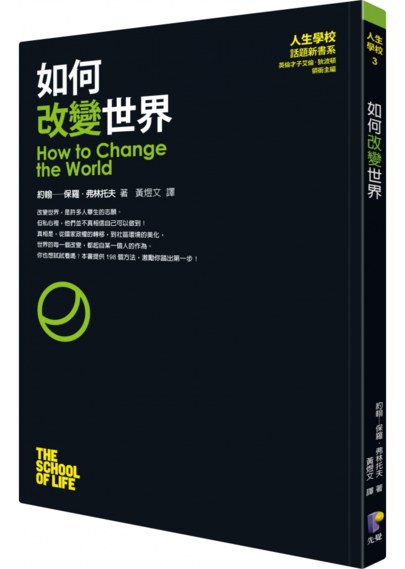甘地:「我拒絕扮演奴隸的角色。我不僅不遵從命令,還要違反命令,因為它們違背我的良知。」
從國家政權的轉移,到社區環境的美化,世界的每一個改變,都起自某一個人的作為。
人類一直不斷透過個人的行動在改變社會。歷史證明,只要專注於大我的目標,並勇於行動,往往就能展現小我的力量,捲動世界!
我們要誠實面對的問題在於,今日有什麼事是我們應該去做的,有什麼事是現在正在進行而我們應加以阻止的。我們要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曾有過應採取行動卻冷眼旁觀的時候,那種後悔莫及的感覺要牢記在心,而為了避免再有這種感受,今後我們應劍及履及,勇於行動。
你我正在改變世界
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很早就察覺到,想更精確地呈現歷史,就必須考慮一般民眾從日常生活瑣事集結起來的影響:「這些是不可勝數且極其細微的行為。」
托爾斯泰認為,打從早晨起床的那一刻起,直到晚上就寢為止,我們一直在創造歷史。我們不僅藉由「做事」來創造歷史,就連「不做事」也在創造歷史。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投票能決定誰當選,不投票也能左右最後的成敗。若從這個邏輯推論,可以說我們在上床睡覺之後也能造成一些改變:譬如一旦我們決定上床睡覺,就不會徹夜草擬一份驚天動地的政治宣言,也不會半夜救濟街頭那些流離失所的人。
這個問題不需深究,畢竟人還是要睡覺。但托爾斯泰的真知灼見使我們了解,所有人都對眼前的事物負有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絕對的核心,每個人都不可取代,」美洲原住民異議分子佩爾提爾(Leonard Peltier)曾說:「在這場結果不是大好就是大壞的苦澀選戰中,我們每個人都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然而,我們從小被教育,歷史是帝王將相的行為紀錄,這種陳舊的想法至今仍難以撼動。即使民主國家也仍積極提倡這種觀念。
在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的紀念會上,「世界各國領袖」紛紛雲集德國,向群眾發表演說。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領袖只是想來柏林沾光,他們跟這個歷史事件根本毫無關連。事實上,東西柏林間的高牆之所以倒塌,要歸功於柏林市民做的許多小事。柏林人目睹「人民力量」在鄰邦造成的巨大變化,再加上東德境內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於是許多人在好奇心驅使下,跑到東西德邊境一探究竟。檢查哨士兵面對大量湧現的群眾,不知該如何是好,他們心裡也想到鄰國最近發生的事,於是開啟邊界讓民眾自由進出。不久,柏林圍牆喪失了阻絕的功能,於是人們便順理成章地加以推倒、拆除。「世界各國領袖」將功勞攬在自己身上,但他們無法抹滅人民的成就,而且還凸顯出一項事實:我們不一定能察覺自己的行動正在改變這個世界。
當我們談到自己在這個世界遭受的挫折時,總說這是「體制」或「現狀」造成的,然後聳聳肩,抱怨自己無能為力,結果不了了之。若有一道高牆硬生生地將我們與親友分離,或許我們也會有相同的反應,因為這麼做比反抗輕鬆。想像一下,假設要舉辦街頭派對,卻發現有幾條微不足道的市政法規明確禁止,而這些法規的原意並非阻止人們在街上開派對:我們最後還是放棄了。當我們嘴裡掛著「體制」或「現狀」這些抽象詞彙時,無形中我們也成了體制與現狀的共犯。事實上,選擇權操之在己。我們可以試著修改或甚至不理會這些法規。選擇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
讓我們用小孩子也能理解的話來解釋:把現狀想像成一個握有權力的國王。不妨閉上雙眼,想像那個畫面。要怎麼知道他是個擁有權力的國王?因為他頭上戴著王冠嗎?還是他坐在黃金打造的王位上?不,這些只能說明他是國王。那麼,我們怎樣才能知道他擁有權力?這得從國王身邊的人來判斷。只要看到有人匍匐在地顫抖不已,就可以了解國王的權力所在。彰顯國王權力的不是國王本身,而是他周遭人的行為。
如果趴在地上的這些人抬起頭來,背對著國王開始談笑風生、抽菸甚或打瞌睡,那麼原本我們想像中頭戴巨大王冠、安坐在黃金寶座之上的國王,看起來就不是那麼有權力了。現在,想像這位擁有權力的國王是舞臺上的演員,那些匍匐在地的人也是演員。演員趴伏在看似擁有權力的國王面前,但他知道這只是演戲:他可以隨時站起身來做別的事。在真實生活裡,我們也可以走出自己平日扮演的角色,去做不同的事。但我們經常忘了這一點—或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這麼做。
選擇權操之在己
之所以會如此,部分原因在於,一般人普遍相信這種說法,且孩子從小就學習帝王將相的歷史,以為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握有權力。就像《綠野仙蹤》一樣,父母與老師鼓勵孩子相信,這些人(以及其他「權威」人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我們長大成人,也被鼓勵相信,雇主和政府也都握有權力。事實上,只要我們相信這種說法,他們就真的握有權力。
把日常生活與反對強有力的君主連結起來似乎有點奇怪,但世上有許多人在面對惡霸欺凌時確實感到無計可施--無論這些惡霸是統治者、雇主或甚至是你的親人--你必須牢記一點(這能讓你如釋重負),即使是順從,無論它會帶來什麼結果,也必須是你自己做的選擇。
托爾斯泰對於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道理感到困惑。他不懂,為什麼加入沙皇軍隊的俄國農民會願意殺死其他的俄國農民,甚至包括殺死自己的父親與兄弟—只因為沙皇要他們這麼做。托爾斯泰對於這個問題以及其他社會正義的問題感到憂心,於是放棄了上流社會的生活,隱居於自己的農莊。他在農莊生活時,結識了一名住在南非,積極參與政治的印度年輕人。托爾斯泰寫信給他,這封信後來出版為〈給一個印度人的信〉。
托爾斯泰在信裡提到,印度屈服於英屬東印度公司的淫威之下:「一家商業公司奴役了一個人口達兩億的民族。把這件事告訴一名毫無迷信的人,他一定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區區三萬人—他們並非身強體壯之人,只是柔弱而尋常的辦事員—就能將充滿活力、聰明、能幹與愛好自由的兩億印度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這當中的意義是什麼?光是數字就能說明一切,那就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自己。」
這名收到托爾斯泰回信的印度年輕人就是甘地,他跟托爾斯泰一樣,屬於社會上的特權階級。但甘地在南非卻因為皮膚黝黑而被人從火車上扔了出去,他因而嘗到不公義的羞辱滋味。從那時起,他決定起而反抗壓迫。甘地回到當時仍受大英帝國統治的故鄉印度,開始發起爭取自由的非暴力運動。
甘地認為意志的改變極為重要,因為它是改變順從與合作模式的前提。他要求印度民眾做到幾件事:首先是心理的改變,從被動的順從轉變為強調自尊與勇氣;其次,使民眾了解自己的妥協等於變相幫助殖民政府;最後,要有決心,絕不合作也絕不順從。甘地認為,這些改變可以透過意識層面的影響而加以推動,因此他致力鼓吹這些改變:
我的演說是為了激起「不滿」。我要讓民眾了解,協助政府或者與政府合作是一件羞恥的事,特別是這個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尊敬或支持。
當奴隸決心不再成為奴隸時,他的腳鐐也隨之脫落。他不僅解放自己,也為其他奴隸指點一條明路。自由與奴役都是心理狀態。因此,我們的首要之務就是告訴自己:「我拒絕扮演奴隸的角色。我不僅不遵從命令,還要違反命令,因為它們違背我的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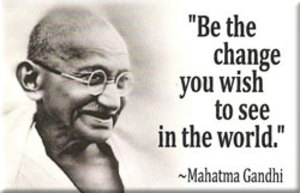
(甘地:要成為你希望看見的改變)
可以想見,英國人一定對甘地的做法大為光火。至今有些人仍難以接受市民不服從的正當性。他們會說,人人都應該守法。然而,抱持這種想法就等於認為,一旦希特勒掌權,所有德國人都必須遵守他的命令。我想現今已經沒有多少人能認同這種說法。相反地,大多數人都相信,在某種狀況下,不服從法律與違背法令絕對站得住腳。
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服從。人們有時會違反法律或不遵守情節輕微的法規,有些人甚至經常如此。有些人違法是基於自私的理由,有些人則是懷抱著高尚宗旨。充滿戲劇性的集體不服從,只是更具體證明這個普遍而日常的真理。
如果你是因為想改變世界--例如,生產便宜又好穿的鞋子--而閱讀本書,那麼你也許會對書中提到改變世界的例子感到吃驚:甘地說的心靈奴役與我提到的希特勒。這些事與你何干呢?的確,想改變世界,我們並不需要相信自己受到奴役或生活在獨裁政體之下。我們只需相信這個世界的確有什麼地方很不對勁(目前市面上賣的鞋子太貴或不好穿?),而且能堅決表示自己不願再忍受這種狀況。
儘管如此,我舉納粹德國為例並非出於偶然。我想表達的是,即使你認為自己的努力無法改變大局,嘗試去做仍有其必要。
懷疑論者總認為,一般民眾的非暴力政治活動無法擊敗納粹。事實果真如此嗎?這種假設性的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證實。夏普(Gene Sharp)不願受限於「非暴力是否能擊敗納粹」的論戰中,相反地,他鼓勵我們思考,無論在德國境內還是境外的占領區,納粹實際上受到什麼樣的非暴力反抗?
夏普獲得牛津與哈佛大學的教授終身職,他於1960年出版第一部作品,由愛因斯坦為他寫序。夏普在大作的第一卷《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學》中要求讀者脫掉眼罩,好好認清政治權力是我們自己的權力,政治權力不是只存在於投票箱裡。除了這本書,夏普還在別的作品裡提供內容多得驚人的非暴力抵抗納粹運動,這些行動經常受到軍事史家的忽視。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無法列出所有事例。以下每一段所舉的例證,各自代表事件不同的面相。
◆當犯人從波蘭一所監獄逃脫時,一名年輕女性電報員冒著生命危險,故意延遲通報時間。
◆在挪威,民眾無視於德軍的存在,把他們當成透明人,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拒絕跟他們坐在一起。這種做法看似溫和,卻足以惹惱德國人:如果在搭乘路面電車時明明有座位卻故意站著,對德國人顯然構成了冒犯。誰能想像納粹的士氣竟是如此脆弱呢?
◆在丹麥,國王同情猶太人的遭遇,於是也戴起猶太人被迫佩戴的黃色大衛星。當丹麥官員得到指示,要圍捕猶太人並且將他們遞解出境時,這些官員故意走漏消息,讓猶太人有時間藏匿。許多丹麥人無視於納粹規定的宵禁,在深夜仍流連街頭。
◆在荷蘭,有兩萬五千名左右的猶太人在非猶太人的協助下成功藏匿。
◆在德國,有一群非猶太裔民眾公然上街抗議,因為他們的猶太裔丈夫與妻子被帶走。這場抗爭發生在二戰的高峰期,地點就在柏林。難以置信的是,抗議者的訴求居然獲得回應:他們的配偶成功返家,而且在往後的戰爭期間都未曾受到迫害。
◆德國有幾位元帥在會議中頂撞希特勒,而且這種情形發生了兩次。
◆厭惡納粹政權的醫師故意讓年輕人體檢不合格,使他們不用當兵(這些醫師後來被稱為「日安」醫師,因為他們跟病人打招呼時總是說「日安」,而不是說「希特勒萬歲」)。
◆德國音樂家面對「不准演奏美國爵士樂」的禁令,於是取巧地為他們喜愛的旋律取了德文名字。
◆最著名的反希特勒行動,是由一群署名「白玫瑰」的人士組織進行的,他們製作反納粹宣傳單,從電話簿隨機挑選投遞的人家,然後把傳單散布到全國各地的家庭裡。這些傳單最早出現於一九四二年,當時德國在戰場上仍處於有利局面。「我們絕不會沉默!」其中一份傳單寫著:「我們要喚起你的罪惡感!」全國各地都可見到這類傳單。沒有人想像得到,白玫瑰居然只是慕尼黑的一小群朋友組成的。最後一批傳單成功偷渡到境外,在印刷了數百萬份之後,由盟軍飛機空投到德國各地。消息甚至傳進了集中營。「當我們聽說慕尼黑發生的事時,」一名囚禁者日後回憶說:「我們彼此擁抱而且大聲叫好。畢竟德國還是有一群正義之士。」
有些非暴力行動實在溫和得可笑:演奏美國爵士樂!但我們將會看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顛覆行動,也能激勵他人起而反抗。
要不是民眾前仆後繼進行微弱的抵抗,希特勒的政權很可能做出更惡劣的事。換言之,如果當初有更多人勇於抗爭,相信納粹也不會明目張膽做出那麼多令人髮指的事。
我這麼說並非評斷當時的人做得對不對,而是要對現在的我們提出挑戰。想像自己在納粹德國時期能做出大膽的行為,其實是相當容易的事。我們要誠實面對的問題在於,今日有什麼事是我們應該去做的,有什麼事是現在正在進行而我們應加以阻止的。我們要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曾有過應採取行動卻冷眼旁觀的時候,那種後悔莫及的感覺要牢記在心,而為了避免再有這種感受,今後我們應劍及履及,勇於行動。
(以上摘自艾倫狄波頓策畫「人生學校」系列六之一:《如何改變世界》第1章〈克服失敗主義〉。
本書後附夏普所整理198種非暴力行動清單)

《如何改變世界》作者
約翰-保羅.弗林托夫(John-Paul Flintoff)
英國知名記者、作家暨廣播節目主持人,也是艾倫.狄波頓於倫敦設立的「人生學校」講師。曾服務於《金融時報》六年,之後轉往《週日泰晤士報》。在2004年任職於《金融時報》期間,曾採訪倫敦慈善機構「孩子公司」的創辦人巴特曼賀里迪(Camila Batmanghelidjh),此篇報導成功地影響了英國政府的政策制訂,並意外募得讀者高達50萬英鎊的捐款。他也為《衛報》《泰晤士報》《每日電訊》等多家報刊撰稿,作品並曾榮獲數座獎項。
他的文字功力備受肯定,美國紀錄片《華氏911》導演麥克.摩爾,以及英國資深劇場導演理察.艾爾,都對他的作品有高度評價。已故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哈洛.品特曾盛讚他的作品:「非常好,非常有意思……事實上,它讓我開懷大笑。」
-
每個人都應該具備好國王的能力,國家命運所依靠的在於「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要負起國家主人的責任,以下兩項能力卻不能不盡快地學會:
1.能分辨善惡對錯,並願意盡可能選擇善和對。2.能區別什麼是短期利益、什麼是長期利益,並且能使兩者有適當的平衡。
這兩項是一般人要妥善處理私事、家事都不能缺少的能力。
-
宮崎駿自認受影響最深的一本書《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在什麼情況下、對什麼事情、有什麼感覺。如果在這方面有一絲敷衍,不管你想了、說了什麼看來了不起的事情,也都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