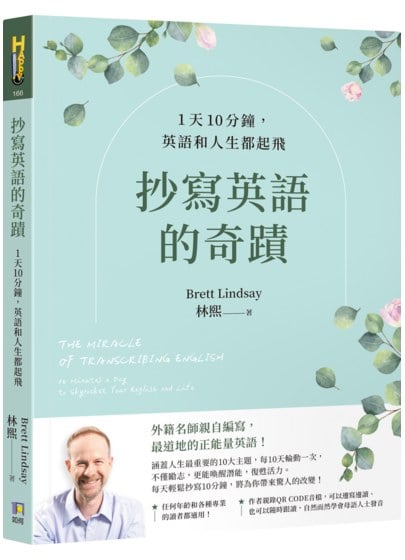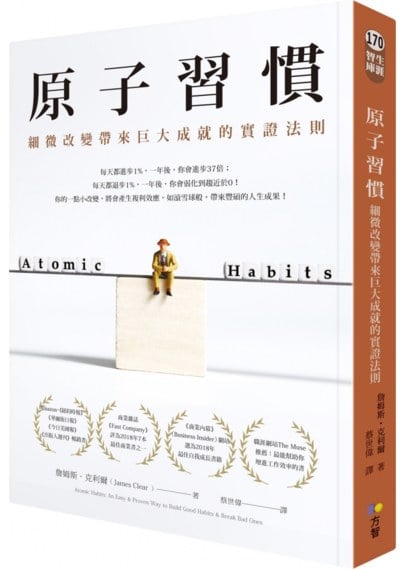「嗨,你好。」她說。
我人在希斯洛機場商務貴賓休息室的酒吧,聽見有人跟我說話,先是瞄到一隻蒼白略帶雀斑的手搭在身旁空著的椅背上,才抬起頭來看眼前陌生的臉。
「我見過妳嗎?」我問道,她看來面生,但口音帶著美國腔,筆挺的白襯衫配上造型牛仔褲,再套上及膝靴,挺像我老婆那群難纏的朋友。
「噢不,抱歉,只是看你點的這杯不錯,我可以坐下嗎?」她輕巧地挪移修長的身軀,側身在鋪著皮墊的旋轉椅坐下,順手把皮包擱在吧台上。
「琴酒?」她望著我面前那杯馬丁尼問我。
「亨利爵士。」
她對吧台內的酒保做了個手勢。酒保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小毛頭,頭髮抓得根根直豎,下巴油亮。她點一杯亨利爵士馬丁尼,加兩顆橄欖。酒送來時,她朝我舉杯。我杯中只剩一點點,說:「就敬出國旅行打的疫苗吧。」
「乾杯。」
我一口飲盡,又點了一杯。她開始介紹自己,那名字我聽過就忘了。我也把名字告訴她,只說泰德,沒提我姓西弗森,至少那時還沒說。我們倆坐在鋪了太多襯墊、燈光過度明亮的貴賓休息室裡,一面喝酒一面閒聊,知道對方也是搭直抵波士頓的航班,在洛根機場下機。她從皮包裡拿出一本薄薄的平裝小說,開始翻閱。我這才有機會仔細端詳她。人是挺美的,一頭紅色長髮,綠藍色眼珠明澈如熱帶海洋,膚色非常白,白到微微泛藍,像脫脂牛奶上面飄著的那一層。如果你在家附近酒吧喝酒,有個那樣的女人在你身旁坐下,誇讚你點的酒,你會想自己是否開始轉運了。但這條規則不適用於機場酒吧,你身旁的酒客下一刻便與你各奔前程。就算這女人也是要去波士頓,我現在心裡只裝得下憤怒,一想到跟妻子的事就火大。我待在英國的那星期滿腦子想著這個,吃不下也睡不著。
擴音器傳來機場廣播,只聽懂兩個詞:「波士頓」「延遲」。我撇一眼放滿酒瓶的架子上方,因背光略顯得暗的電子看板,顯示起飛時間延後一小時。
「再來一杯吧。」我說,「我請妳。」
「好啊。」她說,把書闔上,封面朝上放在錢包旁邊。《蜜月殺機》,作者是派翠西亞.海史密斯。
「書好看嗎?」
「算是她比較弱的一本吧。」
「班機延遲加上一本爛書,沒有比這更糟的了。」
「你最近在讀什麼?」她問我。
「只看報,我沒那麼愛看書。」
「那你在飛機上都做什麼?」
「喝琴酒。擬訂謀殺計畫。」
「挺不錯啊。」她第一次朝我微笑,咧開嘴的那種笑法,我看到她上唇和鼻子下方之間有道笑溝、完美無瑕的牙齒、一小截粉紅牙肉。不知她年紀多大?她剛坐下時,我以為應該有三十四、五歲,跟我差不多。但細看她的笑容和鼻梁兩側顏色褪掉的淡色雀斑,感覺年紀應該不大。大約二十八歲吧,我老婆正是這年紀。
「我搭飛機時當然也工作。」我補了一句。
「你是做什麼的?」
我給了她一個濃縮版,告訴她我如何為新成立的網路公司提供資金及建議;但我沒提自己怎麼賺到錢:等公司開始顯出發展可能,我立刻轉賣給有興趣的人。我也沒告訴她,其實我這一生已不再需要為錢工作。在九○年代末期泡沫經濟崩潰前,我是少數賣掉股票、順利脫身的網路投機客之一。我不提這些,純粹只是不想說而已,並不是怕惹新同伴不快,也不是怕她不想再跟我說話。我從不覺得該為自己賺到的錢感到抱歉。
「妳呢?妳在哪高就?」我問。
「我在溫斯洛學院工作,負責檔案管理。」
溫斯洛是一所女子大學,位於波士頓以西三十多公里的郊區,那一帶樹木蓊鬱。我問她檔案管理員的工作內容,她回我一個應該也是濃縮版的說明:如何蒐集、保存學校檔案之類。
「那妳住在溫斯洛囉?」
「是啊。」
「結婚了嗎?」
「還沒,你呢?」
她說這話的時候,我發現她眼神微微飄移,瞄我左手上是否有戒指。「很不幸,我結婚了。」我說,舉起沒戴戒指的手讓她瞧。「還有,我不是故意在機場酒吧脫下戒指,好吸引像妳這樣的女人在我身邊坐下。我根本就沒買戒指。沒辦法忍受戒指的觸感。」
「為什麼說不幸?」她問。
「一言難盡。」
「班機延誤,我們有的是時間。」
「妳真的想知道我的悲慘人生?」
「悲慘故事我最愛聽了。」
那我告訴妳,但我得再喝一杯,」我舉起手中的空杯,「妳呢?」
「不,謝謝你。我規定自己最多喝兩杯。」竹籤上串著兩顆橄欖,她用牙齒輕輕拉出一顆,張口咬下。那一瞬間我看到她的粉紅色舌尖。
「我常說兩杯馬丁尼太多,三杯卻又不夠。」
「真有意思。詹姆斯.瑟伯好像也說過這話。」
「沒聽過這人。」我擠出笑容,把別人的名言當作自己講的話,多少感到有點心虛。這時酒保赫然出現在我面前,我又點了一杯。嘴巴周圍的皮膚開始產生愉悅的麻木感──幾杯琴酒下肚後往往如此──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酩酊大醉,講太多話,不過這是機場規則不是嗎?雖說她住的地方離我只有三十多公里遠,但我早就忘記她叫什麼,更別提這輩子再遇到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何況跟陌生人喝著酒、談談講講的感覺真是好。光是大聲說話,就能驅散不少我內心的憤怒。
我告訴她下面這個故事:我與妻子結婚五年,先前住在波士頓。九月時我們在肯納威克飯店待了一個禮拜,那裡面對緬因州南岸,我們不約而同愛上了那一帶,甚至以貴得離譜的價錢買下一塊面海的土地。我告訴她,我太太因為拿了個碩士學位,叫作藝術與社會行動還是什麼的,就覺得自己有能力找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共同設計新買下的房屋。於是她這一陣子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肯納威克,跟一個叫布列德.達吉特的承包商一道工作。
「所以她跟布列德……?」她輕巧咬下第二顆橄欖後問我。
「嗯哼。」
「你確定?」
於是我越講越多,告訴她米蘭妲早就厭倦波士頓的生活,我們結婚頭一年,她整天忙著布置我們位於南端區的那棟豪宅。之後呢,她在索瓦藝術街區上的一家畫廊找到一份兼職。畫廊是朋友開的。
其實那時我就覺得兩人關係有點變質。晚餐才吃到一半,就已經沒話講了,也不再同時上床睡覺。更重要的是,我們都變了,不再是當初結合時的那個人。剛相識時我是有錢的生意人,教她品嘗昂貴的酒,帶她參加慈善晚宴,而她是灑脫不羈的藝術家,空閒時訂張機票去泰國海灘,愛去平價酒吧流連。我知道我們倆非常不配,就像通俗劇常見的那樣,但我們合得來,每一方面都完全合拍。我認為自己算好看,而且是大部分人承認的那種帥,但只要我跟她在一起,沒人會看我—就連這點我也喜歡。她腿長胸部大,雙唇飽滿,一張心形臉蛋十分精緻。頭髮是深咖啡色,但她總把它染黑。她會刻意把頭髮弄蓬,一副才剛起床的模樣。她皮膚非常好,根本不需要化妝品,但她非得畫上黑眼線才肯出門。在酒吧或餐廳時,我看到男人目不轉睛盯著她,或許這只是我內心想法的投射,但他們看著她的表情實在是飢渴又原始。我覺得慶幸,至少我不是活在男人習慣身上帶著武器的時代或地區。
去緬因州肯納威克旅行是臨時起意,因為米蘭妲抱怨我們倆已經一年多沒單獨相處了。我們在九月的第三個禮拜出發,剛開始幾天天氣晴朗溫暖,但到了星期三,從加拿大南下的暴雨把我們困在套房,哪兒也去不了。離開房間也只能去飯店附設的地下室酒館吃龍蝦、喝阿拉加什白酒。那場暴風雨過去以後,天氣變得沁涼乾爽,陽光不再那麼明亮,黃昏提前來到。我們穿上新買的毛衣,朝旅館北方的懸崖走去。通往懸崖的路徑蜿蜒著,一側是海水怒漲的大西洋,一側是亂石磊磊的峭壁。前不久還瀰漫著防曬乳氣味的潮溼空氣,變得淡薄,帶著海水的氣味。我們不約而同愛上這地方,因此當我們走到小徑盡頭的懸崖高處,看見一片種滿了玫瑰果的土地打算出售,我立刻撥告示牌上的電話號碼,二話不說買下。
一年以後,玫瑰果叢剷光,挖了個噴水池,這棟有八個房間的房子外觀差不多整修完成。我們請來的總承包商叫布列德.達吉特,這人離過婚,身材壯碩,黑髮濃密,下巴蓄著鬍鬚,鷹勾鼻十分醒目。我一連幾星期留在波士頓,指導一群剛畢業的麻省理工學生,他們發明了專門用來搜尋部落格的新式運算法。米蘭妲待在肯納威克的時間越來越多,在飯店訂了個房間,審視房屋裝修的每一道細節,從磁磚到浴缸都力求完美。
九月初,我決定開車去找她,給她一個驚喜。汽車開上波士頓北方的九五號州際公路時,我在她手機留下訊息。接近中午時我抵達肯納威克,去飯店找她,那裡的人告訴我她早上就出去了。
我往新別墅駛去,把車停在礫石車道上,前方停著布列德的福特貨卡車,米蘭妲那輛知更鳥蛋藍色的BMW迷你跑車也在。我好幾星期沒來巡視,看到裝修進度滿高興的。窗戶都已裝上,而我訂購的青石鋪路石(花園有幾處泥土凹陷必須修整)也已經送到。我沿著路走到房屋後頭,發現每一間位於二樓的臥房都有小露台,而從一樓附有紗門的遊廊走下去,是個非常大的石砌庭院,庭院前面挖了個長方形的洞,看來應該是泳池。我沿著庭院的石階拾級而上,透過面對大海的廚房頂窗,看到布列德和米蘭妲。我正打算輕敲窗戶,提醒他們我來了,但眼前的景象讓我住了手。他們倆閒閒地靠在新裝好的石英流理台上,望著窗外山坳的景色。布列德叼著一根菸,我看到他把菸灰彈到另一隻手擎住的咖啡杯裡。
不過真正讓我停下手的是米蘭妲。她的姿勢有種說不出來的什麼。看她背靠著流理台,斜倚在布列德的寬闊肩膀上,一派輕鬆自在。我注視著眼前這一幕:她略略抬起手,布列德便把點燃的菸遞進她兩指之間,她深深吸了一口,把菸遞回去。兩人默默交換香菸,沒有看對方一眼,於是我知道他們不但上過床,很可能也已經愛上了對方。
但我第一個感覺是驚慌,而不是憤怒或氣沮。我怕他們看見我站在外面院子裡,窺探著他們此刻的親暱。於是我重新沿來路走回大門口,穿過遊廊,推開玻璃門,站在充滿回音的房子裡大叫:「哈囉!」
「在這裡!」米蘭妲大喊,我走進廚房。
他們稍稍移開一些,但仍然靠得很近。布列德把菸扔進咖啡杯裡掐滅,米蘭妲說:「泰迪,怎麼突然來了。」只有她會叫我泰迪,這是我們倆之間的暱稱,叫著玩的,其實根本不適合我。
「嘿,泰德,」布列德說,「目前為止你有什麼想法?」
米蘭妲從流理台後面走過來,吻了吻我的嘴角。我聞到她身上昂貴的洗髮精香氣,還有萬寶路的菸味。
「看起來不錯。我要的鋪路石磚已經送到了。」
米蘭妲笑了:「我們讓他選一樣東西,所以他只關心那個。」
布列德也繞過流理台,跟我握手。他的手掌甚寬、指節粗大,掌心溫暖乾燥。「想不想到處看看?」
布列德跟米蘭妲帶我參觀房子,布列德談講建材的事,米蘭妲告訴我哪一樣家具要擺哪兒,我不禁想方才的事會不會是我想歪了。兩個人跟我說話時,都沒有顯出特別緊張的樣子。或許他們只是變成好朋友,就是那種會互相打氣、合抽一根菸的朋友。米蘭妲不吝於表達情感,也不避忌肢體碰觸,她會勾住女生朋友的臂彎,跟我們的男性朋友打招呼或道別時,親吻他們的嘴唇。我突然想,搞不好是我太大驚小怪了。
參觀完房子以後,我和米蘭妲開車回肯納威克飯店,在名叫馬廄的酒館共進午餐。兩個人各點一份煙燻鱈魚三明治,我喝了兩杯威士忌蘇打。
「妳學布列德,又開始抽菸了嗎?」我問她,設下圈套想讓她現出原形,看她怎麼回話。
「什麼?」她雙眉緊皺,眉間擠出一道深溝。
「妳身上有點菸味,剛在房子裡時我聞到了。」
「我不小心吸了一、兩口,但泰迪,我沒打算再抽菸。」
「我其實不覺得怎麼樣,只是隨便問問。」
「你能相信房子快弄好了嗎?」她拿起一根薯條蘸我面前擠出來的番茄醬。
我們聊了一會房子的事,我益發懷疑剛才看到的情景根本沒什麼。她表現得泰然自若。
「週末會留在這裡嗎?」她問我。
「不會,我只想過來看看妳。我今晚約了馬克.拉馮斯吃晚餐。」
「取消約會,留下來。明天天氣應該會很棒。」
「馬克專程飛過來跟我見面。我得先搞定一些數字。」
我原本打算整個下午待在緬因州,希望米蘭妲能在房裡陪我,睡個長長的午覺。但如今我發現布列德跟她在嶄新高級的廚房裡(而且是我付的錢)互動親密,便臨時改變主意。用過午餐後,我開車送米蘭妲回新房子,她得回去取車。之後我並未直接開上九五號州際公路,而是改走一號公路,往南開到克特瑞暢貨中心,全是專賣店,起碼綿延五百公尺長。我在其中一間店門口停下車,是專賣戶外運動用品的店,之前開車經過無數次,從沒進去過。十五分鐘後,我已買了好幾樣東西:一雙防雨的迷彩圖案長褲、連著帽兜的灰色雨衣、戴起來有點太大的飛行員眼鏡,還有一副高級的雙眼望遠鏡,花了快一萬五千元。我拿著剛買的裝備到家居用品館對面的公共洗手間去,換上這身新行頭。我拉高帽兜,戴上眼鏡,覺得不會被人認出,至少隔著一段距離時認不出來。我繼續朝北開,然後在肯納威克山坳旁的停車場停下,好不容易把這輛奧迪四輪傳動汽車駛進兩部小貨車中間停好。我想米蘭妲跟布列德不太可能專程來這個停車場,但也沒必要讓人發現我的車子停在這裡。
風停了,鉛灰色的天空低垂,空氣中有溫暖潮溼的雨水味。我往潮溼的海灘沙地另一頭走去,攀上看來有點鬆動的大塊頁岩,來到懸崖小路的入口。我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去看右側一望無際的大西洋,眼睛只管盯著腳下的鋪石步道。雨後溼滑無比,時不時有樹根擋路。部分路段已完全崩壞,有一面告示牌警告行人小心,字跡早已模糊不清。或許是因為這樣,這條小路沒什麼人經過,那天下午我只看到另外一個人,是個穿著波士頓棕熊隊球衣的少女,身上有大麻味道。我們擦身而過,不朝對方看,也沒說話。
快走到小路盡頭時,我看到一面快傾頹的水泥牆面,幾乎與小路等高,圍住一棟石造房屋的後院,再往前就是將近五百公尺的荒廢土地,地勢越來越高,頂端是我們的土地。小徑在此往下延伸入海,穿越短短的海灘(海灘上布滿砂礫、壞掉不能用的浮標和海藻),然後沿著彆扭歪曲的雲杉樹中間蜿蜒而上。雨勢開始變大,我摘下淋溼的太陽眼鏡。這時候米蘭妲或布列德幾乎不可能在外面,不過我想還是別靠近已經清理好的土地。峭壁下方有一大片常綠灌木林,我決定躲在那兒觀察。就算其中一人往外看,發現我揹著望遠鏡,也會以為我是賞鳥客。假如他們往我這邊走來,我可以很快朝後方小路撤退。
當我終於看到別墅在遠方浮現,矗立在一片荒涼土地之上,我再一次驚訝地發現,後側—面向海的那一面—與朝向大路的前側,是如此巧妙相對。別墅前側以小碎石裝飾,加上幾扇小窗和一道黑沉沉的木門,上面的門拱設計得華麗誇張;房子後面則將木材漆成淺米色,一式一樣的窗戶和陽台,看起來像是中型飯店。我問米蘭妲何以需要七間客房,她回我說:「我朋友很多。」然後奇怪地看我一眼,彷彿我剛才問的是「為什麼家裡要有浴室」這種問題。
我看到一棵長得歪歪扭扭的雲杉樹,像盆栽一樣矮,底下適合藏身。我在潮溼地面上趴下,全身俯臥,然後開始調整望遠鏡,定好焦距後瞄準別墅。這裡離別墅不到五十公尺,可以清楚看到窗戶裡面的情況。我先掃視一樓,沒看到任何動靜,然後逐一審視二樓樓面,還是沒有。我先停下來,用裸眼掃視房子外觀一圈,希望可以看到屋前車道。房子裡似乎沒人,儘管我剛才送米蘭妲回去時,布列德的貨卡車還停在那裡。
幾年前,我跟一名同事一起去釣魚,他跟我一樣做網路投機生意,也是我認識的人裡面,外海捕釣技術最厲害的。他只要往海面上盯著瞧一會兒,就知道哪裡有魚。他告訴我,祕訣是眼神別聚焦,你同時看著每一樣事物,收進視線範圍內;這樣一來,任何一絲顫動也躲不過你的眼睛,你會看到水面下的騷動。那時我照他說的話做,結果只引來一陣頭痛。當我用望遠鏡全部掃視一遍,依舊什麼也看不到時,我決定再試一次他的方法。我盡量讓眼前的事物變得模糊,等待某個動作自然浮現。盯著房子看了不到一分鐘,就看到北側的高窗—應該是起居室—裡頭有些動靜。我舉高望遠鏡,盯著窗戶看:布列德和米蘭妲方才走了進去。我看得很清楚,午後略微沉下的太陽照進窗戶的角度剛剛好,室內一切顯得十分清晰,又不至於反光。我看到布列德走向一張桌子,是木工師傅臨時用板條箱拼湊成的。他拿起一片木材,看起來像是天花線板的一部分,遞給我妻子看。他伸出手指劃著線板內的凹槽,她也伸出手指劃著。他嘴唇蠕動不知在說什麼,米蘭妲只是點頭。
有那麼一刻我覺得實在荒謬,一個疑心病太重的丈夫穿上迷彩裝,窺探自己的妻子和承包商。突然間我看到布列德放下線板,米蘭妲一扭身讓他抱住,她微微側過頭,吻住他的嘴。他身體往前傾,一隻大手擠壓她的臀部,把她緊緊摟向自己,另一隻手攫住她散亂的髮絲。我告訴自己別看了,但不知為什麼,始終無法移開視線。我起碼看了十分鐘,只見布列德彎身壓住我妻子,掀開她深紫色裙子,脫下她小小的白色內褲,從後面進入。我看著米蘭妲很有技巧地側躺下來,一手撐住桌角,一手在兩腿之間摸索引導著他進入。顯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身體止不住向後滑,跌坐在地。之後我沿著來路回去,看到一個被風吹皺水面的深水坑,我拉下帽兜,方才吃的午餐統統吐在水窪裡。
「這是多久以前的事?」聽我說完後,身旁的旅伴這麼問我。
「差不多一個禮拜。」
她眼睛一眨一眨,咬住下唇,我發現她眼瞼白得像衛生紙。
「那你打算怎麼做?」她又問。
整個星期,我不知問了自己多少遍。「我只想殺了她。」我的嘴唇因為喝了太多琴酒有些麻痺,但我還是對她微笑,眨了眨眼睛,表示這不過是個玩笑。但她神情嚴肅,挑了挑紅色眉毛。
「你這麼做沒錯。」她回答,我想她接下來會暗示這是個玩笑,但等了一會,她沒有任何表示。她定定地看著前方,我望向她,這才發現她比我一開始以為的還要美得多,是一種超凡絕塵的美,跨越時空,像極了文藝復興時期畫作的女主角。不像我老婆,看起來像是五○年代艷情小說的封面女郎。我正打算開口說話,只見她抬起頭聽擴音器傳來話聲模糊的廣播,說我們可以準備登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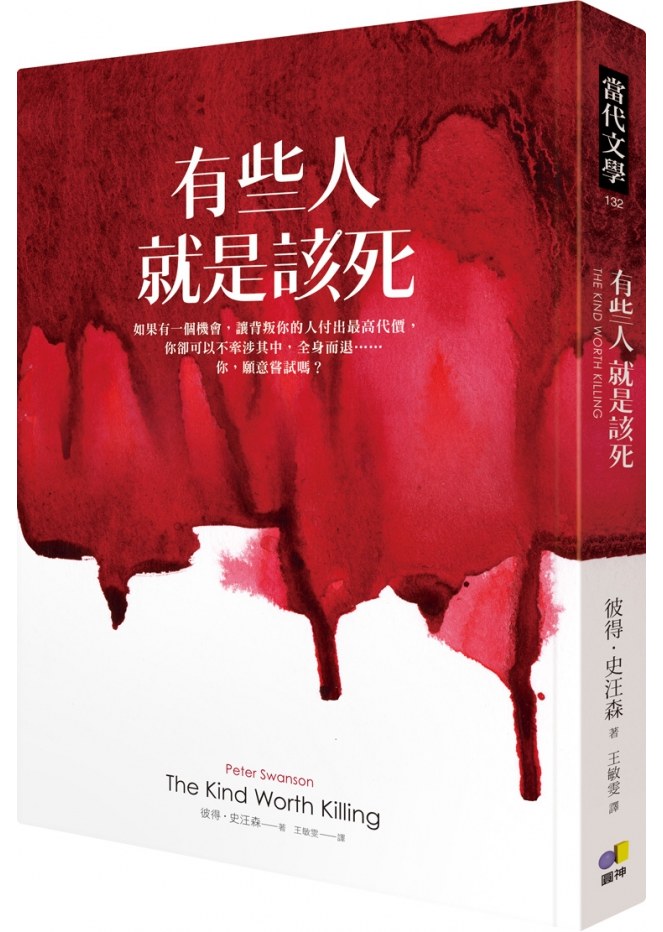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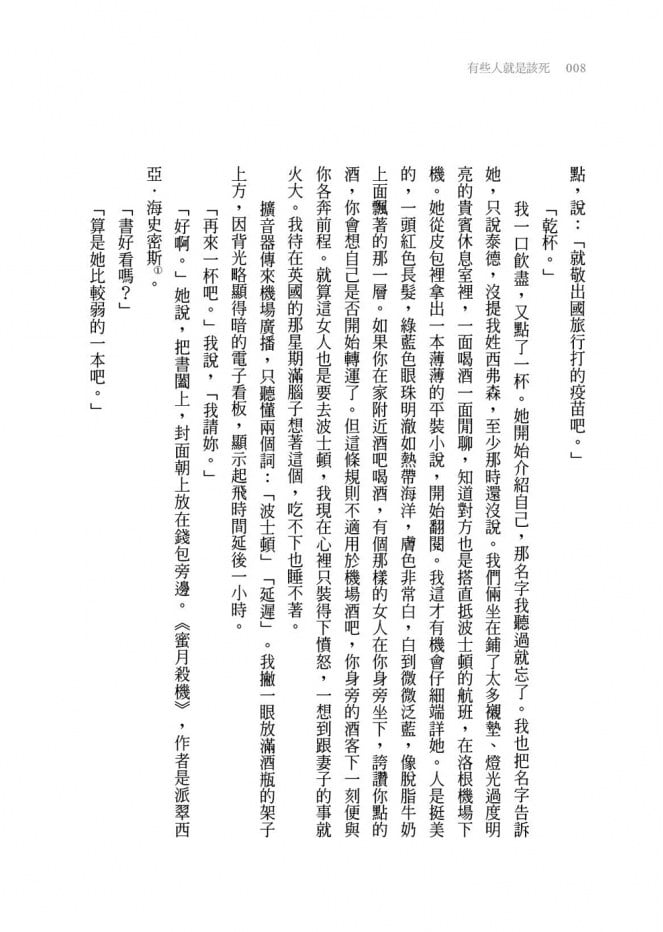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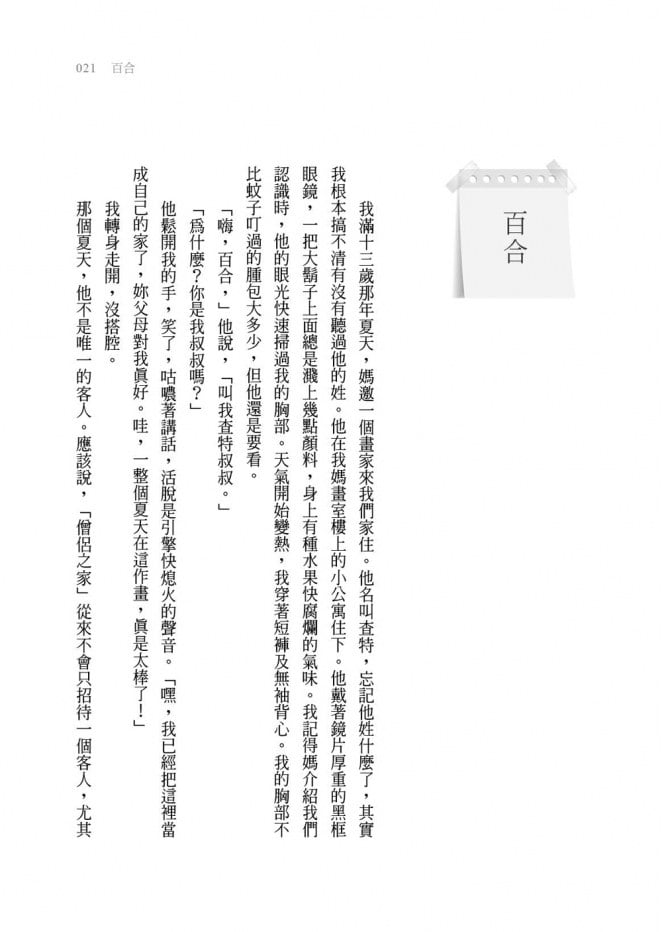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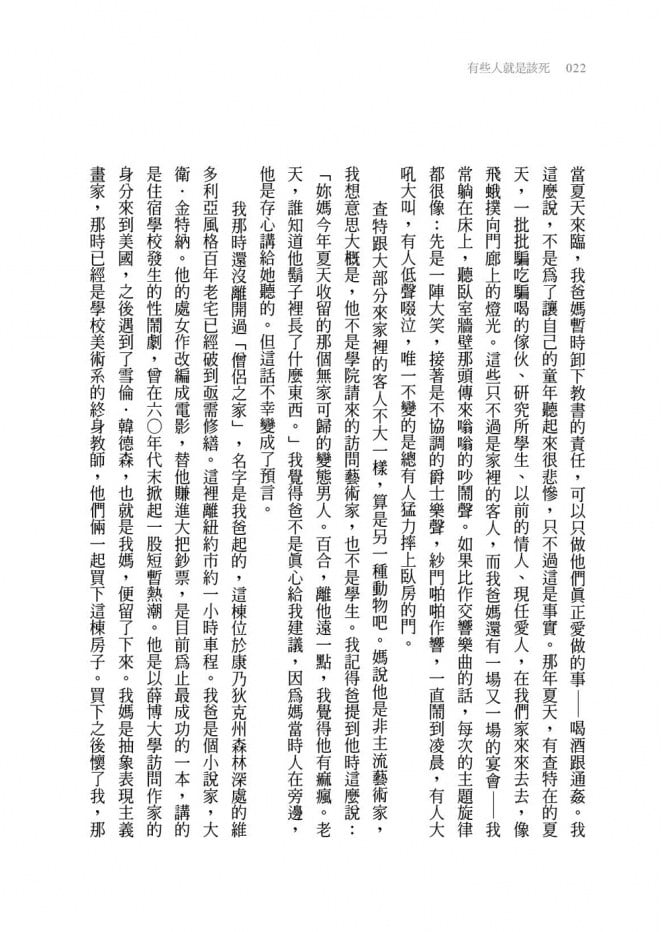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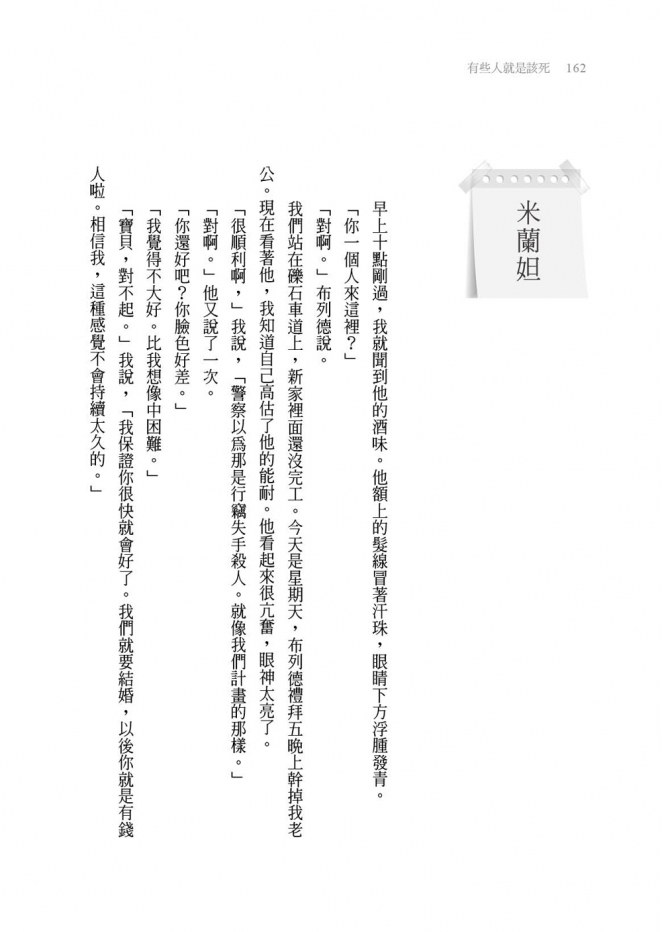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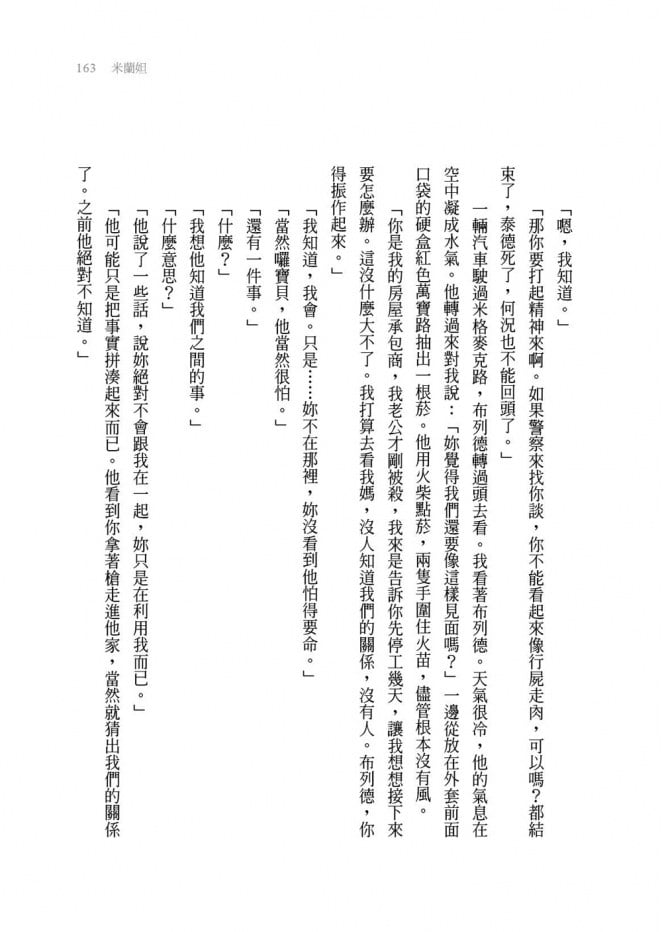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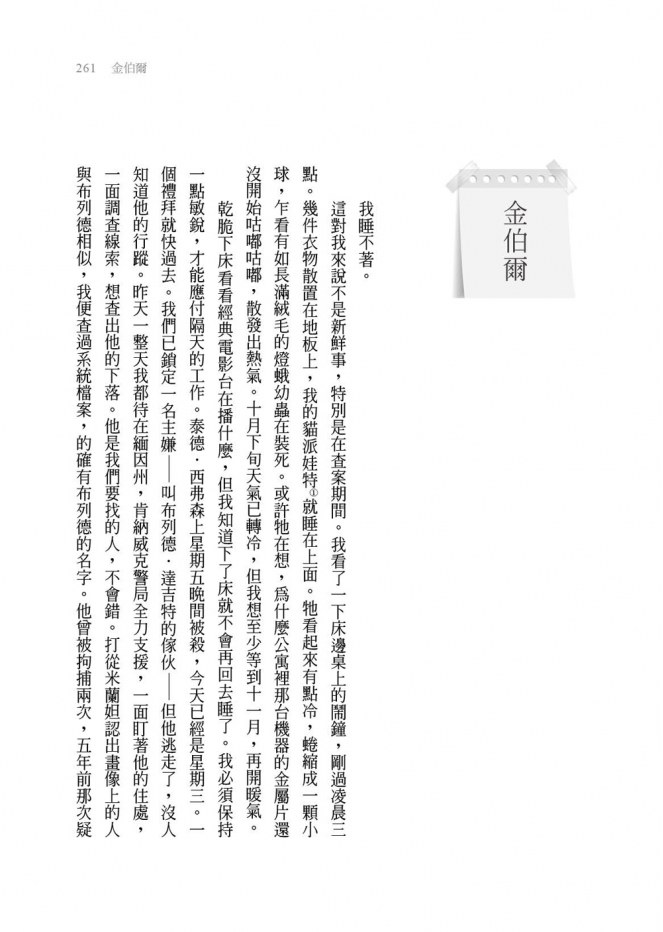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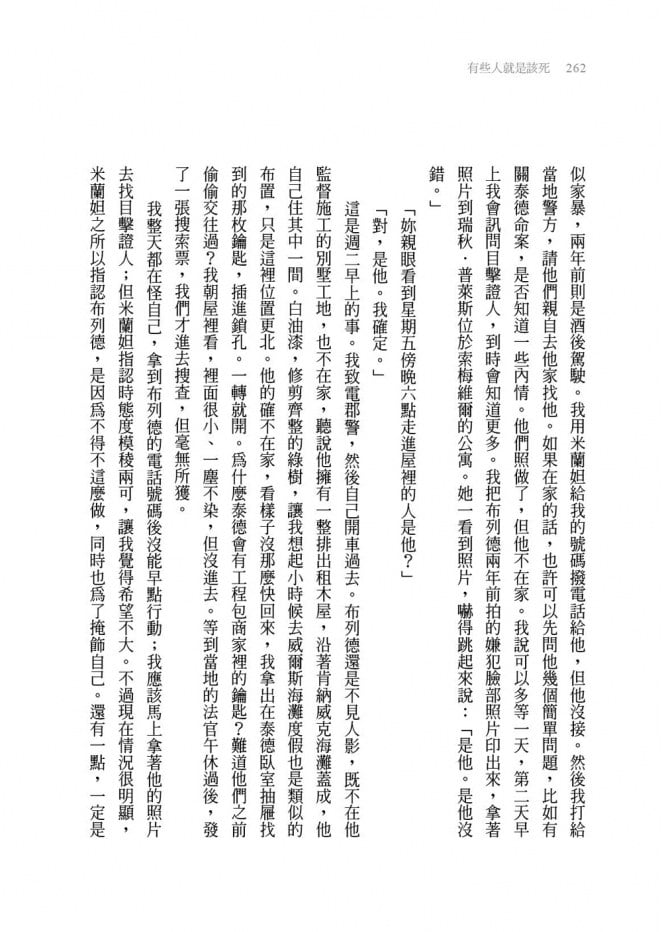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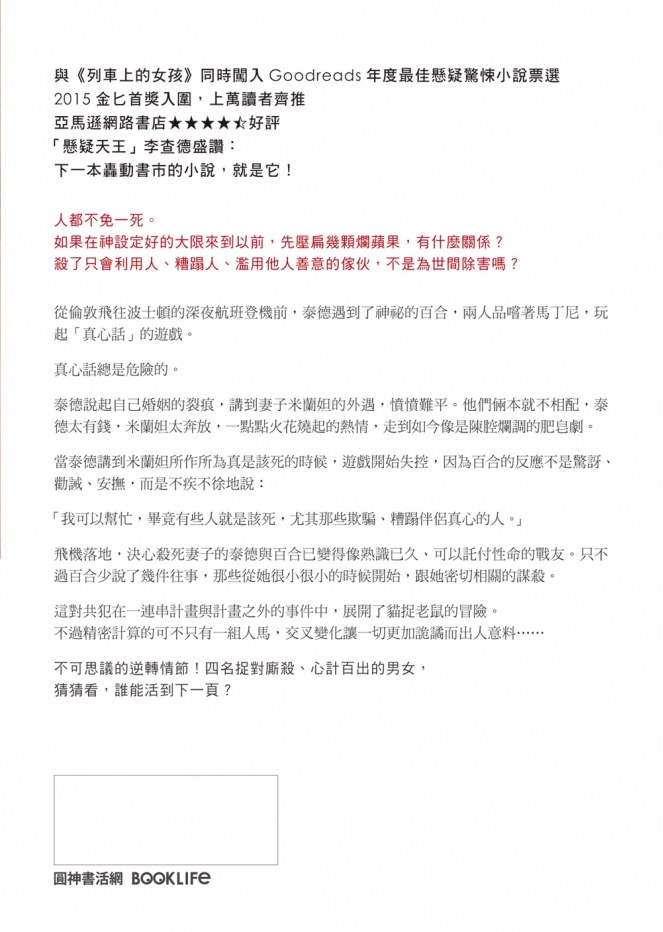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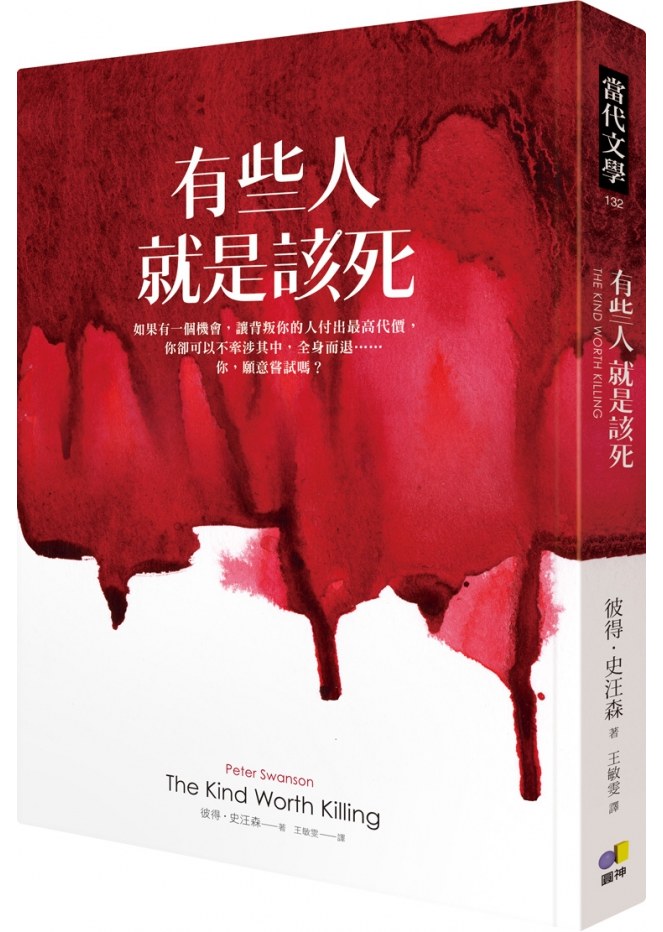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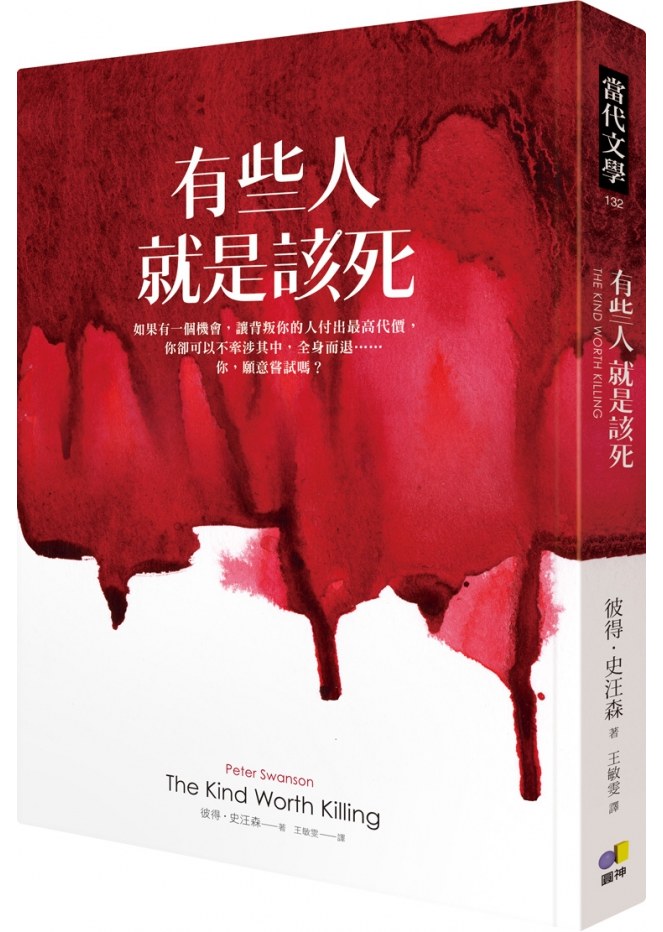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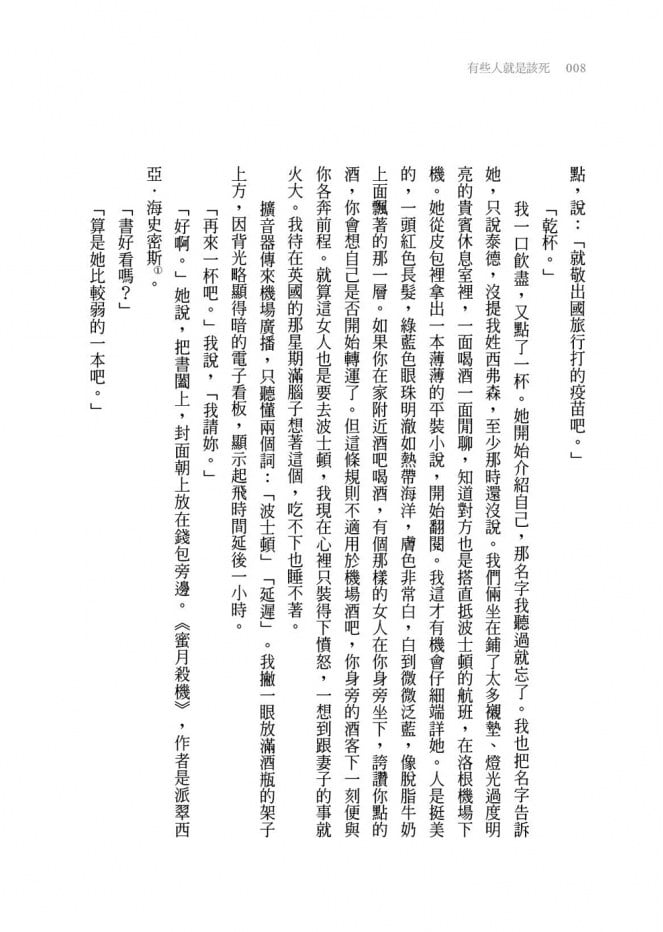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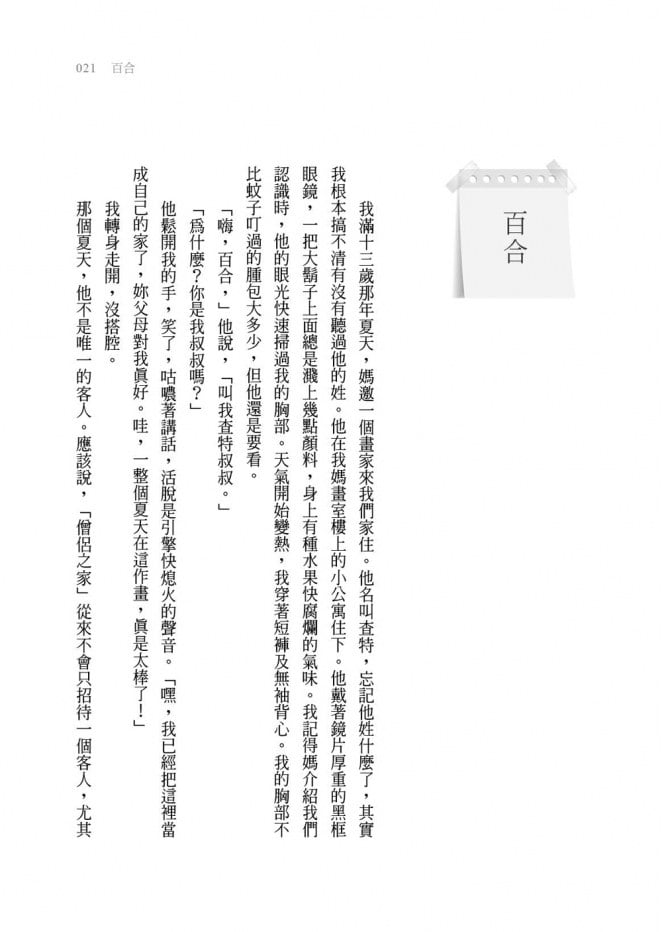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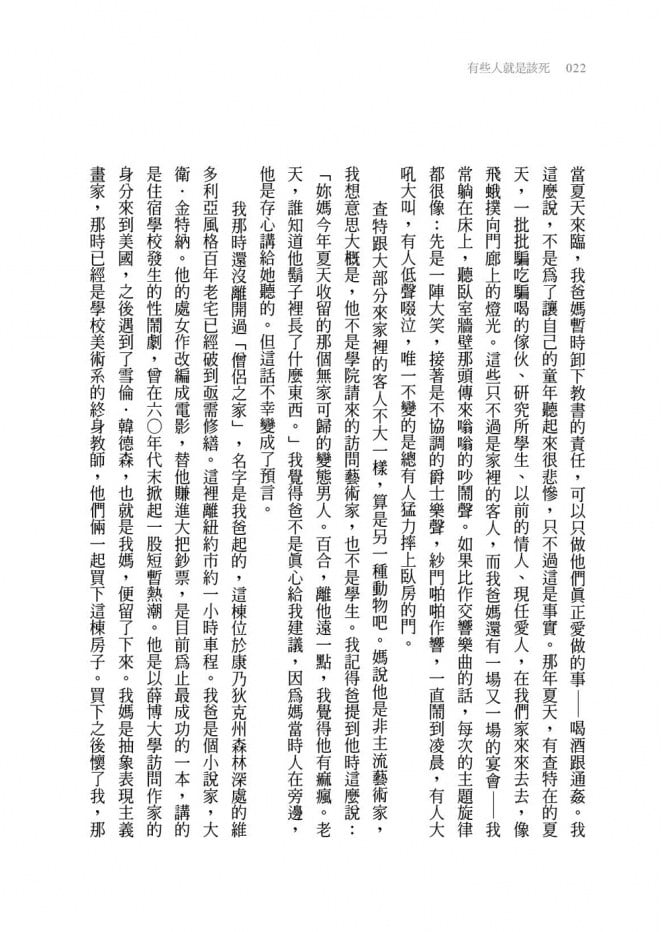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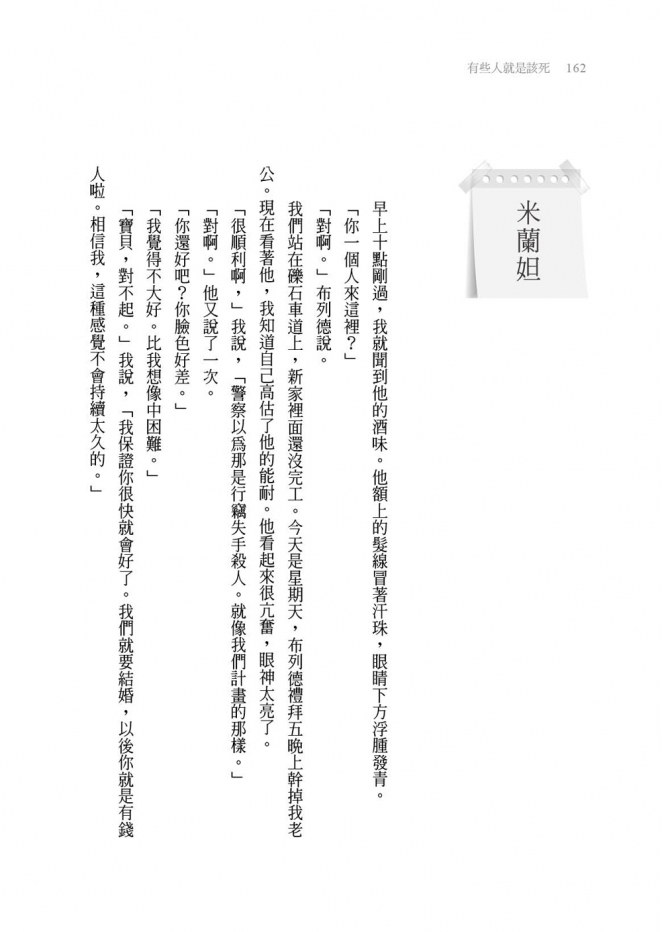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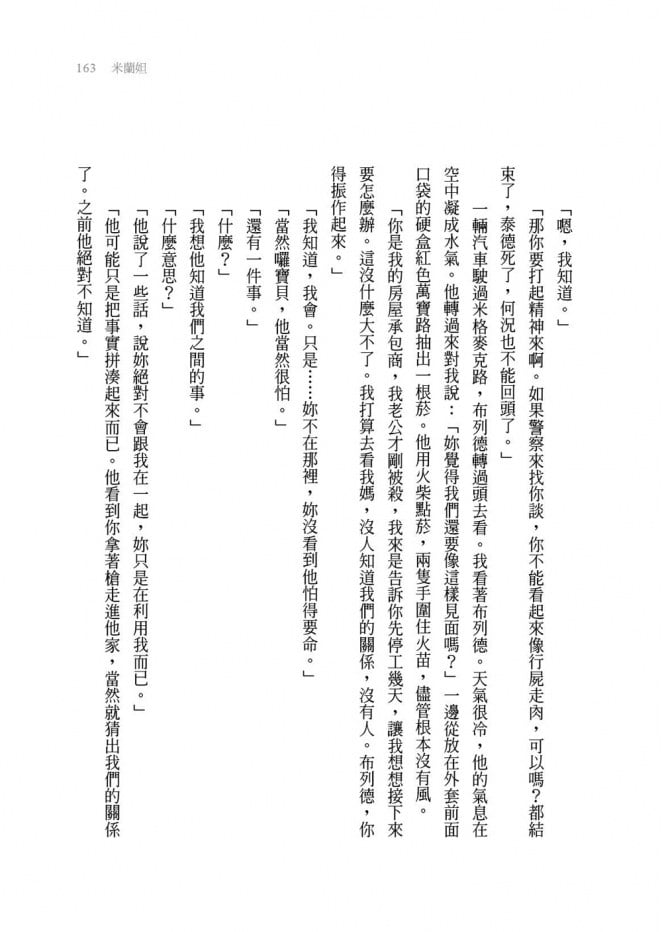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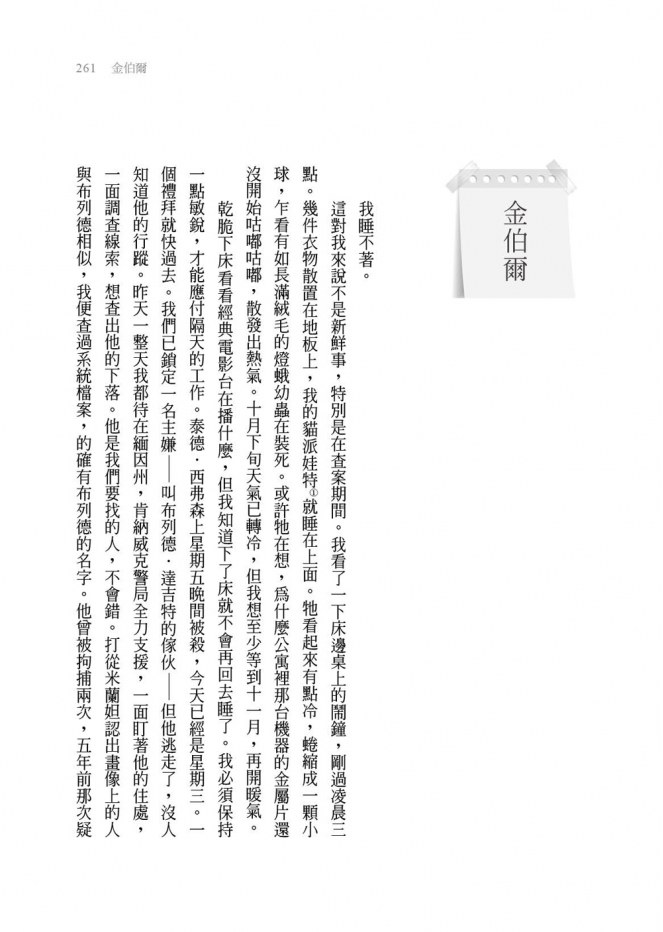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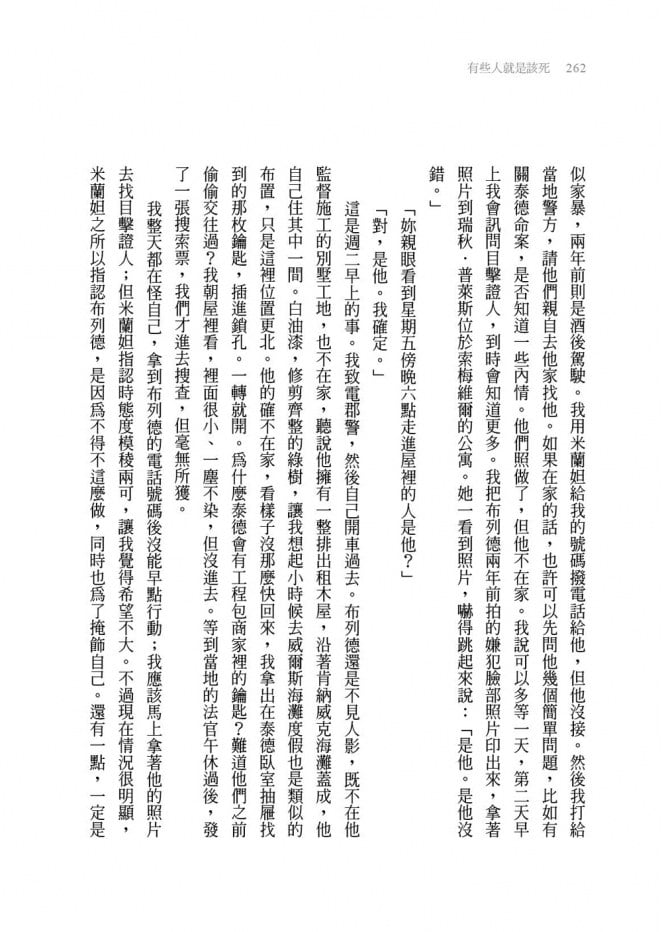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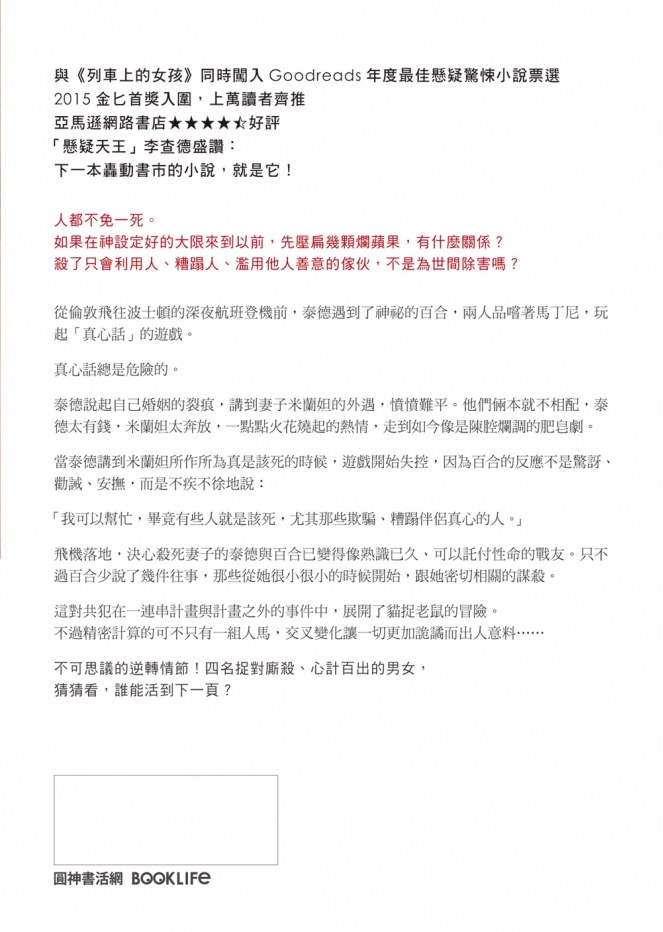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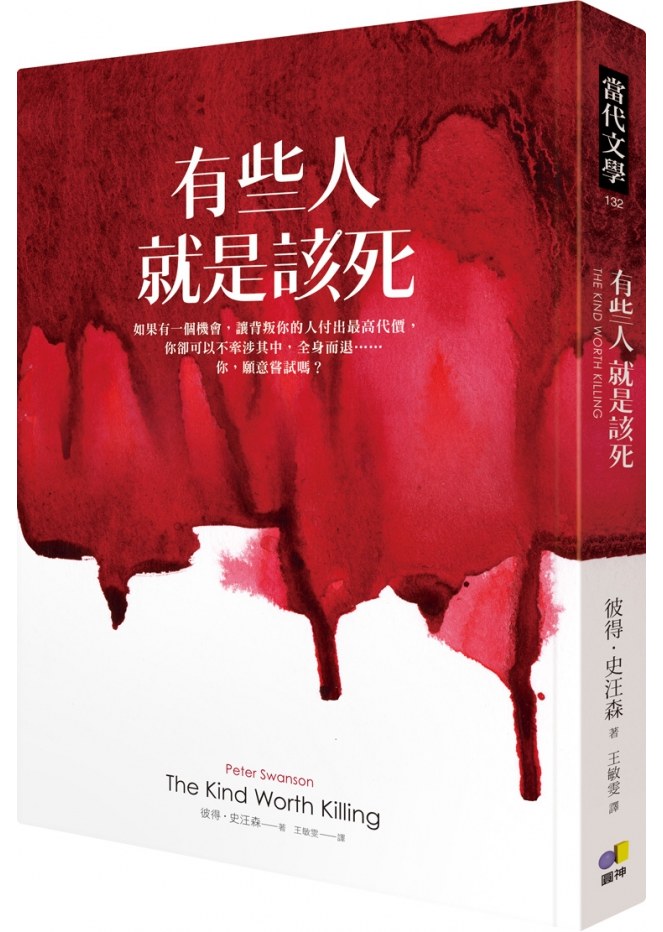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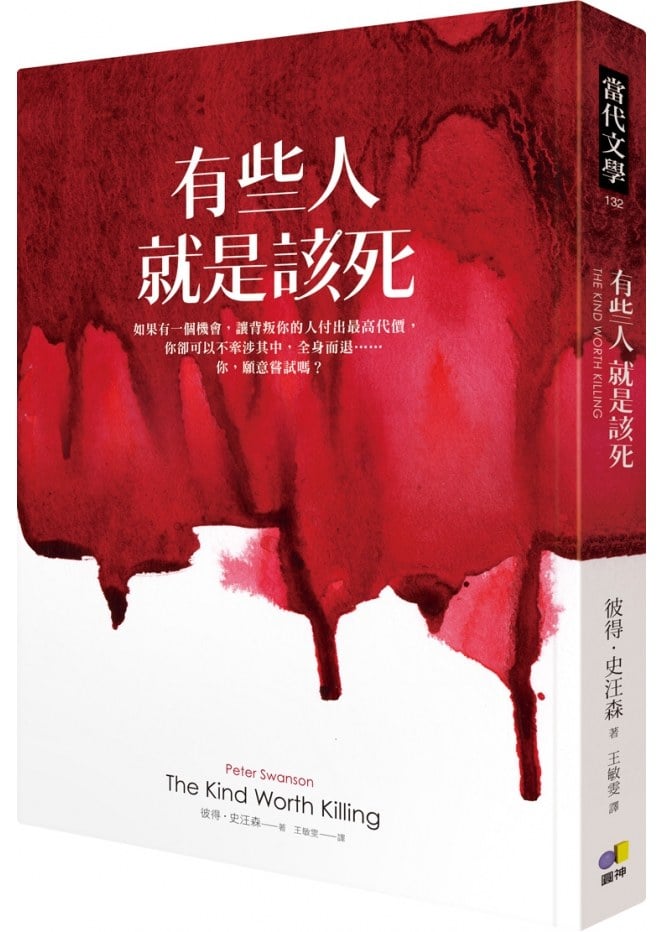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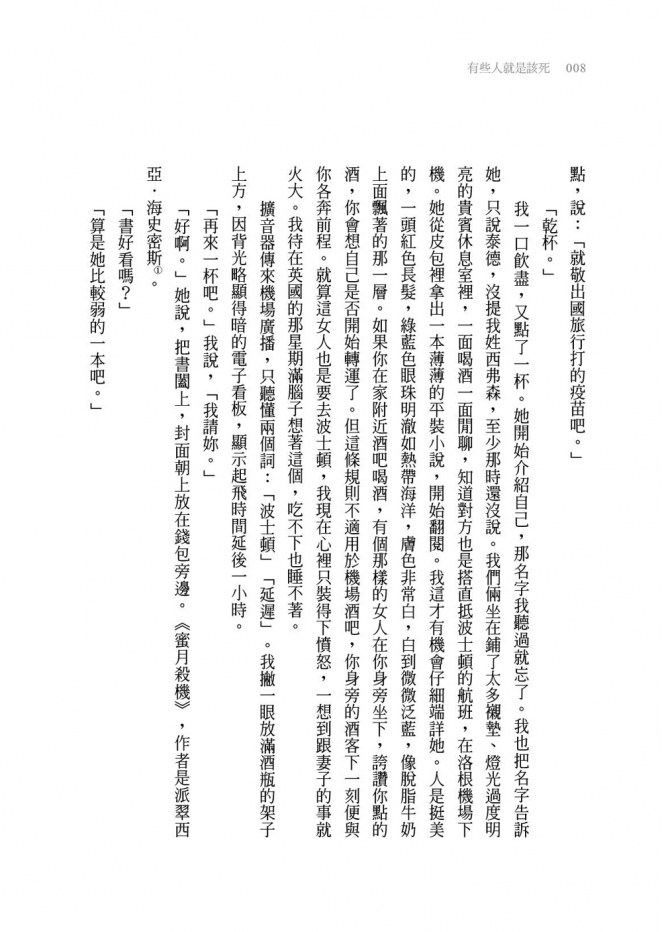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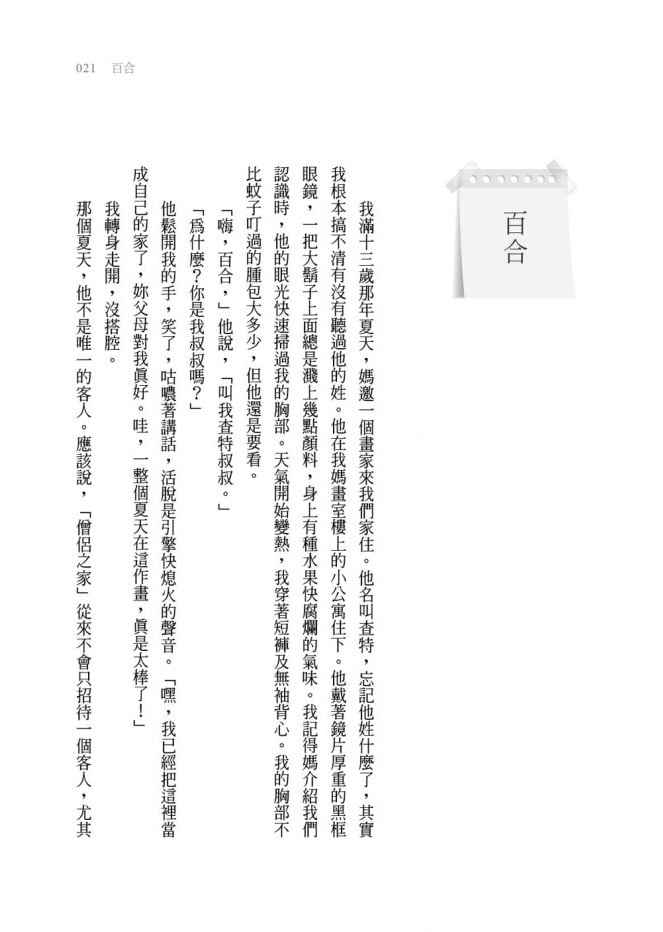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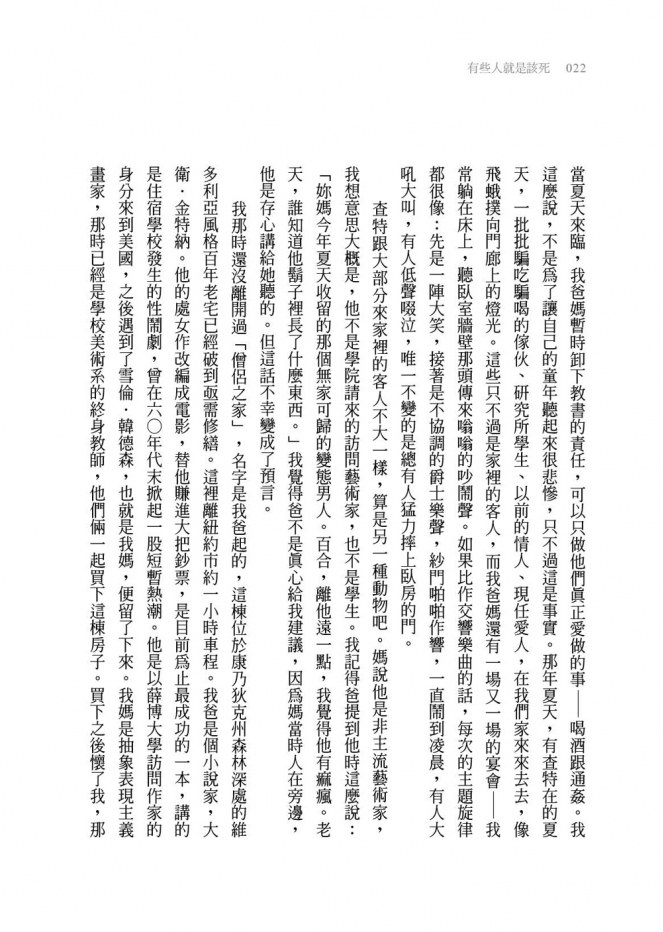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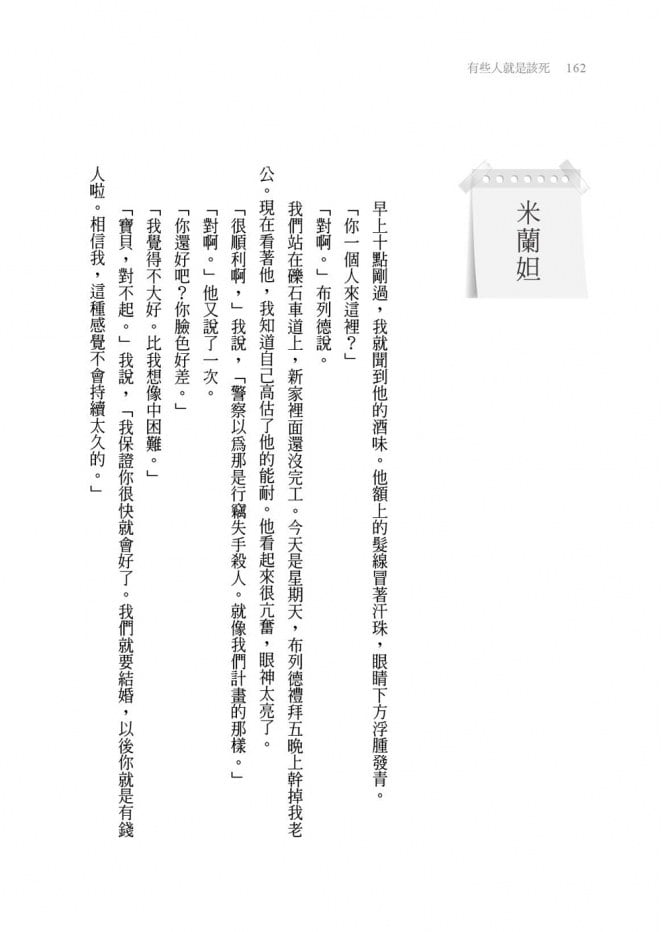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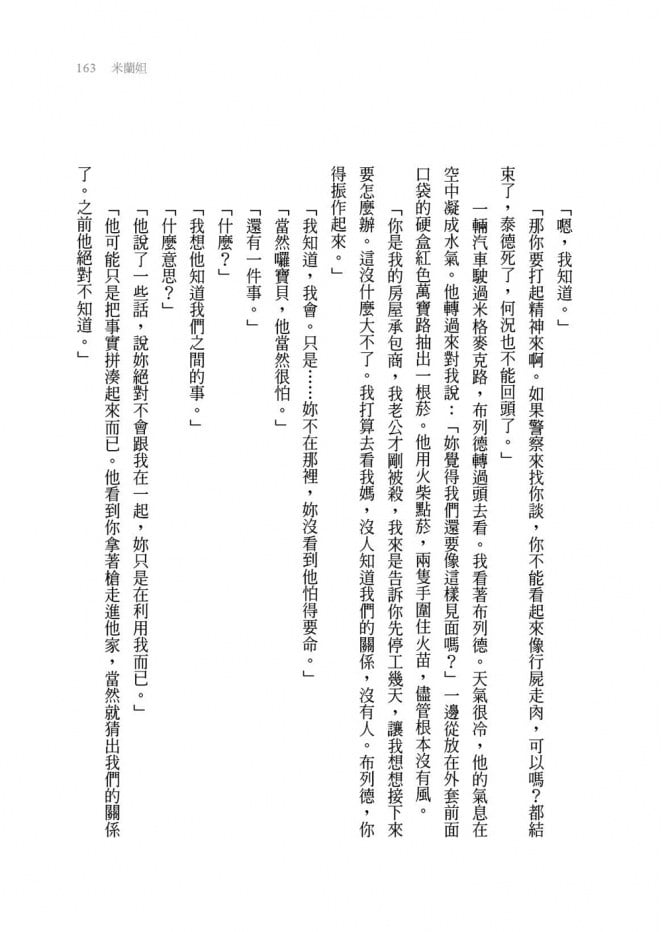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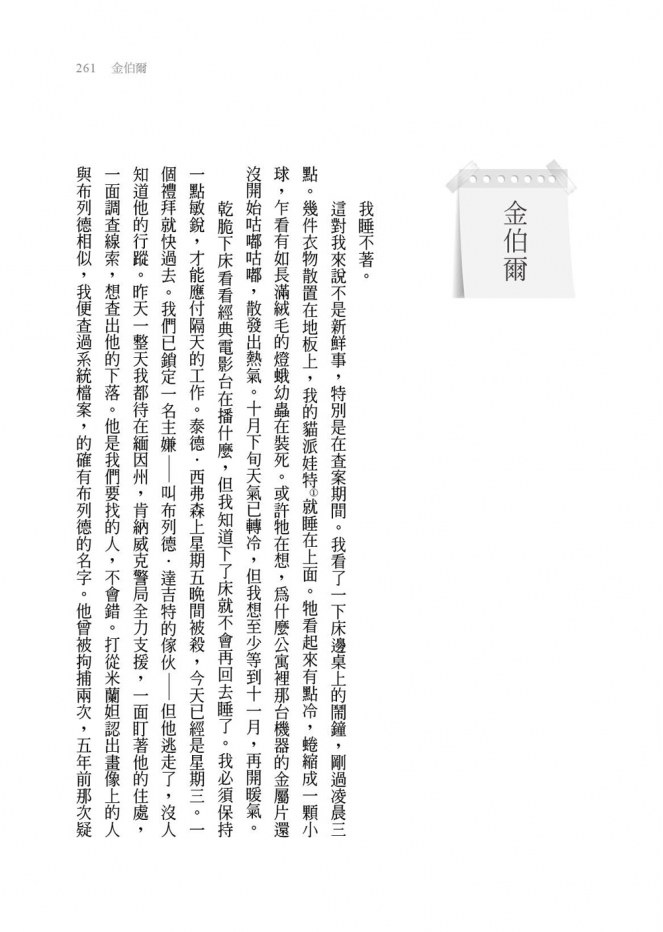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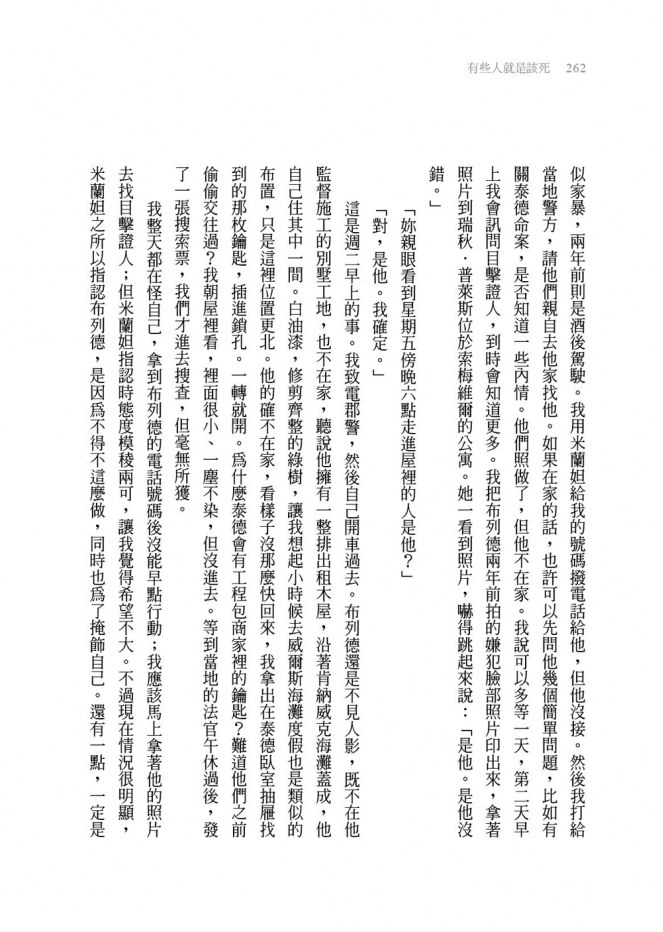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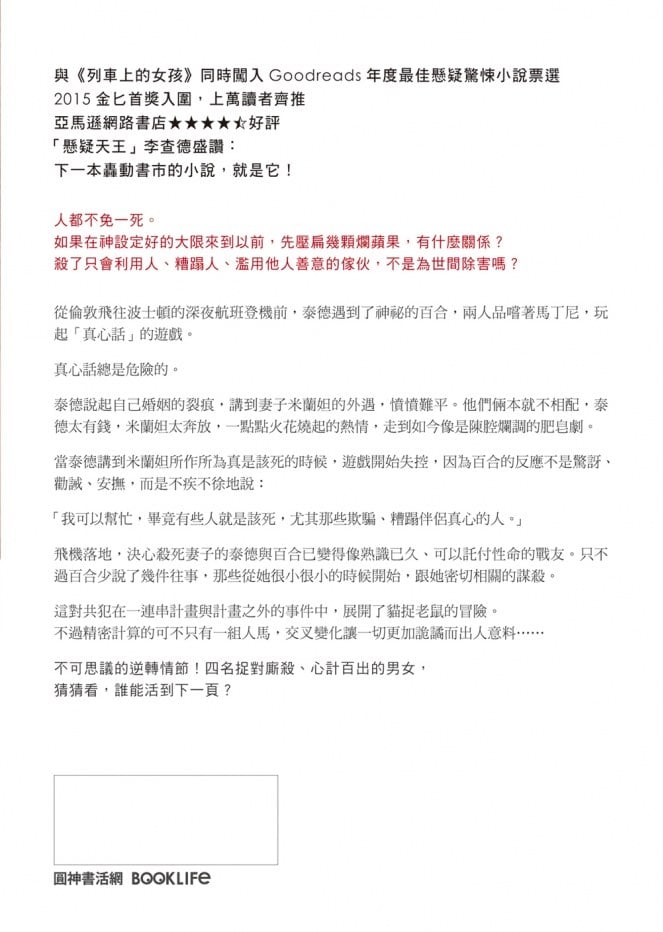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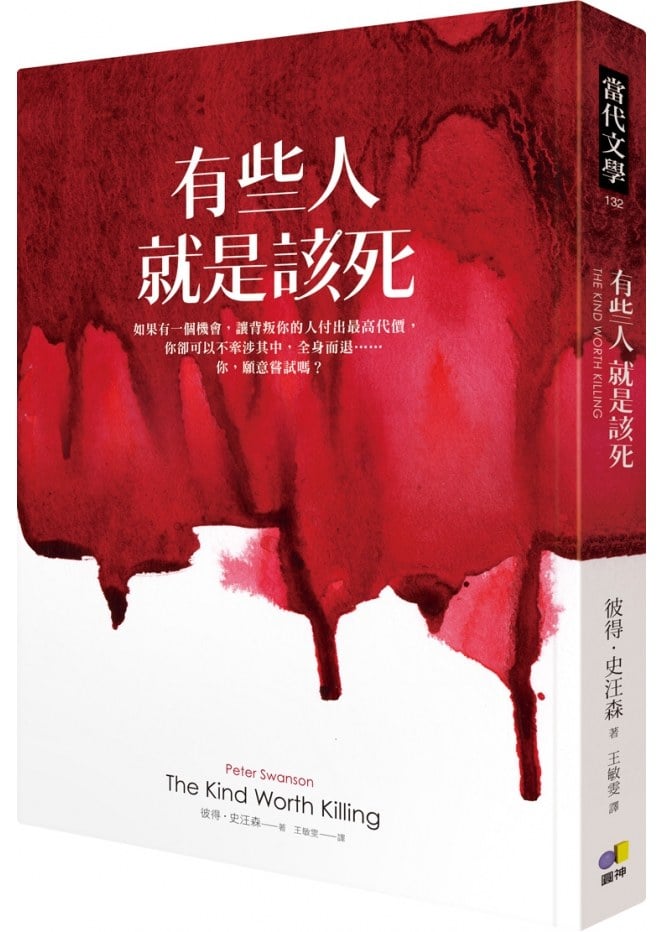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