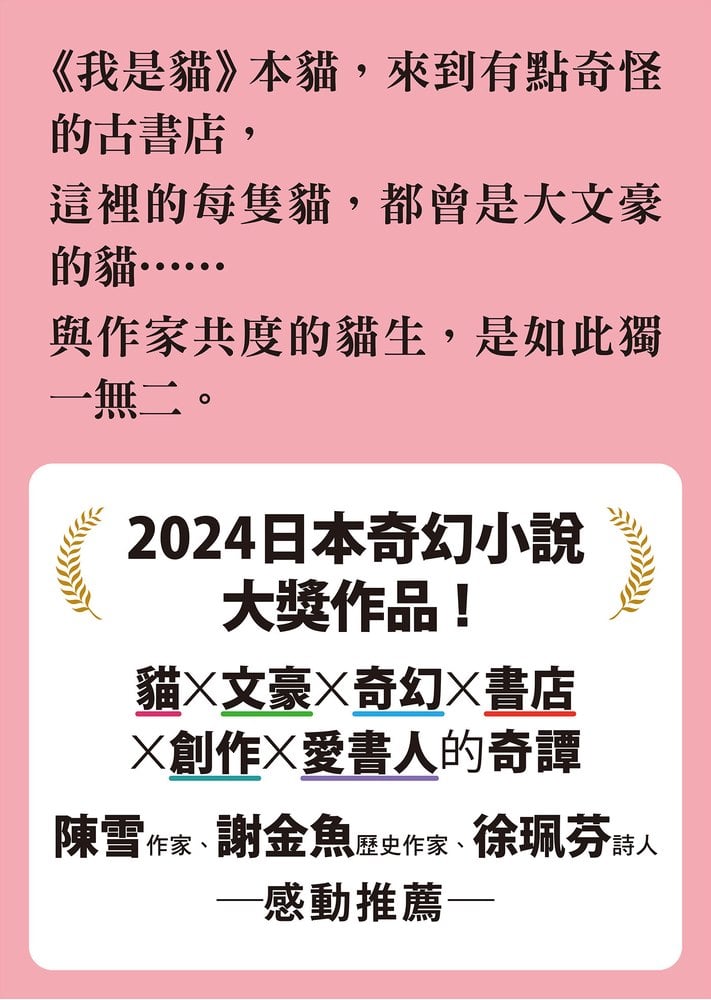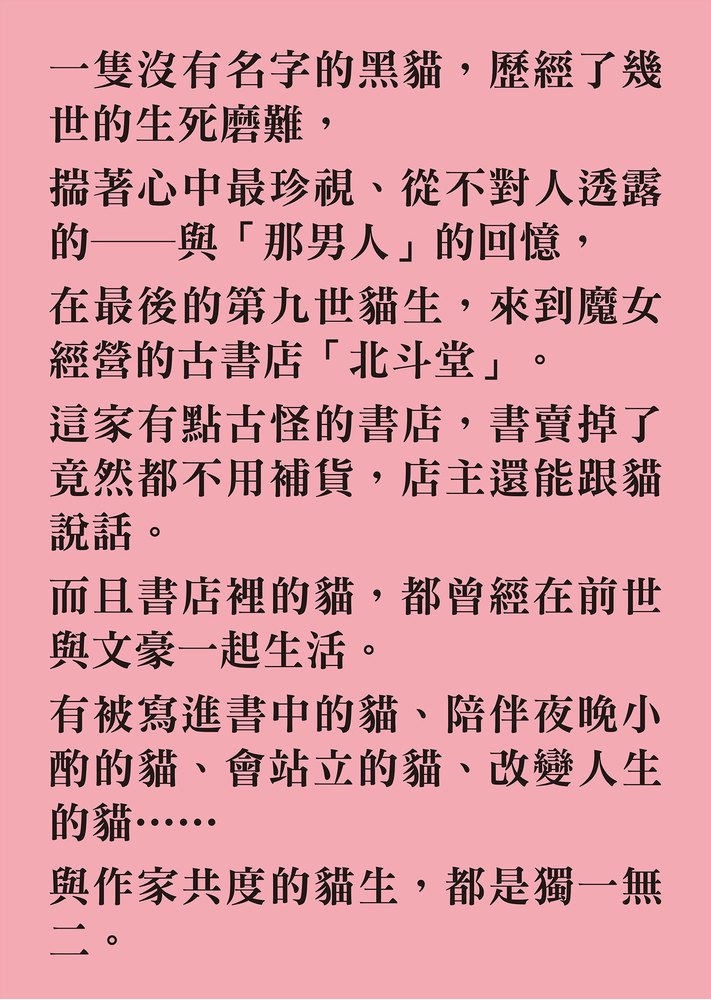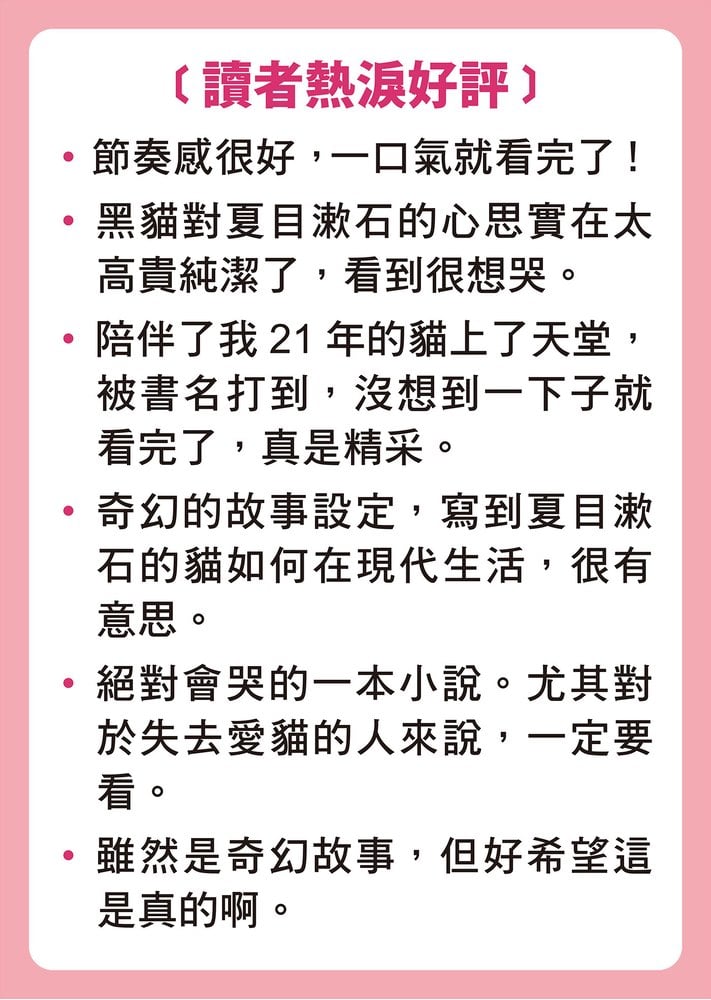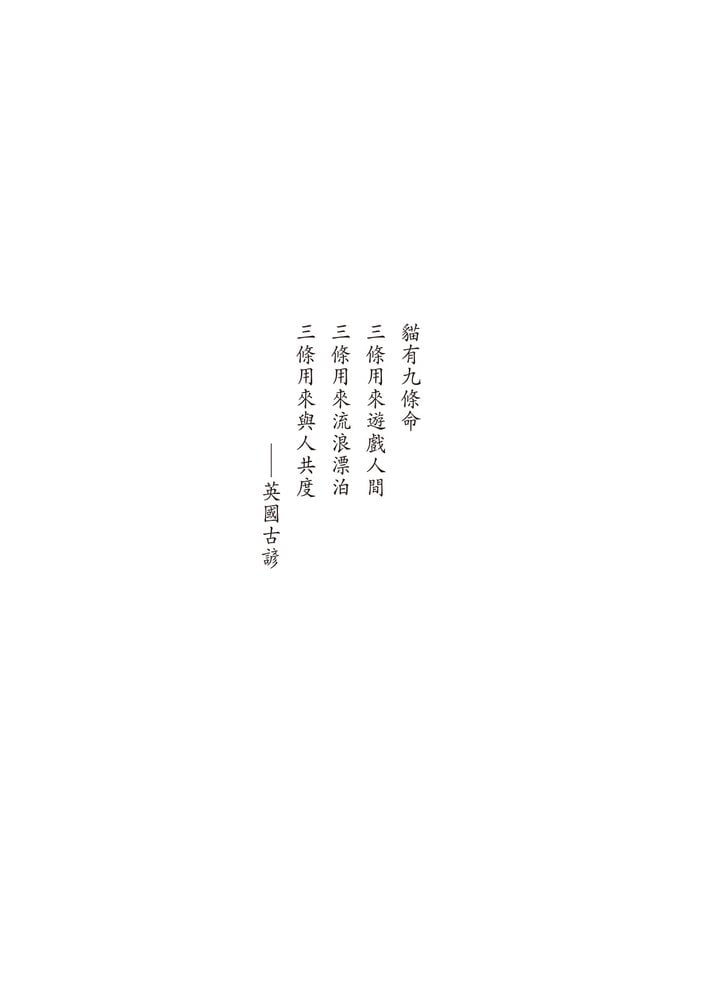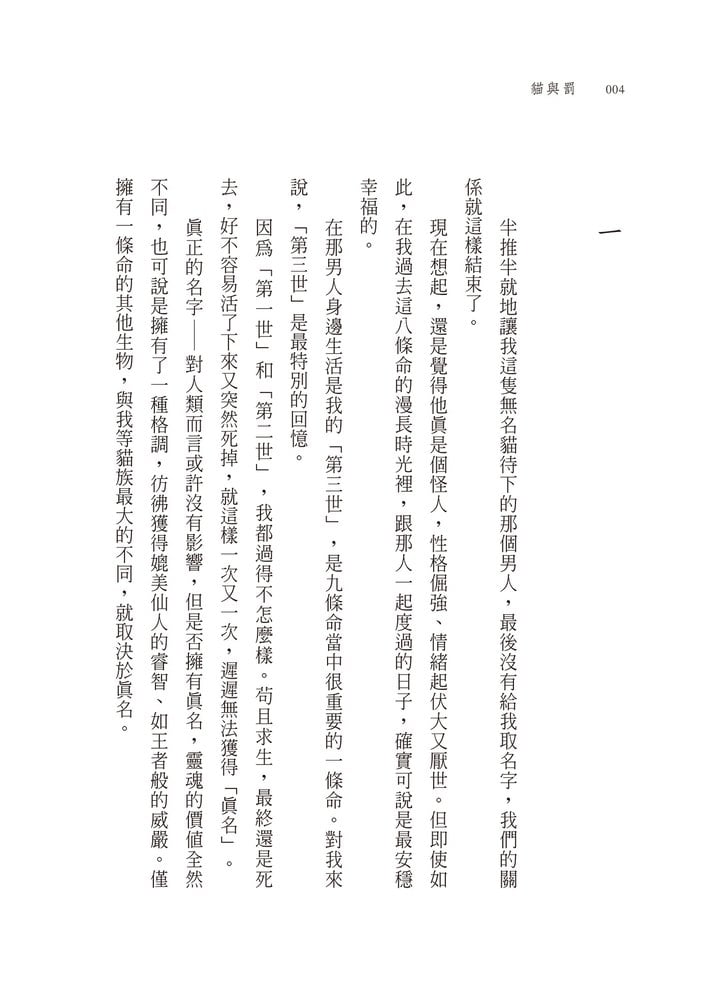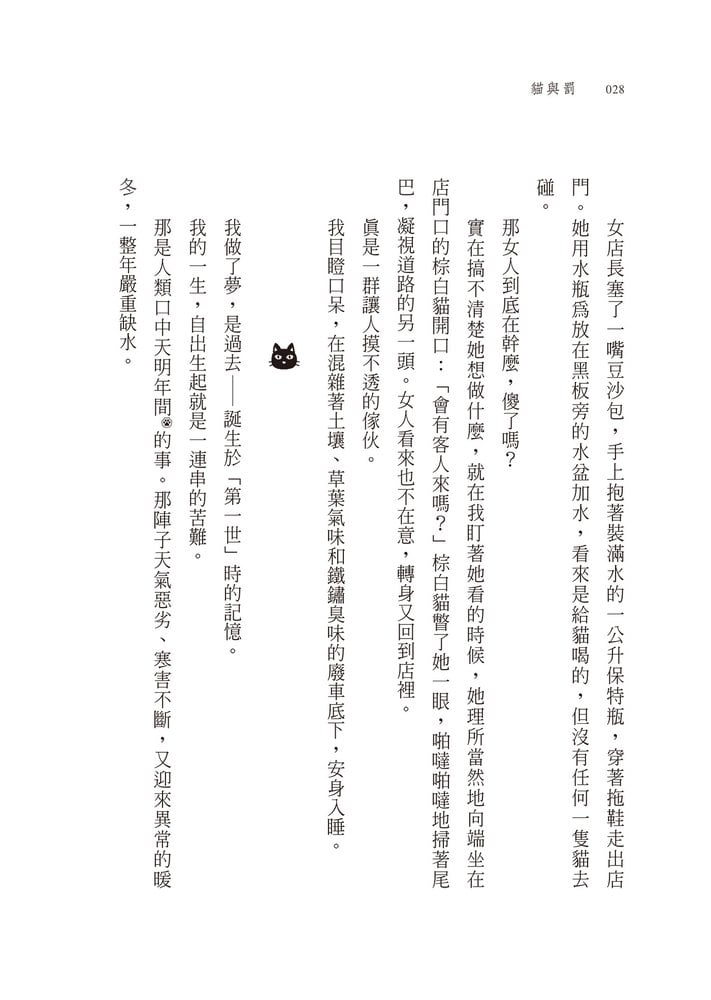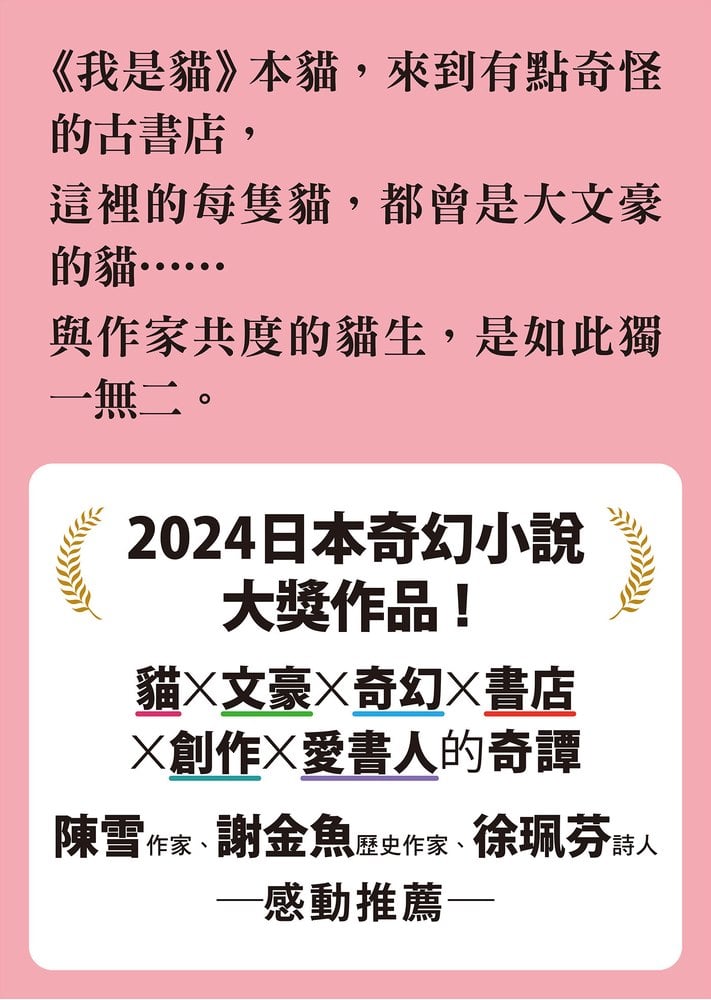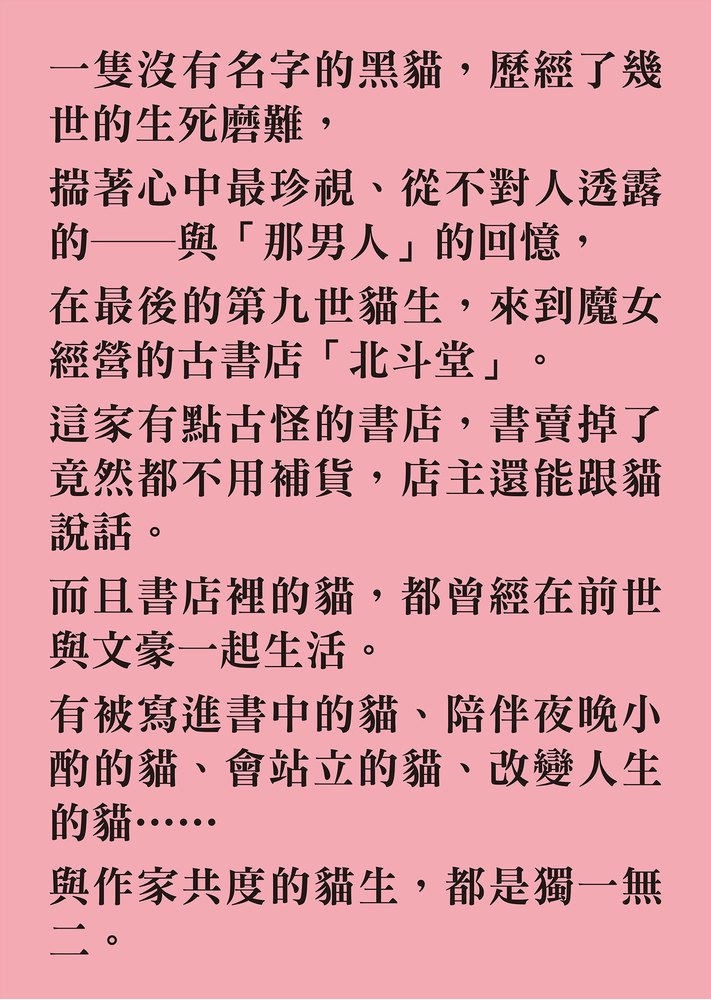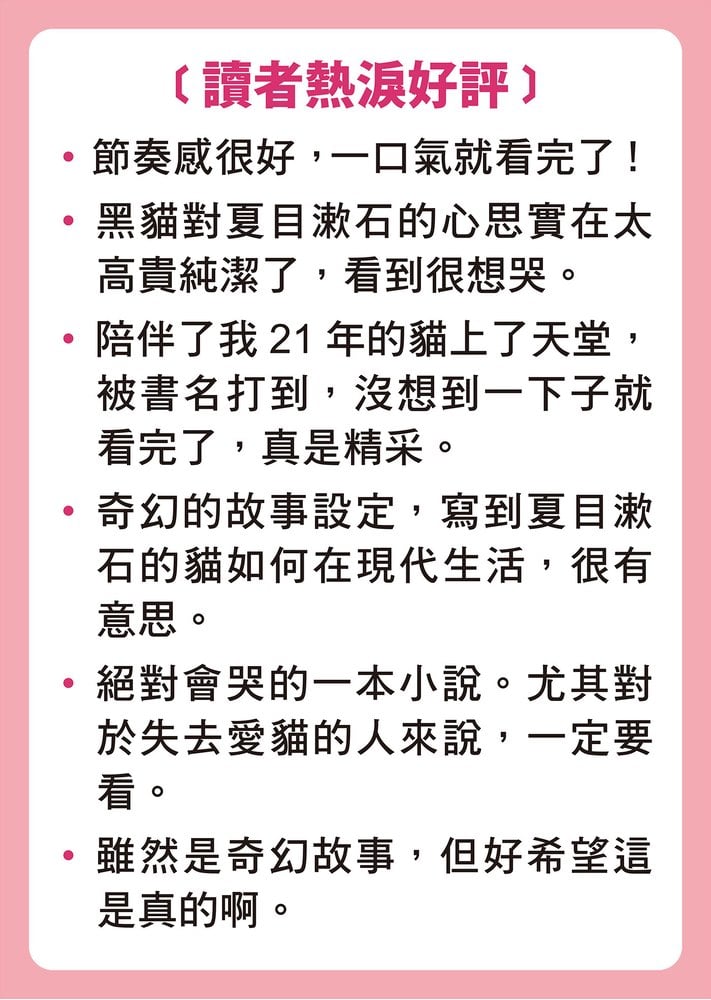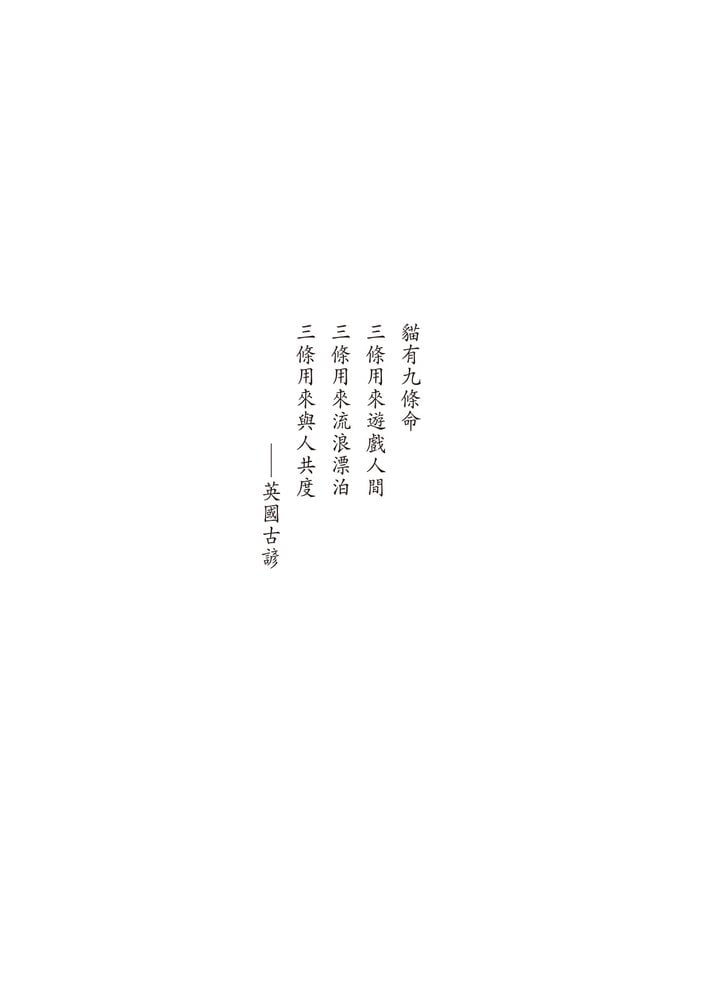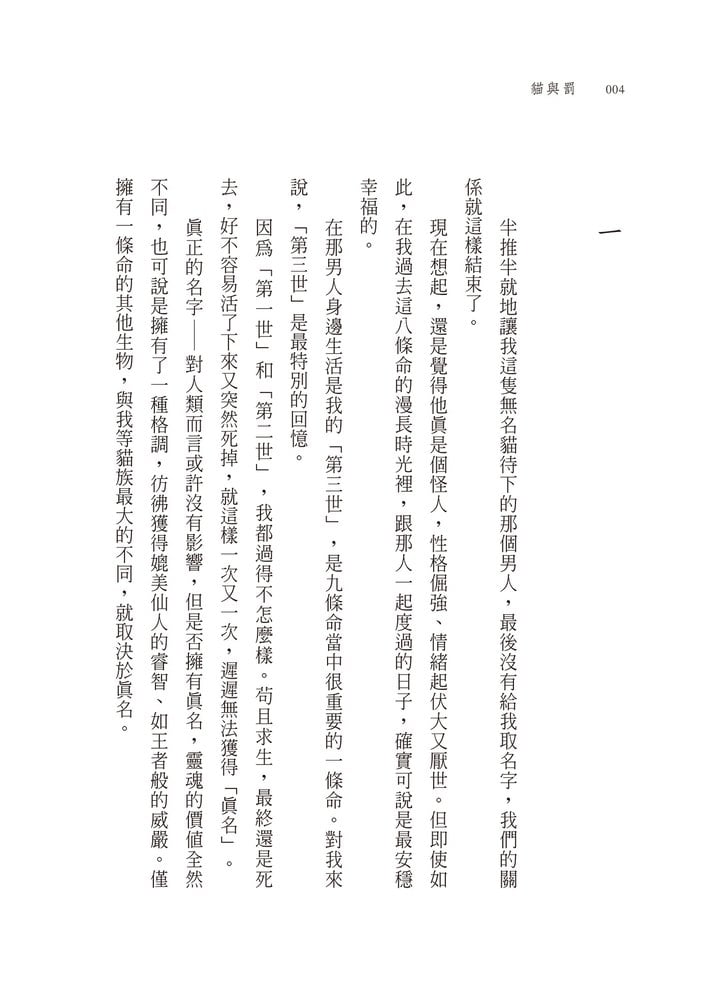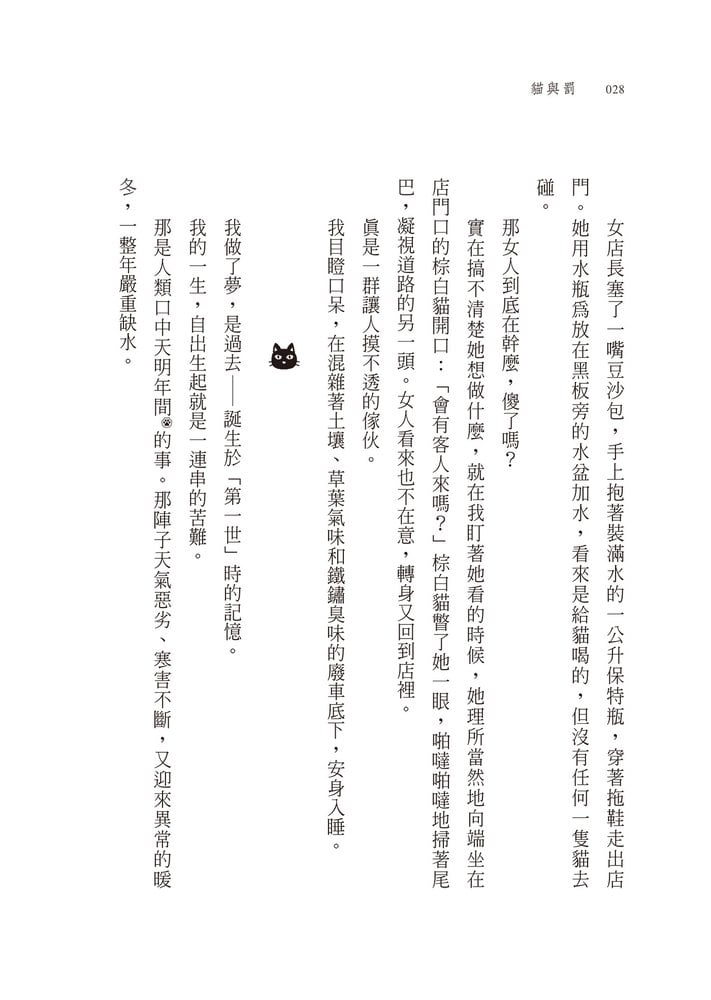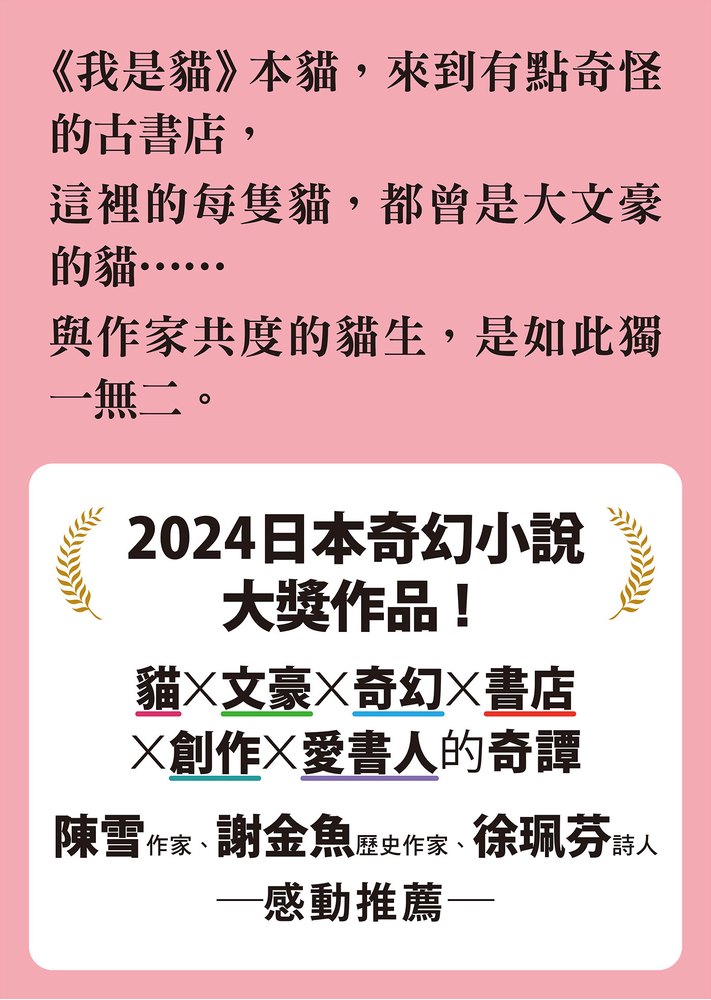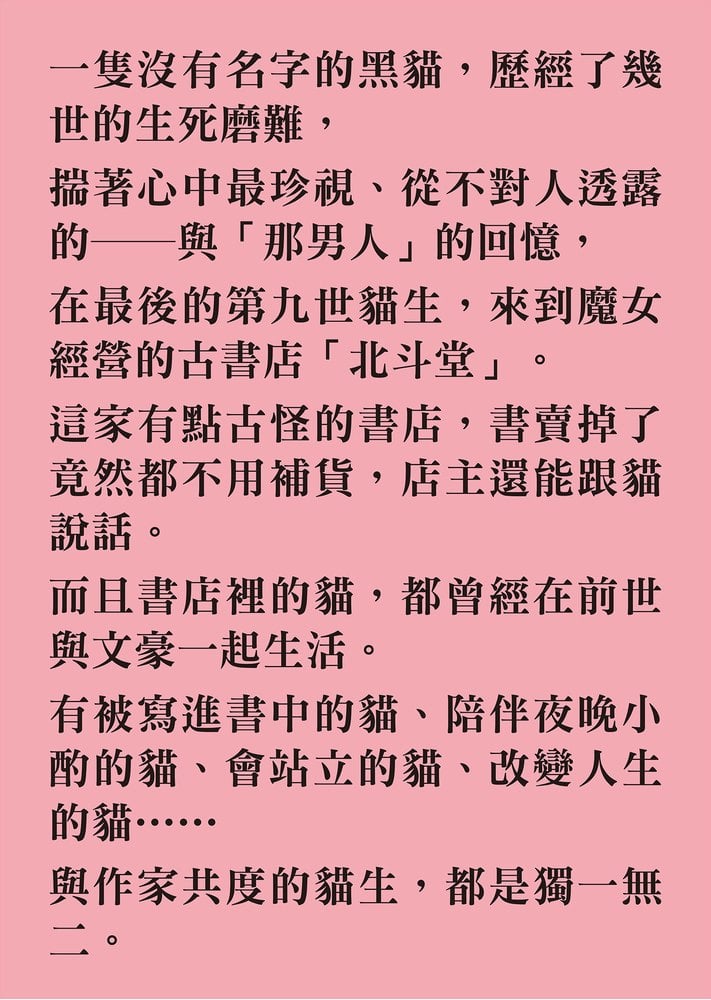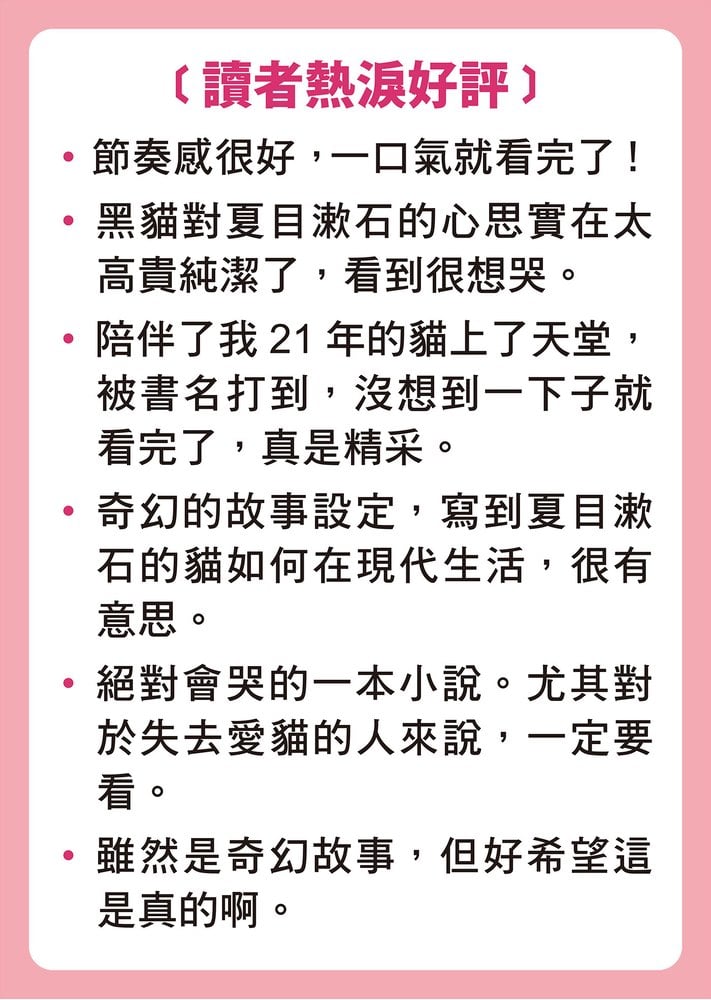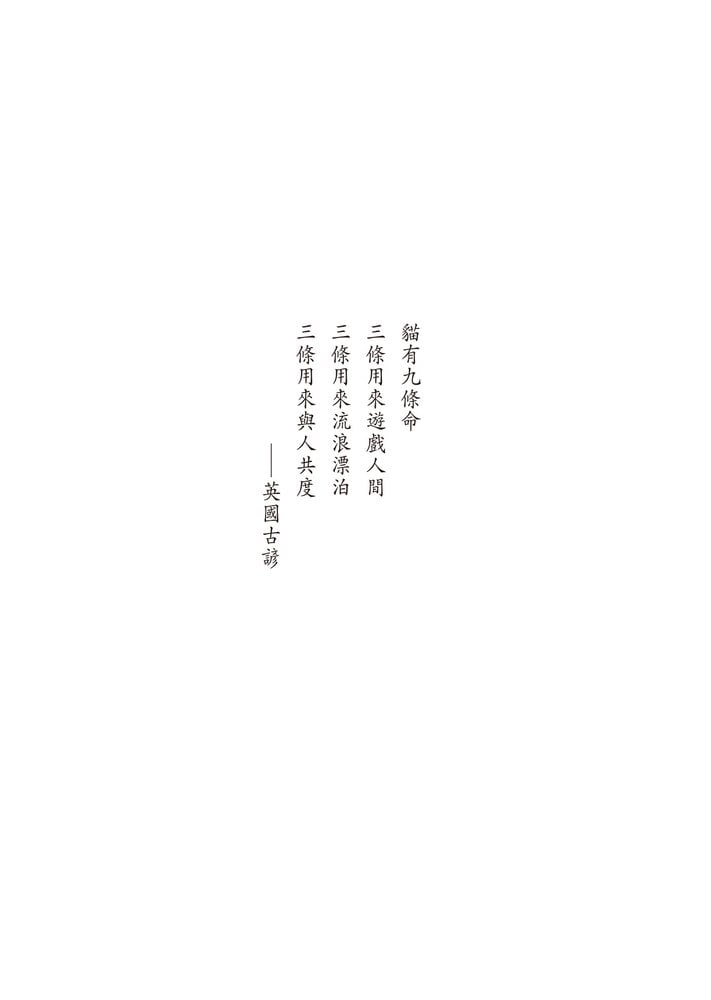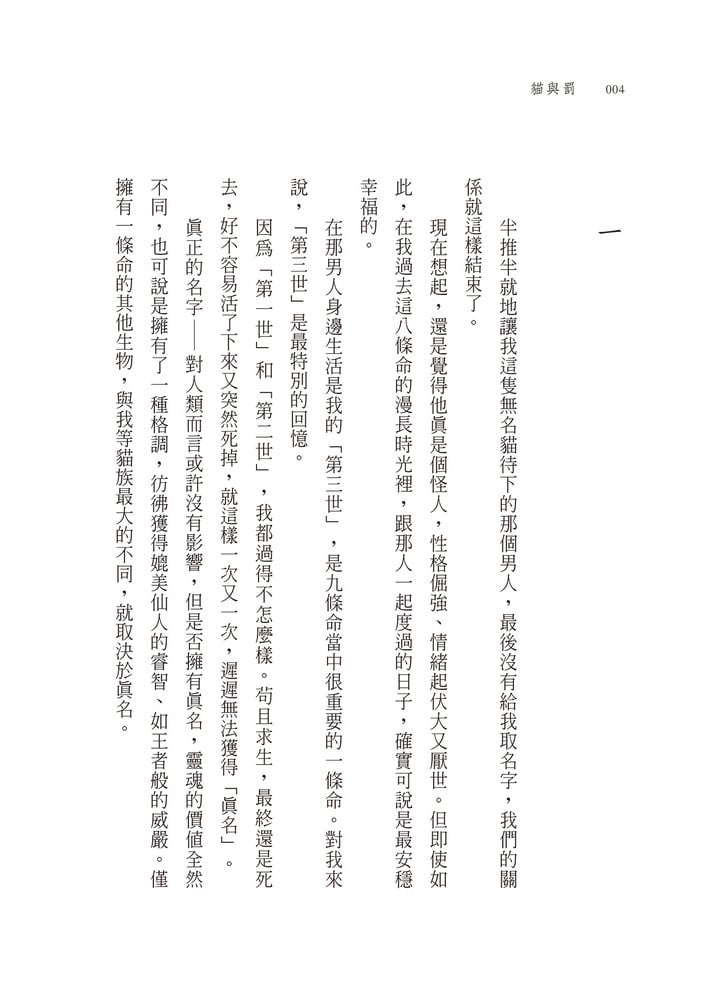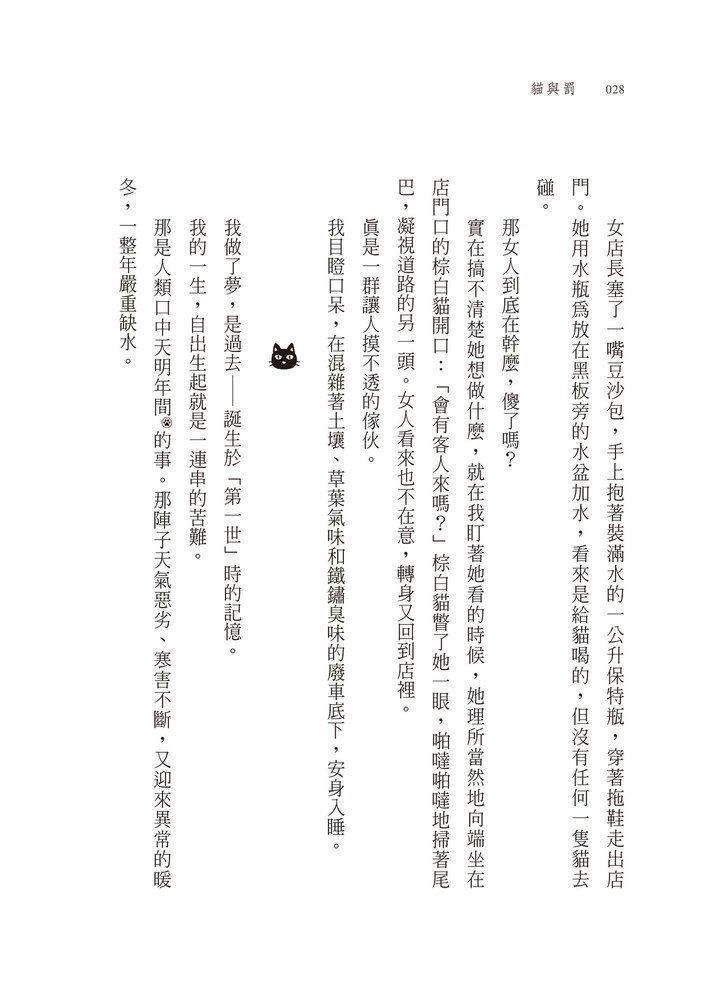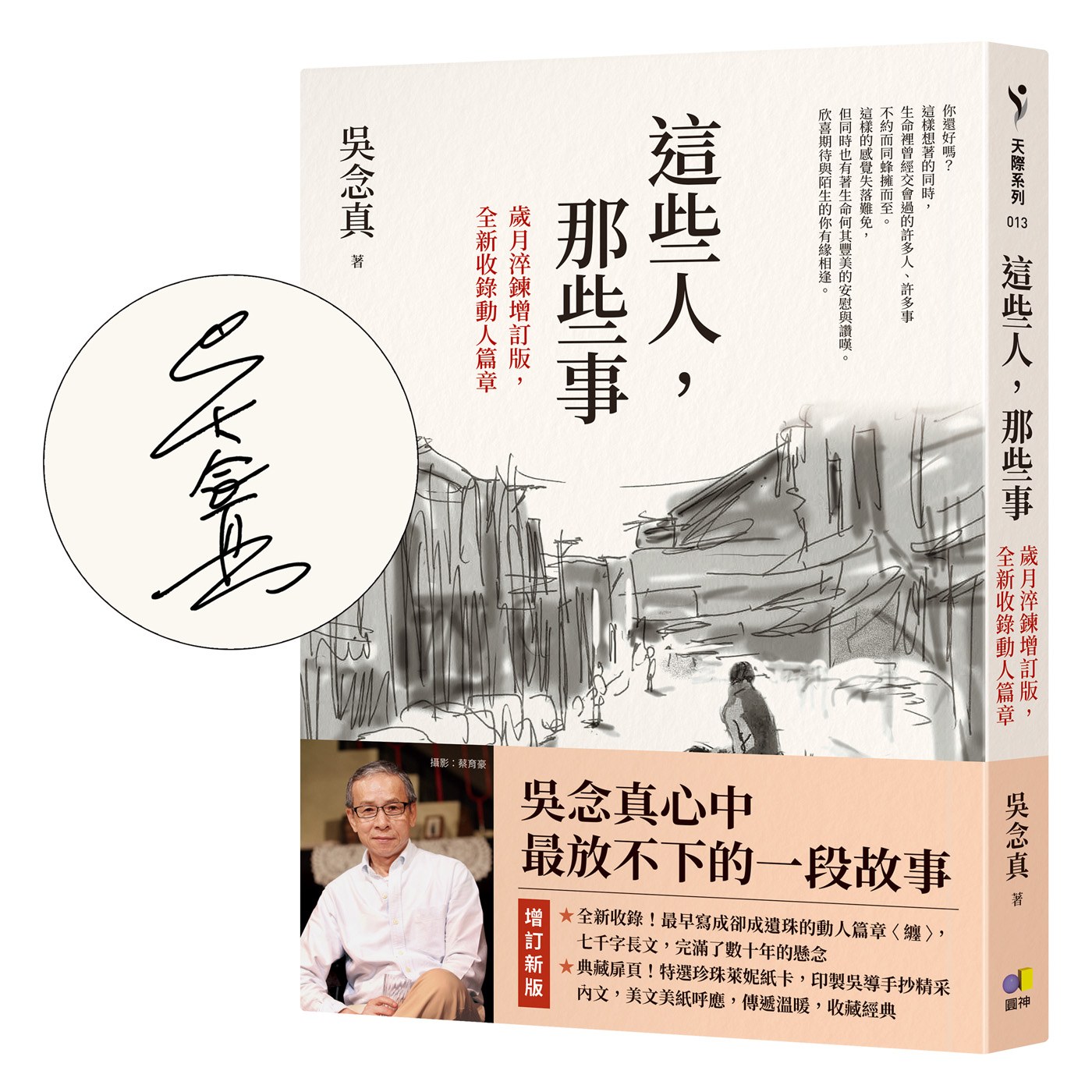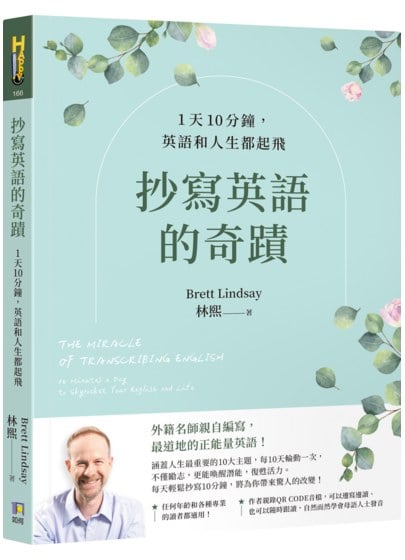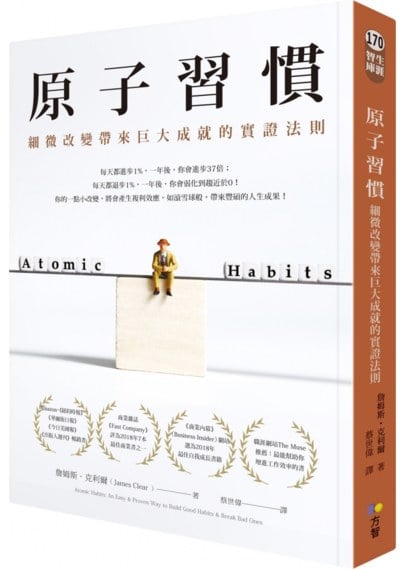半推半就地讓我這隻無名貓待下的那個男人,最後沒有給我取名字,我們的關係就這樣結束了。
現在想起,還是覺得他真是個怪人,性格倔強、情緒起伏大又厭世。但即使如此,在我過去這八條命的漫長時光裡,跟那人一起度過的日子,確實可說是最安穩幸福的。
在那男人身邊生活是我的「第三世」,是九條命當中很重要的一條命。對我來說,「第三世」是最特別的回憶。
因為「第一世」和「第二世」,我都過得不怎麼樣。茍且求生,最終還是死去,好不容易活了下來又突然死掉,就這樣一次又一次,遲遲無法獲得「真名」。
真正的名字──對人類而言或許沒有影響,但是否擁有真名,靈魂的價值全然不同,也可說是擁有了一種格調,彷彿獲得媲美仙人的睿智、如王者般的威嚴。僅擁有一條命的其他生物,與我等貓族最大的不同,就取決於真名。
若是本就不打算擁有真名,那也就罷了。但沒有真名的貓,只是愚鈍無知的芸芸眾生,不管把九條命重複活幾次,都無法跳脫野獸的範疇,不過就是可悲的靈魂。
能越早得到真名越好,但以我的狀況而言,沒那麼容易。所以在得到「第三世」的生命時,無論如何都希望那男人能為我取名。
但他實在是太漫不經心,都特地收留我了,卻把我丟給老婆照顧。他跟老婆以外的家人說話時,要不是大發脾氣、就是滿不在乎地說人壞話。
跟到這樣的飼主,我的「第三世」還是沒能得到名字就結束了。到了「第四世」仍沒有名字,實在無法展現我的格調。
──沒辦法,我決定借用那男人的名字,自稱「金之助」。
但之後我依然沒機會用到這個真名,下一條命、再下一條命,都白白度過。再下一條命、以及再下一條,也一樣。
到了「第八世」,我終於領悟到活著是多麼空虛的事。
人類總是把「活著」想得太困難。大部分的動物只要吃頓飽飯、睡個好覺就很幸福了。可以不用擔心飢餓、不用怕被吃掉地活著,這樣就好了啊。
但大部分的人類要不是說需要錢、再不然就是追求人生意義,還真是不自量力。在他們之中不知有多少人為此所苦。
而絕大多數把遠大夢想掛在嘴邊的人,最終什麼也沒達成,就這麼死了。
夢想這種東西,根本就不該擁有。
遇見災厄時,無須反抗,只要順其自然,一切不過就是運氣。就算身邊多重要的傢伙死了,也與我毫無關聯──這麼想就輕鬆多了,所謂達觀,不就是如此嗎?
那個男人也是因此染上心病的嗎?
我時不時回想,卻沒有答案。反正貓無法理解人類的想法。
就像人類也無法理解貓的想法。
「第九世」,最後的一條命。
不管將會以多麼淒慘的死狀結束這一生,「第九世」真的是最後了。我已經下定決心,不再對任何人抱持任何期待,只要漠然地活完就好。
對我如此消極的決心一無所知的母親,就像對待哥哥姊姊們一樣,仔細舔舐我的身子,百般疼愛。
那是在神社緣廊底下,當時下著雨,帶著一絲寒意。我渾身發抖,身子沒有淋濕,但一時間想不起前八世累積的知識與經驗,那股寒意挑起了本能的恐懼。
母親像是要安撫我似的,持續舔著我的身子,姊姊和哥哥也總是依偎在我身邊。不管降生於哪一世,這份無條件給予的溫暖與關愛總是不變,但我也深切地明白,不久後就會失去這一切。所以我並未向他們撒嬌,只是沉默地由著他們。聽著雨水打在土壤和樹葉上的聲響,這天我很快就睡著了。
黑暗潮濕的神社緣廊下方,是我們一家子的安身之處。
母親、兩個姊姊、一個哥哥,他們的毛色都是橘虎斑或棕虎斑。唯有我是一身黑毛,連肉球都是黑的,母親對這樣同一的色彩十分讚嘆。
「黑黝黝的真漂亮。」
大姊也這麼說。但對我來說,這毛色已經跟著我幾十年,一點感覺也沒有。看我這麼冷淡,哥哥抱怨:「真是不可愛。」逕自舔起了毛。
吸著母親的奶,過往的記憶慢慢復甦。每當回想起來,重複了一次又一次、過去八世的記憶,再次烙印在腦中,我對他人的警戒心就一層層加強。就連對原本該坦然交心的母親和兄姊也是。
即使如此,他們依然沒有棄我於不顧,還是對一點也不可愛的我百般疼愛、照顧。觀察著他們,我茫然地想著──
母親對孩子傾注毫不保留的愛。這份不求回報、無條件的愛,或許是不變的共識吧。這樣的愛養育孩子、帶來活下去的力量,傳承到下一個世代。這確實是無私奉獻的行為,也是一種亙久的大愛。但這真的是愛嗎?
愚蠢至極。持續到永恆的愛,最好是存在。這不過是同胎手足的記號所誘發的義務性舉動罷了。
我迄今為止的每一條命幾乎都悽慘落幕,在我看來,真實的愛不過就是虛妄的夢話。
把無謂的事全都忘了、全部無視,才是生存的法則。從這一點來說,我們貓族在求生上,比人類要來得聰明多了。
……所以我再也不打算受到誰的照顧了。
不要再管我了。
我已經受夠人類了。
我出生時,正是梅雨時節。
地點並不清楚,不過似乎是某個鄉下地方。從小山向下望,看得見田園連綿的山間四散座落的民宅。這座神社建造在白天鮮少有車輛通行的小山森林裡,罕有人煙。鬱鬱蔥蔥的茂林中,篩落的點點日光溫暖舒適,與從前住在東京時的喧囂與異臭無緣,這片大地充滿芳醇的土壤和水的氣味。
成為我們基地的神社,就是如此宜居的場所。只不過時時會有像是神社管理員的男人過來,在我們頭頂上乒乒乓乓地打掃。他似乎討厭所有動物,也包括貓。母親說,她曾經經過那男人家附近,被他凶狠地追出來趕走。之後,母親就不斷地告誡我們「絕對不能被他看到」。我想起從前虐待我的男人的樣貌,不禁渾身發抖,一直遵照母親的忠告。
危險的地方、不能去的地方,我一面記住這樣的地點,以神社為中心,在山裡與家人一起四處徘徊、尋找食物。這片陌生的土地慢慢變成了我們的庭院。
就在這樣的習慣根深柢固的六月底,走在日光下會開始感到不悅、地面燙得受不了,我們自然而然地在神社緣廊下度過白天,傍晚到夜裡才外出尋找食物。
我們也差不多來到該戒掉母乳、開始吃固態食物的時期了。母親開始在遊戲中教我們狩獵的方式。
我畢竟有前八世的記憶和經驗,其實沒有什麼需要學的新知識。我不曉得母親和兄姊是第幾世,我們貓通常也不會特別去提,只是感覺得出我的狩獵技巧比兄姊來得好。
只不過小貓的身軀實在精力旺盛,跟成貓的狀況不同,想下手輕一些便太弱、想出點力則太大力,記憶和身體的動作總對不上。為了找回感覺,再怎麼不樂意,我也只能陪著大家一起玩。
也不曉得姊姊們知不知道,她們從不曾對我多說什麼。看到母親的尾巴拍動著,我無法壓抑本能地撲上前去、努力想用兩隻前腳抓住,而她們只是靜靜看著我度過這樣無意義的時光。有時我大力拍打、啃咬,她們也只是用前腳輕輕把我撥開。
捕蟬、捕野鼠、喝河裡的水、有人靠近就逃跑躲起來,不得已要到村子裡時,就得小心車子。
這樣理所當然的事終於成為習慣、內化為本能的時候,大姊在某個傍晚散步回來,語帶興奮地說:
「跟你們說喔,我找到可以要到飯的地方了。」
她說隔壁山腳搬來一戶新的人家,將空了許多年的屋子重新改裝,住進裡頭。
她在附近農道的樹蔭下午睡時,生面孔的人類餵飯給她。
他們應該是從都市來的人類吧,看到野貓覺得稀奇,毫無「貓會在田裡拉屎、還會偷魚乾,是可惡的小偷」這種對附近農民來說是常識的認知。
對野生動物來說,沒有比不花力氣就能吃到飯還更簡單、更確實的覓食方式了。對此,母親、哥哥和二姊都非常開心,說著明天就一起去吧。我連忙阻止他們。
人總有一天會離開,會餵野貓的人也會輕易捨棄野貓。一時興起就對動物百般疼愛、一覺得麻煩就毫不在乎地丟掉。每天的糧食要仰賴這樣的生物取得,實在是太危險了。我拚命說服他們。
但不只哥哥姊姊,就連母親都似乎對我說的話毫無概念。
「不用再自己獵食,也不用挨餓了啊?」
他們只想到眼前的事,完全無法理解我說的話。
這一刻我才終於明白。
他們全都是「第一世」。
他們完全不懂人是多麼三心二意的存在,這樣的生活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如此難以置信的樂觀,在在顯示出他們對於與人類互動,懂得比我要少得多。
遲鈍、無知又愚昧。但聰慧如我心知肚明,就算吐露內心翻湧而上的怒氣和厭惡,也留不住他們。
自隔天起,我的家人白天都在會餵飯的人家附近度過。他們找我一起去,我也堅持不肯,依然留在神社的緣廊下。
啊,又來了,又是這樣。
相信的人事物最終都會離開,也該放棄了吧。明明已經這麼告訴自己無數次,內心深處還是隱約期待著,這次說不定不一樣。就連到了「第九世」還是這樣。
是無條件付出的親情導致?或是每當轉世,記憶就會被推向遺忘的彼方造成的呢?再怎麼不甘心也無濟於事。
我依然自行獵捕蟲鳥,怠惰的家人則是每天來來去去,前往人類的地方。
……就這樣,不知從哪天起,他們便不再回神社了。
到了夏末,我的個頭大了一圈,已經可以靠自己獵到足夠的食物了,我的家人還是沒有回來。
我不知道理由。雖然不知道,但很明顯是因為跟人類太過親近了。
是被人收編了嗎?然後我被他們拋下了嗎?
想這些也沒意義,我就只是窩在以夏天而言太過寒冷的緣廊下方,決心過著與孤獨共眠的日子。
我沒想過要被人類收編,也沒想過要去找家人。說穿了,到頭來大家都得獨自活下去。依賴就輸了、相信就輸了。要是忘了這一點,我的心一定會深深沉進黑暗中、傷透了吧──我這樣說服自己。
那樣的孤獨,我深深明瞭。
炎熱的夏天也緩下勢頭,森林中吹過的風開始帶著微微涼爽。
我的體型變大之後,開始躲進神社後方森林的樹叢中睡覺。四面通風的緣廊下方只有我一隻貓,實在是冷得受不了。
我也曾溜進神社內度過夜晚,但白天實在待不住,不知道那個討厭動物的男人何時會來,總是靜不下心。
而且我也開始對這個地方膩了。
沒有家人的溫暖,只是虛度每一天。最重要的是,只剩下我一隻貓在這兒打發時間,實在太無聊了。再加上離山或海近的地方,接下來進入秋冬季節會非常寒冷,怎麼想都不覺得我可以在神社底下悠哉度過。
正思量著該怎麼辦的時候,我想起過去幾輩子有那麼幾次,曾經短期受到生活在都市的人類照顧。大多數的人類都會群聚生活,所以在大的聚落裡冬天相對溫暖。都市的惡臭較鄉下嚴重得多,但總比凍死在路邊好太多了。
我決定前往市區。
不過倒是不必到需要跨越縣境的遠方,要是去比這裡更冷的地方就沒意義了。
我填飽肚子,小睡片刻,趁著夜色下了山。總之先往南去吧。我踩著還有些濕軟的碎石子路向前走。
月亮缺了左半邊,將夜晚照得通亮。即使如此,我漆黑的身子還是能融入夜色中。應該不會被麻煩的野獸或人類發現,可以順利穿過山路和農道前往市區吧。
大片的田園傳來蟲鳴聲,彷彿大合唱的鳴叫,對我們貓靈敏的聽覺來說真是吵到不行。連青蛙也叫起來的地方,比森林還吵鬧。我很想趕快通過,但田園彷彿無止境地延續著。
一心一意地走著,我的念頭自然而然飄到消失的家人身上。僅僅不到三個月的短暫相處,卻在內心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想來就氣。
──你要去哪裡?
我彷彿聽見母親的聲音。
猛地回過頭,眼前是我走過的沒有道路的路徑,以及一整片寬闊的田野。在那彼方,有幾間還亮著燈的屋子錯落其中。原先就不密集的房子,看起來更加空蕩蕩。
我突然想起「第七世」的事。
我對人類感到絕望,轉世後就出生在一座貓居住的島嶼。人類稱這裡為貓島,電視節目也特別報導。許多人來島上無謂地戲耍我們,還有不負責任的人,大老遠把不想養的貓帶來這裡丟掉。就是這麼一個像垃圾場的地方。
我的「第七世」在那裡度過一生。對人類已經毫不信任,也無法融入同類,只是孤獨地活著。就算身邊有再多貓,我也從不打算跟誰拉近距離。看著疏落的燈火,那段時光的回憶鮮明地在腦中甦醒。
如今我隻身一貓,獨自前往城市。自由自在地活著,就是這麼回事。
寒冷的夜風吹得我渾身發抖,催著我加快腳步離開村莊。
結束了看似漫長實則短暫的夜晚,依然沒見到市區的影子。
以貓的腳程,光是要從山間的一個村落到另一個村落,就是一段苦旅。走了一整晚,目的地還是遠在天邊。氣溫逐漸悶熱起來,呼吸著混雜草葉和土壤氣味的空氣,我持續走在彷彿無窮無盡、綿延的鄉間道路上。瀰漫朝霧的潮濕空氣包圍著我。
此時,遠方依稀傳來引擎聲。
我連忙離開道路,逃進樹林的草叢中躲起來。從草叢中往我走來的方向望去,一輛老舊的發財車顛簸地開了過來。車身遍布泥土髒污,載貨台上堆著農具和蔬菜。發財車在一段距離外停下,駕駛的老頭仗著四下無人,下了車就在路邊解放起來。又不是野貓,真是沒教養的男人。
這個沒品老頭的長相我有印象。他一星期有幾天早上會開發財車,到市區車站附近的無人蔬菜商店補貨,是一個農家老頭。忘了是什麼時候,應該是溜進他們家,偷吃曬在院子裡的魚乾時的事。我跟大姊在他家院子,聽他跟家人抱怨年紀大了,在路邊小便越來越難順利解放。
總之,只要搭上這輛車,就能載我到市區。
我不發出一點聲音竄向車子,輕巧地跳上貨槽。在充滿泥土氣味的蔬菜環繞下,我鑽進農具的陰影中,蜷起身子。
不久後,解放完畢的老頭再次發動發財車。嘈雜的引擎聲伴隨惱人的震動,將我連同蔬菜與農具一同載往市區。不知是不是一下就適應了劇烈的晃動,我還稍微小寐了一下。
睡了一陣子,發財車停了下來。
我睜開眼,往載貨槽外頭張望。
聞不到泥土和樹木的氣味,也聽不見蟲鳴。從載貨槽望出去,看不見遮掩天空的山,只是極其平凡的住宅區。一如所料,這裡比森林溫暖多了,但相較之下空氣並不太清新。不遠處傳來電車駛過、車輪撞擊軌道的聲音,吵得不得了,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老頭打開載貨台的檔板,取出幾份蔬菜。我躲在農具的陰影中偷看,確認他轉身背對發財車、依序將蔬菜放上無人商店的貨架,我悄悄跳下載貨台,再次走在道路上。
早上的市區雖不像農村那麼早起,也已繁忙起來,上百個人類像是被吸進車站中,前往各自工作的地方。為了避開人潮,我決定往票閘口相反的方向,鮮少人行走、小路交錯的彼方走去。
走在圍牆上,餘光瞥見聚集在鐵路及車站月台上的人類,我打從心底感到不可置信,所有人都低頭看著手邊的書報和手機,沒人注意到我這隻小貓。大家都只關心自己。
人類就是這樣,喜歡在這種讓人壓力升溫的密集場所行動,透過這樣的行為,勞動、賺取金錢,獲取每天的吃食。
人實在是奇妙的生物。不管轉世多少次,這個想法從未改變。
生而為動物,肚子餓了,自己去覓食就好。但這些傢伙卻有著莫名的矜持和尊嚴,愛充面子、找藉口,說什麼這樣才是理想中的自我,又是追逐夢想、又是奮力工作,然後搞壞身體,最終死去。
相較之下,貓真是聰明多了。依照本能行動的同時,關鍵時刻也能以知性和理性應對。因為有著「生存」這個行動本能,無暇顧及無謂的矜持。
現實就是如此冰冷無情,理想主義者難以存活。
經驗與本能這麼警告著我。
沒錯,我總是遵循本能。就算討厭人類,還是與之互動,乃源自於我對生存的需求。我沒道理要遵照他們定下的規則走。
所以,在這被日光照亮的住宅區,我順從自己的直覺,隨心所欲地走著──沒錯,就只是走著。
但不知為何,我的身子像是被吸引似的往某處前進。
好渴、好餓,但比起先捕捉蟲子或麻雀填飽肚子,我的腳步毅然向前邁進。
無關自身的意志,穿越道路、轉過彎、爬上坡道、走下階梯,就像是走在熟悉的路上。我持續邁步,彷彿有什麼在引導我一般。
然後,我在一間店鋪前停下腳步。
那是這年頭少見,個人經營的舊書店。
店門面向稍稍變寬的道路,木造的外觀看來十分老舊。小店突兀地矗立在住宅區,左側和對面都是空地,看起來就像只有這裡未曾隨時代演進,遭到孤立一般。
於此同時,陳舊的外觀看來又十分融入這片土地。
在那個男人的時代,這樣的舊書店理所當然──充滿紙張的氣味,書本雜亂地放在架上,只勉強保留一個人能通過的寬度。就只有架著遮陽棚、鑲著毛玻璃拉門的門口看起來稍微新一點,應該是以前重新裝修過,其他部分就這樣隨時間老化了吧。
那男人回家時,身上的衣服常常飄散這種店裡的氣味。我想起他總是板著一張臉,看起來百無聊賴、卻十分熱衷地讀著看起來很無聊的書。有時也會看到打盹,睡到口水滴在書上。
有個跟那男人明明一點也不像、卻散發著某種神似氛圍的奇妙女人,站在店門口。
她身穿褪色牛仔褲配襯衫的俗氣打扮,踩著拖鞋,拿著掃帚把店面旁邊樹上掉下來的葉子掃開。眼神凌厲、稍稍駝背,長髮隨手紮在腦後。年紀嘛,大約三十多歲吧。脖子上掛著勾了鍊子的眼鏡,眼鏡鍊上裝飾著木枡吊飾。實在是俗不可耐。
就連鄉下地方的現代女性都打扮得更得體呢!我忍不住想抱怨,但想想實在也沒必要對女人的外貌多作評論。只不過是個不值一提的冷淡女人,我為何要跟她扯上關係?
明明這麼想,我卻不知為何在那店門前、在那女人身邊,停下腳步仰起頭直盯著她看。
或許是察覺我的視線,女人看向我。眼神看來像是在瞪我,但她停下揮動掃帚的手,帶著一抹淺淺的微笑,向我開口。
她說的第一句話,實在非常奇怪。
「來得比我想的早呢。」
這人是怎樣?
有許多人會因為喜歡貓,單方面對貓說話,自顧自地表達好意,實在是麻煩得不得了。
但她說的話跟這些人又不一樣。她不改淡然的態度,轉身面向我,然後開口問: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腦袋正常的人類,根本不會這樣問問題。因為沒有人會期待貓做出叫聲以外的回答。不巧,我們並沒有能跟人類溝通的語言,根本不可能回話。
但這個女人直直地面向我、低頭看著我,等我回答。
那不是不期待回答的單方面提問。女人直盯著我的臉,動也不動,很明顯地,她在等我開口。
我的身子終於動了。我匆匆轉身跳上鄰家的圍牆,鑽進房子間的陰影中,拚命逃離女人身邊。
女人沒有追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