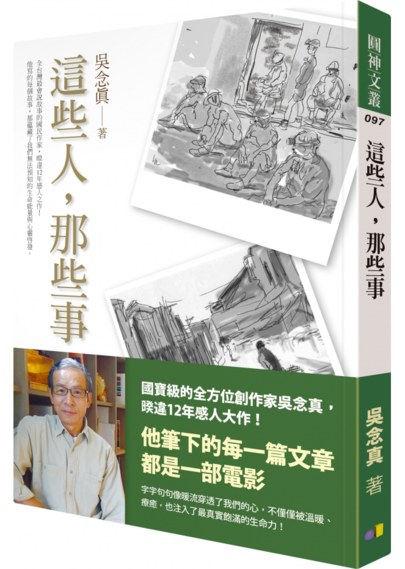五年級生、41歲才當爸爸的黃哲斌,突然發現自己對於做爹娘這件事,與當年的父母相較,很迷惘。
他回憶起自己的父母那代,平日忙著脫離時代的困頓,面對子女使用命令句,加上雞毛撢子或藤條,就能完成九成以上的教養任務。至於人生目標,上一代大多採取明確的數字管理,考幾分,第幾名,第幾志願,甚或退步一名打一下,對他們而言,這些最終能代換為大學聯招分數,以及畢業第一份工作的月薪數字。
但是現在當爹娘,親子關係像是量子力學一樣複雜。父母那一套顯得老舊落伍,命令式語句經常是無效指令,體罰子女則是羞羞臉的事。還要面對全新的親子教養哲學、以及全新的免疫系統醫學。
然而他終究得從自己的原生家庭探討,因為那些經歷,將形塑他作為一名父親,在日常無數親子時刻的決策或回應。這些迷惘與驚奇,便成就了《父親這回事》。
這一次,他談起了他的母親。他的母親,能幹精明,愛子心切,完全監督他青春期的交友狀況,當年沒有line沒有email,所有抵達信箱的香水信件一律查封,而他許久之後才知道,媽媽還一一造訪這些女生家庭,當面表達「請遠離我的兒子」的意見。經此一役,黃哲斌就很少跟媽媽說話了。
在這之前,他無力反抗的小學二年級,他的母親為了逼促他便當吃光光,決定親自到學校......。原來這只是他與母親愛恨交織的鬥爭前奏曲,就像電影《哈比人前傳》不過是《魔戒三部曲》六百分鐘史詩的開胃前菜。

當我有了孩子,變成一個超齡奶爸,有次在《天下》的報導裡讀到一個名詞,「直升機父母」,意指過度保護並介入子女生活的父母,他們像一架直升機,時時刻刻在孩子頭頂盤旋,引擎發出震耳聲響,偵察行蹤,監視日常舉動,透過對講機指揮兒女的人生去向。
若以此標準,我的母親不但是直升機父母,而且是一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配備夜視系統及兩具高馬力渦輪引擎,搭載三十釐米機砲與地獄火、響尾蛇飛彈,全天候待命,可隨時升空,攔截並摧毀她兒子的人生路障。
不,我不是開玩笑,我是認真的,帶點讚美及喟嘆意味。
自我求學開始,母親就展現她強大的陸空協調作戰能力,喔,我是指她的母愛。她到我的學區國小,打聽一年級哪個老師最認真、教學最嚴格,然後,拜託老師,拜託校長,讓我如願安插到她心目中的理想班級。
此外,無論她學針織,學緞帶花,學做串珠皮包,幾乎每位老師都會收到一個,一不小心,她就翩然降臨教室門口,展現她靈活的外交手腕,經常讓我想去撞牆,因為其他同學的媽媽,幾乎很少出現。
讓人佩服的是,母親為了讓我吃到新鮮飯菜,每天上午,她一面看顧藥房生意,一面燒菜做便當,中午快遞親送到校,順便與老師熱絡攀聊。
我童年最悲慘的一次經驗,與便當有關。由於我每天總剩下半個便當的飯菜,就急急閤上鐵蓋,跑到操場打棒球;母親屢次示警無效,有天中午,她送了便當,但未離去,而是拉來一張沒人坐的小木椅,一屁股坐在我身邊,接著拿出鐵湯匙,神色自若一口一口餵我吃飯,我只得張大嘴,像一頭準備奉獻肝臟製作鵝肝醬的法國鵝,當下,教室一反常態鴉雀無聲,只有同學吃吃竊笑。她把便當盒刮個一乾二淨,神色得意撂下話,日後我若不乖乖吃光最後一顆飯粒,她每天都會餵我吃便當。

當時我小學二年級,毫無反抗能力,只能變成全班嘲笑對象。有一位經常捉弄我的林姓同學,每到中午,就會站在教室門口,大聲說:「你媽來餵你吃便當了。」時至今日,我仍記得母親拿著鐵湯匙,用力刮著不鏽鋼便當盒的尖銳刺耳聲響,就像恐怖片《半夜鬼上床》系列裡,佛萊迪以利刃指甲劃過玻璃窗戶的音效,陪我度過童年的限制級夢境。
好吧,那是還沒有教養書籍、沒有親職專家的年代,沒人告訴我母親,她的越位行為嚴重犯規,應該紅牌驅逐出場,加罰禁賽兩場。對她而言,這是讓我每天吃光午飯的最佳行動方案。「愛之深,責之切」,只求達成目標,不擇手段,似乎是當時模範父母的共同信仰,只差沒把這六個字,直接刺青在子女背上。
整個童年與少年時期,我在母愛的戒護下生活,如果可以,我相信她很樂意留在學校當書僮,每天幫我磨墨,順便幫老師擦黑板。然而,母親是矛盾的,她又感染了某些西式教育的精神,上了小學,開始給我零用錢,每星期十元,教我儲蓄與理財概念,或者,她會邀請班上同學回家開慶生會;小五或小六,她就鼓勵我跟同學一起出門,到圓環附近的遠東戲院看電影、或到信義路國際學舍逛書展買書,「培養獨立生活能力。」她說。
我始終不理解,她如何調和這些矛盾,就像我無法理解「開明專制」的美妙,新加坡式民主、北韓人民很幸福、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早已在我家秘密實驗二十年。然而,當時的我還不知道,小學二年級的便當慘案,只是我與母親愛恨交織的鬥爭前奏曲,就像電影《哈比人前傳》,不過是《魔戒三部曲》六百分鐘史詩的開胃前菜。

圖:41歲的黃哲斌,連續收下兩次送子鳥的包裹。至今他始終慶幸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然而,母親治軍嚴謹的風格,並非一無是處。時至今日,我承襲了她的一些堅持,例如,小孩晚上九點準時上床,而且無論多睏多累,刷完牙才准睡覺;早上不許賴床,必定吃完早餐才能出門,寧可提早到校也不准遲到,這些囉唆細瑣的舍監守則,變成母親留給孫子的一點非物質遺產。
如今,我不時看見父母騎機車載著兒女上學,小孩坐在後座,一手環抱前座的大人,一手拿著麵包,邊打瞌睡邊吃早餐,那一刻,我會記起母親的鐵面無情,並微妙發現自己像是一只承載遺傳基因的染色體螺旋,默默背負一些家庭記憶的碎片。
另一方面,我又對抗著、積極打破母親的好學生守則,包括「全勤獎」的執迷。小學時,即使我感冒發燒四十度,照樣得抱病上學。當時,國語課本有個英國海軍大將納爾遜的故事,提到他與哥哥一起上學,有天遇上大風雪,哥哥打算半途折返,卻被納爾遜嚴詞勸阻,堅持冒著惡劣天候到校;我讀了這故事,心想:「哇, 如果我媽生在英國,應該會變成海軍上將。」
當然,母親不是一代名將,但她嚴格要求麾下的兩名小兵,無論如何,上學視同作戰,不准陣前逃亡。我的全勤紀錄一直保持到五年級,那年放寒假前,我的下腹痛了兩天,也彎腰抱著肚子上了兩天課,第三天,實在超出小學生的肉體忍受極限,半夜送進大稻埕馳名的徐外科,確診是闌尾炎,而且嚴重化膿,「已經發炎爆開」,醫生對我忍受痛楚的能力嘖嘖稱奇,立即推進開刀房手術切除。術後必須住院一星期,因為傷口未完全縫合,還留著一條橡皮管,讓腹腔裡的膿液排出體外,那次可割可棄的經驗,是我小學六年唯一的請假紀錄。
畢業典禮上,看著其他同學上台領取全勤獎,母親忍不住喃喃自語:「好可惜,差一點點。」但我一點也不覺可惜,我的手術傷口早已癒合,但因病情延誤過久,復元不易,巨大縫線爬在我的右下腹,像一隻被踩扁的蜈蚣。
現在,我偶爾會為兩個小孩請假,帶著他們去旅行,台中、花蓮、台東、南投、台南、墾丁、香港,每一段旅程,都夾帶一點逃離課堂的紀錄;年輕的母親若在場,一定搖頭嘆氣說亂來,那位投錯胎的英國將軍,會神情嚴肅搖著食指,唸起六字箴言:「勤有功,嬉無益。」
--摘自《父親這回事:我們的迷惘與驚奇》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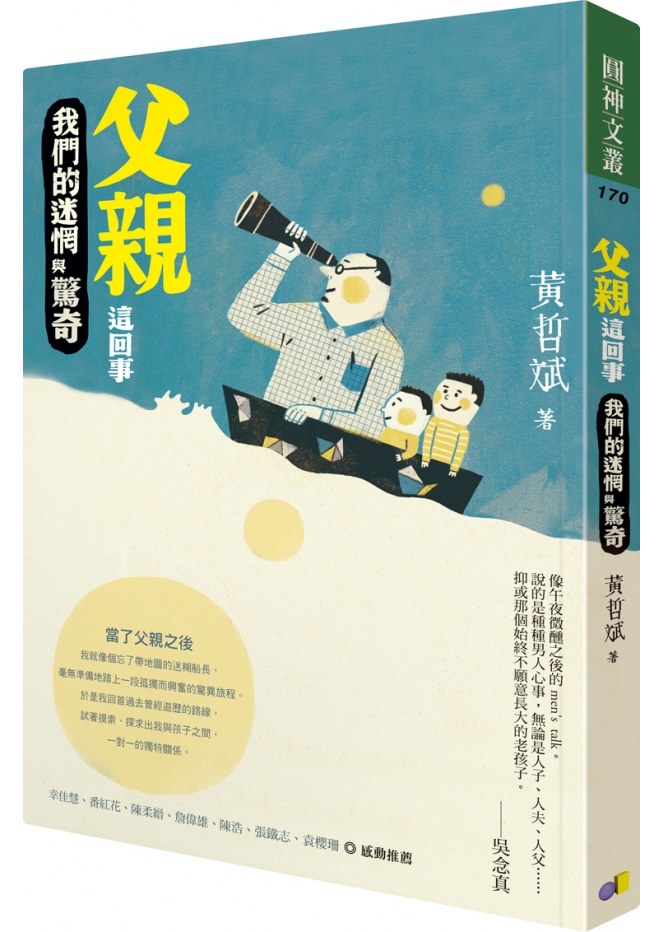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