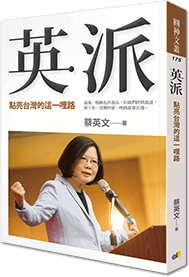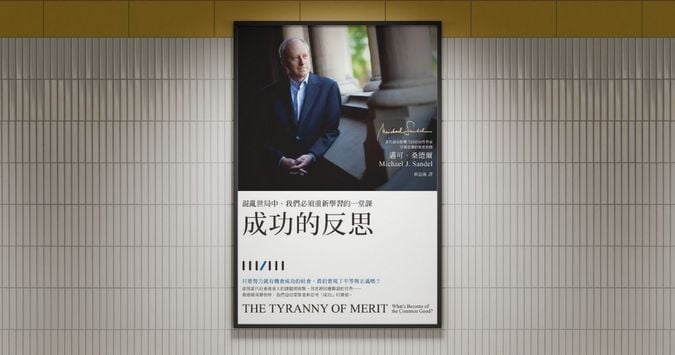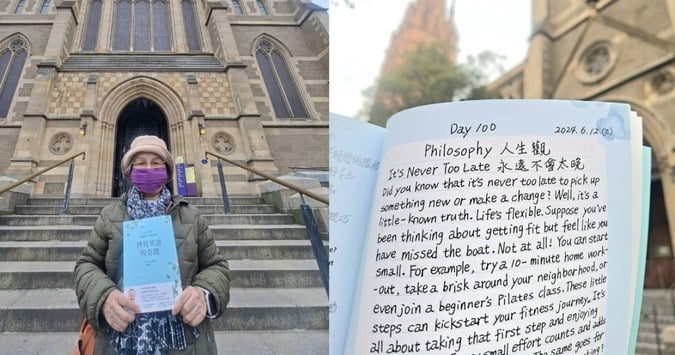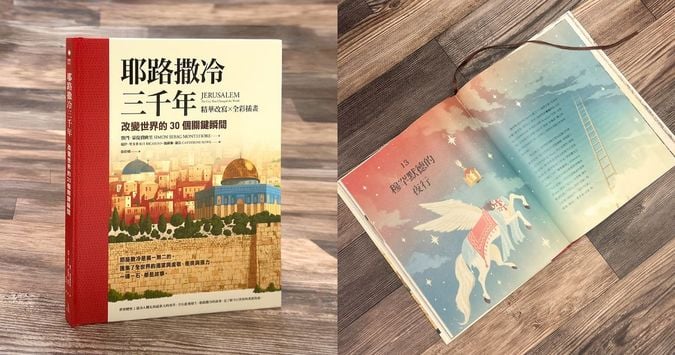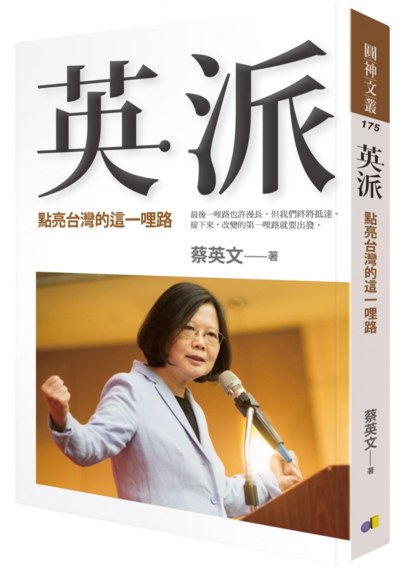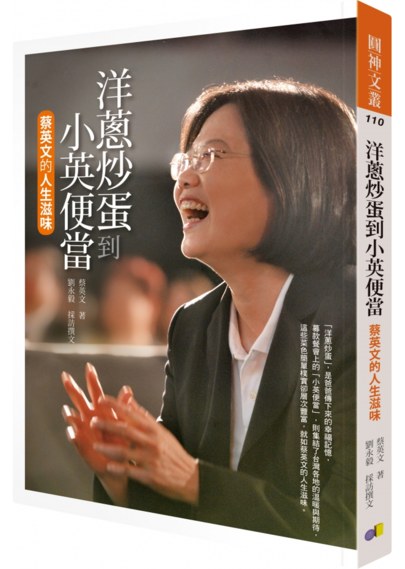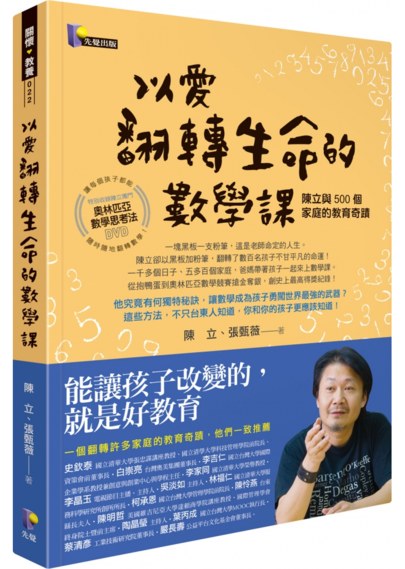原來我們做的遠遠不夠──《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哩路》
「我們等妳好久了,怎麼這麼晚才來啊?」一個小女孩認出我,在公共廁所旁拉著我問。
時間是2010年我參選新北市長的後期。當天已接近晚上十點,我才匆匆從上一個行程飛奔到平溪。由於時間已經非常緊迫,我一到了就要上台說話,不過,我還是擠出一點時間,先溜到廟埕旁的公廁上廁所。腦袋裡面正在想等一下要講什麼,哪知道一出洗手間,便被幾個孩子圍住。
她們的天真迅速感染了我。我就跟她們聊了起來:「妹妹,妳們怎麼這麼晚還在外面?」我一邊牽著她,一邊催促著其他孩子往會場走;有的孩子說是跟著阿公來的,也有孩子大聲回答說,是被阿嬤帶著「一起來看蔡英文」。
我把他們帶往會場,演講的時候,我特地盯著台下看,我看到很多牽著孫子孫女來晚會現場的阿公阿嬤,一眼望去幾乎看不到屬於青壯年紀的父母。

(圖:《英派》。幼齡的孩子總是真情流露,直接抱了上來。)
當阿公阿嬤變成孫子的爸媽 ……
我要講的事情其實大家不難猜到,就是隔代教養。在台灣許多地方,尤其往鄉下走,這已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當家長離開家鄉到外地工作,便把孩子留給老家的長輩照顧。某些地方政府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設立公共托育機構來減輕家長的照顧負擔,但在非都會區,政府能介入幫忙的資源和機會都不多,除非是弱勢貧窮家庭。
長久以來在學術圈和政務官的訓練,讓我習於做抽象而整體的政策思考。但是那晚,當我看到這些隔代教養的孩子時,腦中浮現了更實際的困惑:難道這些家庭,都不需要政府的幫忙嗎?要怎麼做,政府與社會才能具體又有效地幫這些家庭解決問題呢?
類似的問題一直停留在我腦海裡面。跟以前不同的是,在擔任黨主席時,我忙著參選或輔選,比較沒有時間好好來端詳這些問題,現在,我則有了較為充分的時間來找答案。
被黑道抱怨「找不到小弟」的陳爸
透過朋友的介紹,我得知在台東有個很特別的「書屋」,他們願意給我一個機會去看看那裡運作的情況。
迎著太平洋的風,我來到了知本。「建和書屋」在這裡己經有了十多年的歷史,負責的陳俊朗以課後伴讀的方式,照顧了許多孩子。
原來在台北工作的陳俊朗,十多年前毅然放下手邊的生意,全家返鄉。一開始他只需照顧兩個兒子,現在,他成了照顧上千名弱勢孩童的「陳爸」。
黝黑的陳爸有點得意的說:「當地的黑道都抱怨找不到『小弟』了!」
起初,他只是在自家院子教兒子和兒子的同學讀書,有時還要先煮飯餵飽他們,才能繼續寫作業。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他自己夜裡還得找資料,補進度。
「最難受的是,常常得先替那些孩子擦藥,才能教功課。因為這些弱勢孩子在學校不是被體罰、被霸凌,就是被酒醉的爸媽家暴,滿身傷痕,怎麼可能安心讀書?」說起十多年前的事,陳爸的心情依然激動。
書屋不只提供孩子寫功課與念書的環境,還安排運動、音樂等多元課程,以彌補學校與家庭教育不足。陳爸也要求孩子們要利用假日做社區服務,「有所得,相對也要懂得付出」,這是陳爸在教導孩子們時的堅持。
我問他:「政府不是對弱勢家庭有補助嗎?那些補助有沒有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陳爸聽了我的問題之後反問我:「幫助?當補助讓孩子成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家庭關係會好嗎?」
他的話一語點出政府的盲點。父母找不到工作,生活沒有目標,而孩子的問題來自家庭,家庭問題不解決,光是課輔並不足以讓孩子健全的成長。簡單地說,這不只是錢的問題而已。所以,從幾年前開始,陳爸也開始協助家長戒毒、戒酒、戒賭,開魚池、闢菜園,提供工作機會給他們。這樣做的結果便開啟了一個正面的循環,很多受過幫助的家長也跟著投入改造社區文化的行列。
他以民間力量直接進入社區處理病根,把家庭、學校和學生三方面連結起來。同時他把社區帶進來,用社區照顧和照養,來補強家庭功能弱化和學校功能不足的問題。
這種實踐力量實在令人印象深刻,不過,同一時間,長年在政治領域工作的我,卻不得不反省,政府的資源為什麼無法下在刀口,做有效運用呢?

(圖片來源:快樂學習協會:孩子的秘密基地)
我不能只是讚嘆,我要能加入他們
我們在思考政策時,主要會從社會整體面評估,看數字、看概況。但實際在人民的生活中,資源的分配如何被使用,卻不是能從數字裡顯現的。
建和書屋的例子讓我們看到,行政系統從家庭和學校兩條路徑提供資源,但這些資源卻無法解決孩子面臨的真實難題。
政府做不到的,民間就自己扛起來做。書屋的模式已進行十四年,這種從社區著手的路徑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讓我感受到民間擁有無窮的潛力,也有無盡的力量。
所以,話說回來,我能為像陳爸這些人做什麼?離開知本之後,我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我知道自己不能只是讚嘆這股民間的力量,我應該加入他們,為他們做一點事情。因為在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許多像陳爸這樣的人,對社區有想法和熱情。我告訴基金會的幕僚,我們要做為一個平台,匯集資源,來幫忙進行這樣的照養體系。這也是「小英基金會」存在的目的之一,我們可以善用自己做為民間團體的優勢,我們可以在政府之外,匯聚社會資源來幫助弱勢的孩子,讓他們在成長的這條路上,有著較為公平的機會。
.jpg)
(圖:《英派》,小英教育基金會的成立。
希望「小英的故事」原文Nobody's girl,變成 Everybody's child。)
教育,為何讓部落的孩子失了自信?
為了找尋這樣的可能性,我又走訪了台東巴喜告部落的桃源國小,那裡有位鄭漢文校長。
鄭校長雖然是漢人,但他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傳承教育工作,有著深深的使命感。他告訴我:「在原住民部落的教育不應把孩子教成漢人,而應教導孩子們認識自己的部落文化,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
他還說,曾有部落耆老對他很不滿:「我們都把孩子給你們教了六年,你們還想怎樣嘛!」
那句話敲醒了他,原來,正統的學校教育制度對原住民而言,是另一種文化。為了讓孩子學習漢人的教育制度,原住民文化反而失去了傳承的機會。
部落裡的孩子,不僅面對資源落差帶來的教育弱勢,也因為文化差異,而產生文化弱勢。
鄭校長提醒我觀察低年級的孩童與高年級孩童的差別。低年級的孩童往往有著慧黠的眼神,身子與腦袋機敏又靈巧。他們會向我們飛奔而來,跟鄭校長撒嬌,也跟我問好,聒噪的你一言我一語,急著表達自己,熱情直接的肢體語言很有感染力。
可是,高年級的孩子就略微不同。他們在正規體制裡被教育了幾年,逐漸失去了眼裡的光采,肢體表達上變得退縮,笑容轉為靦腆,也沉默多了。我知道,是我們的教育讓他們被馴化,失去了自信。
家穩定了,孩子就安心了
除了教育,讓他們失去自信的,還有整個大環境。
在部落,父母沒有合適的就業環境。換句話說,這裡的情況和前述知本的故事一樣,如果要解決偏鄉裡的教育問題,不能只從教育面著手。
鄭校長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在部落中設立了木工坊、布工坊等,讓父母有了留在部落工作的機會。他說:「家長做工養家,勤奮的精神會被孩子看到,被社區肯定,自我價值就浮上來。如果只是靠補助過日子,孩子會覺得父母沒用,內心深層的悲苦,無力發洩。親子雙方的心情都很不好受。」
當我造訪太麻里的「向陽薪傳木工坊」的時候,我看到那裡有各種木製生活用品及小擺設整齊的陳列,它們沒有塗漆上油,指尖便可感觸到細微的深淺木紋,自然的原色透著時光與漂流木之間的對話,這些都是獨一無二的作品,說它們是藝術品也不為過。
一旦父母有了工作,家中經濟情況便獲得改善。家穩定了,孩子的心定了,教育問題就能解決了。
我們在談政策或做學問時,講究的是一體性、系統化。但人的生活卻無法系統化,因為人是多樣的,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以一體化來管理這個社會,就會喪失多元性。
我們坐在辦公室裡思考決策時,往往為了效率,會向系統與標準化傾斜,只有來到現場親身體會,才能理解以往政策的局限。
幾位返鄉的原住民青年,在鄭校長的鼓勵之下,自己動手彙編布農族辭典;部落耆老也被邀請,在學校裡教授傳統文化課程,讓界線被穿越,讓孩子們在每天生活的教育現場,就能學習自己族裡的文化。

(圖片來源:快樂學習協會:孩子的秘密基地)
快樂學習協會:決心做偏鄉孩子的「路燈」
同樣的,在嘉義東石,吳念真導演和圓神出版社簡志忠社長,正和一群朋友成立「快樂學習協會」,為偏鄉學童提供課後輔導。
起因是來自於紙風車基金會某次下鄉為孩子搭台演戲後,吳導收到一位老師的長信。信裡寫著,孩子從來沒看過這樣的演出,興奮極了,但這場演出就像是漂亮的煙火,放完後,一切還是回到原來的樣子。偏鄉的孩子們下課後無處可去,四處遊蕩,僅有課業跟不上還算好,不好的結局則是岔入歧途,一輩子被耽誤。因此,吳導和幾位朋友聯合起來,決心要做偏鄉孩子的「路燈」。
台灣社會真的有許多人,願意出力,共同解決下一代的困境。在吳導和簡社長的計畫帶領之下,小英基金會也找到了施力點。
這裡被命名為「孩子的秘密基地」。在課輔教室裡,我看到一個戴眼鏡的小男孩表情好認真,聽著年輕的課輔老師耐心解說九九乘法表。
我無法預測眼前的這個小男孩,幾年之後的人生發展;但我能肯定的是,有了這個「秘密基地」,他的未來就出現了正向發展的機會。
點亮台灣
沿著走廊,一間間教室走過,看著教室裡天真童稚的臉龐,看著那些付出青春熱情的青年。我心裡有一種很飽滿的感覺,像是得到一份意外的禮物。
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是,在台灣,在這個充滿向上力量的社會裡,想做事的人一點都不孤單。找到方法,找到人,找到力量,我們就會為那些原本沒有出口的人找到出口。
陳爸、鄭校長、吳導、簡社長,以及無數的人們,他們都願意當路燈,也都在當路燈。電影《一代宗師》有這麼一句:「有燈就有人。」這些路燈越多,這塊土地就會減少令人感到無力的陰暗角落。
本文出自蔡英文著作《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哩路》
部分照片出自快樂學習協會:孩子的秘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