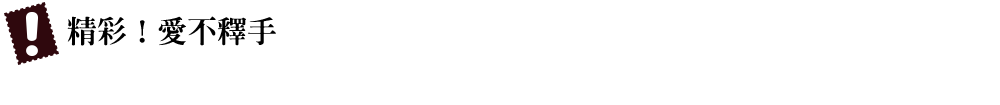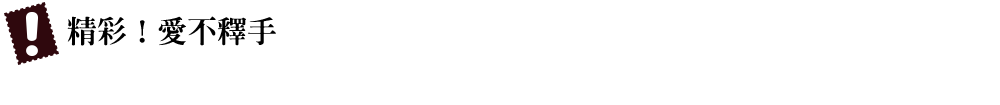忽然一陣敲門聲
坐在我客廳沙發上的大鬍子下令:「講故事給我聽。」說真的,這情況讓人很不高興。我是「寫」故事的人,不是講故事的。而且就算要寫也是自己想寫,不是聽命於人。上一次要我講故事的是我兒子,那是一年前的事,我講了個妖精與貂的故事,內容現在都忘了,而且他聽不到兩分鐘就睡著。不過今天的情況和上一回有基本上的不同,因為我兒子沒有鬍子,也沒有手槍;因為我兒子好聲好氣求我講故事給他聽,而這個男人根本就用搶的。
我努力想跟這個大鬍子解釋清楚,放下手槍比較好,對他對我都好。有把上了膛的槍指著腦袋,要想出故事很難。可是他很堅持,還說:「在這個國家,你想要什麼東西,都得訴諸暴力。」他剛從瑞典來,在瑞典完全不是這樣。在那裡,你想要什麼東西,只要客客氣氣地說,多半都能得到,但在令人窒息的中東可行不通。他才到這裡一個星期,就明白事情如何運作……或者該說,事情是怎麼個無法運作了。巴勒斯坦人想要國家,好好說,得到了嗎?才怪。後來他們開始炸小孩和公車,大家才開始聽他們講話。在這個國家,誰有能力就有權利,各方面都如此,無論政治、經濟或停車位都一樣。蠻力是我們唯一能理解的語言。
喂,我想講理。「喂你個頭,」大鬍子咕噥一聲,扳起扳機,「你不講故事,兩眼中間就會進一顆子彈。」我看出眼前選擇有限,這傢伙是認真的。「一間屋子裡坐著兩個人。」我開始說了。「忽然一陣敲門聲。」大鬍子忽然僵住,我一時之間還以為他聽得入神,但其實並不是。他在聽別的。有人敲門。他說:「開門,但是別想搞鬼,不管是誰,都趕快應付掉,動作要快,否則下場會很難看。」門外的年輕人是做問卷調查的,有幾個問題要問,都很短,有關於這裡夏季的潮濕,以及夏季潮濕對我情緒的影響。我說沒興趣回答問卷,但他硬是闖了進來。
他手裡抓著資料夾,一屁股就坐在沙發上。瑞典人也在他旁邊坐下。只剩我還站著,還想假裝。我說:「請你離開,你時間挑得太爛了。」「太爛?呃?」他打開塑膠資料夾,拿出一把大左輪槍。「為什麼我時間挑得太爛?因為我比較黑?因為我不夠好?面對瑞典人,你有全世界的時間;面對摩洛哥人,面對一個脾臟碎在黎巴嫩的老兵,你就連該死的一分鐘都騰不出來。」我努力想跟他講理,但做問卷的將左輪槍舉到唇邊要我閉嘴。「少來,」他說,「別找藉口,坐到那邊去,快給我吐出來。」我問:「吐什麼?」老實說,我挺緊張的,瑞典人也有槍,事情搞不好會失控。「別惹我,」做問卷的提出警告,「我的槍很容易走火。把故事吐出來,快點。」瑞典人也說:「是啊。」並且把他的槍也掏出來。我清清喉嚨,從頭開始:「三個人坐在一間屋子裡。」瑞典人說:「不許再說什麼『忽然一陣敲門聲』。」做問卷的不懂他何出此言,卻立刻附和:「繼續說。不要有敲門聲,講點別的,給點驚喜。」
我停頓片刻,深吸一口氣。忽然一陣敲門聲,他們用威脅的眼神看我,我聳聳肩膀。這不是我的錯,我這回講的故事裡沒人敲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