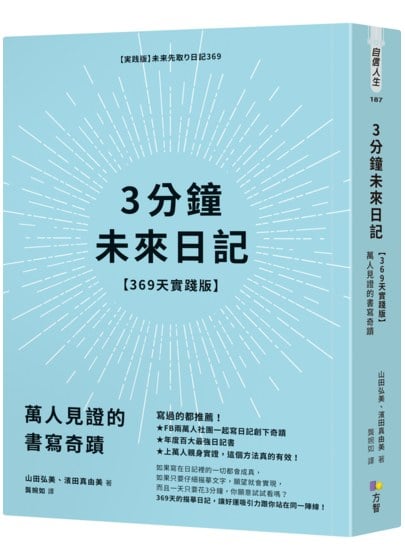第一章 科學家與修理匠
腦是軟的。我有些同事把腦比作牙膏,但並不是很正確。
腦沒辦法像牙膏一樣塗開,也不會像牙膏那樣沾到你的手指上。
想像一下豆腐,那種軟度也許是精確一點的比喻。如果你把腦切成方塊,儘管形狀不會像豆腐那麼完整,但或多或少仍能保持原狀。不過,受傷或腫起來的腦會更軟。這時候如果用高速手術鑽頭在腦殼打個洞,稍微壓一下,腦就會從頭顱裡被擠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大概就比較像牙膏了。
有關腦的質地問題,始終在我心中盤桓。
為什麼?
因為我是神經外科醫師,腦是我的事業。
雖然我很清楚,人腦是一套細微、複雜且神祕的系統,我卻經常必須將它看成是一種居住在堅硬頭顱內多骨區域中的柔軟物體。我接觸過許多被腫瘤、血塊、感染所侵害,或因中風而完全腫脹的腦。還有些被子彈、釘子甚至蛆跑進去的腦。我看過所有最脆弱的腦。然而,不像其他神經科醫師、精神科醫師等腦科專家,只在頭蓋骨之外檢測腦,神經外科醫師與這個人體最複雜的器官,多了一層雙手直接接觸的關係。我們既是科學家,也是修理匠。
我的科學家部分,會為腦部不可思議的心智、意識、記憶和語言等表現形式而沉迷;而我的修理匠部分,則在為紓解病患腦中過多的壓力而插管時,管口能順利噴出透明液體而感到滿足。在日常手術工作中,科學家的那個部分多半退居在修理匠的手工技術之後。這其實不是問題。因為如果在你腦中有個正在擴大的血塊,你想要的,會是一位技術純熟、而且最好動作敏捷的人腦修理匠。你不會在乎為你動手術的醫師有沒有在《科學》或《自然》那些學術期刊發表過論文。
讓我用一個最簡單明瞭而且確實「純手工」的實例來說明。
多年前我還在實習的時候,有一次被緊急傳喚到急診室,電話那頭簡要報告著:「有一根釘子卡在這位木工的額頭左側裡面……神經方面未受損傷。」在那一刻,我心裡掠過什麼念頭?回想前額葉系統的研究,思索語言、記憶的複雜神經網絡?不!我想的,是外科手術的具體考量:釘子是尖的,腦部則充滿血管,這釘子很可能直接插到血管。當然,這些思考都在瞬間發生。我在此詳加描述只是加強說明的效果。
我在急診室看到的,是一個坐在輪床上的年輕人,大概三十多歲,完全清醒、動作靈活,雙臂交叉著休息,仍穿著施工用的工作鞋。當我出現時,他緊張地微笑著。
他就是那位病患嗎?看起來實在不像。
他正是受傷的患者。他解釋說,當時他和木工朋友一起在房屋邊的樓梯上工作,朋友站在數階之上,兩人用自動釘槍將重型釘子打進牆板。朋友在發射釘子時手滑了一下,那釘子就打進了站在下方的人││也就是我的病患││的左前側頭部。事發當時,木工仍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雖然在朋友手打滑的那一刻,他感覺到一陣刺痛,也聽到來自同一方向的咒罵聲;但當他的手指發狂似地搜尋頭頂時,卻沒有摸到任何血滴,也感覺不出異狀。他不確定釘子是否在頭裡,但他的朋友卻十分確定。
當我撥開他的小平頭,仔細檢查頭皮時,我看到釘子銀色扁平的頂端,並未完全與頭皮齊平,而是有點深陷。除了釘子以外,他看起來很好。在五分鐘快速的神經外科檢查後,我找不出任何問題。我將他送到長廊盡頭做電腦斷層掃瞄,發現這根釘子與他的頭蓋骨呈完美的垂直狀,並鑽入左額葉達兩吋之深。幸運的是,並未插進任何大血管。與較常見的槍擊傷害不同,他的腦並沒有出血跡象,這是個相當清爽俐落的穿刺傷害。
在那一刻,我最大的擔憂││因釘子穿入引發的腦出血││已得到紓解。現在,我應該緩口氣,來仔細思考複雜的科學問題?或是運轉我身為腦外科醫師所具有的驚人智力?當人們說「不須動用腦科醫師」這句話時,他們假定我們是最聰明的人。但到目前為止,我有展現出任何高超的智能嗎?我的思緒再度回到實際而具體的問題││我們必須從這位男子的頭裡取出釘子。釘子進入時,並沒造成出血;釘子取出時,也同樣必須避免出血。
我走進等候室,除了他的妻子之外,那位面色蒼白、心情沮喪的朋友也在那兒,低著頭凝視地板。我試圖稍微振奮他們的心情。是的,釘子的確進入他的腦中,但依目前的判斷,他的腦功能完全正常,而且釘子並未造成出血。這位朋友沒有抬起頭,只是打開手掌,將一根被他握得暖烘烘的大型銀色釘子交給我,與嵌在傷患頭裡的釘子相同。他說:「我不知道……這釘子或許對你們有幫助……你們可以知道要應付的是什麼東西。」從X光片中,我並沒看出這根釘子的柄軸上有兩個以銳角狀突出的黃銅色倒鉤。雖然我不是木工,但我可以猜到這個倒鉤的作用在於確保強而有力的支撐。我向他致謝,並把釘子放入白袍口袋裡。走回急診室途中,我用手指撫過尖尖的倒鉤,再度思考出血的問題。以外科手術來說,基本、普遍並具關鍵性的主題,就是避免及控制出血,而非火箭那一類的深奧科學。
召集了包括神經外科醫師主管和麻醉科醫師在內的相關團隊之後,我將傷患帶到手術室,繞著釘子頂端剃掉一小塊頭髮,再沿著頭蓋骨,在頭皮上切出一條短短的直線。醫學課本並沒有告訴我們如何從頭顱內取出釘子,所以我們只能憑著常識,來段即興演出。我們以釘子頂端為圓心,鑽起一小片前額骨,連同以倒鉤牢牢嵌在上方的釘子,慢慢地從頭蓋骨將這一小片前額骨挖起。雖然看得到頭蓋骨上有個小缺口,腦的表面也有一個被刺穿的傷口,但是並沒有出血。我們覺得自己很幸運(「好運勝過本事」││這句話是外科醫師愛用的口號)。
接著,我們用與這位傷患的行業比較相襯的大型工具,將倒鉤夾起,並把前額骨上的釘子從內側敲出來。用抗生素溶液浸泡過挖出的骨頭後,再用迷你鈦板和螺絲釘,把它靈巧地固定回原位,然後縫合頭皮。事實上,我們縫合最外層頭皮所用的道具是釘槍發射的手術釘針,而不是縫合線。當時,我並未意識到這個動作的微妙和諷刺。不出二十四小時,病人就踏上了歸途,還沿著長廊與將釘子打進他頭裡的朋友一路說笑。
有一天晚餐過後,我向家人和朋友敘述這個故事,他們全都嘮叨不休地問我同一個問題:「他怎麼可能正常?有東西插進他的腦袋哩!」終於來到了這一刻,讓我的科學家部分得以神氣活現地發表高論,與為此問題著迷的觀眾來場步調快速的座談會,解答他們的疑惑。畢竟,我並不只是個技師,而人腦也並不只是塊豆腐。
他怎麼可能正常?首先,根據例行的臨床檢查,我們認為他的腦功能正常,這樣的斷言無疑是有點粗糙。然而,他說話流暢並能適切地回答簡單問題。我要求他在五分鐘內記住三樣東西,他做到了。當我在他的眼前閃燈,他的瞳孔有反應,眼睛也對稱地移動。他的臉部肌肉沒有下垂。他的臂力和腿力正常,知覺也正常。他的反應能力沒問題。他的手可以做出快速、具有統合性的動作。換句話說,他的五分鐘神經外科檢查結果,完全令人滿意。
然而,前額葉具有相當精密的功能,遠遠勝過我曾測試過的其他構造相對簡單的額葉。前額葉是頭腦內的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新進化形成的。若把猿猴的前額與人類的前額相比,則一個傾斜、一個凸起。我們可以為許多被我們所認定的性格、智能而感謝或怪罪我們的前額葉。前額葉的損傷是十分微妙的,包括洞察力、心情和較高層級判斷力(套句行話,就是「執行功能」)的改變。我無法在病人被飛快送往電腦斷層掃瞄前的急診室五分鐘檢查內,偵知那些變化。我只是神經外科醫師。我們必須請教神經心理學家,為我們評估這些更為複雜的腦部功能。
「那麼,妳為什麼不把這個可憐的傢伙送去做更精密的測試?」我的晚餐聽眾以一種困惑和略帶非難的語氣問我;為什麼我只是宣布他「沒事」,便請他走人?我解釋說,外來的物品是釘子而不是電鑽,腦被侵犯的部位十分微小。特別是這寬大的前額葉可以是相當寬容的,尤其是在僅牽涉到其中一側的時候。舉例來說,在病人自己察覺到任何異狀之前,發現前額葉有個長成柑橘大小的腫瘤,並不是稀奇的事。事實上,病人通常根本就沒察覺任何異狀,而常常是由堅持要他來就醫的配偶或朋友向醫師解釋:「他就是不對勁,但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腦的種種作用具有某種程度的重複與彈性,當某部位受到損害,有時候可經由其他部位得到補償(一種稱為「適應性」的卓越能力)。即使腦沒有直接產生補償,病人通常可以在毫無知覺之下間接地妥善處理。舉例來說,當一個人產生輕微的記憶困難,他可能會開始寫下更多事情,藉以為自己的存在保有無縫的連貫性。然而,適應性的力量畢竟有限。單側前額葉的損傷通常可被妥善地包容(另一側的前額葉可提供某種程度的補償),但是當兩側同遭損傷時,卻經常會帶來無可挽回的毀滅。
回到前面所提的木工,我們確信一個出現在單側前額葉的細小傷痕,對腦造成的傷害是微乎其微的。就算透過神經心理學仔細、耗時的測試,鑑定出微弱的認知退化,病人真的會在乎嗎?他或其他人會注意到這個問題嗎?他身兼木工、丈夫或朋友的生活會受影響嗎?令人懷疑。以更冷酷、現實的理由來說,病人或醫院會願意為這些測試付費嗎?他的保險公司當然會評估成本,並質疑測試的必要性。此外,在我對他前額葉的恢復力具有十足把握的前提下,我最關心的問題不是功能不良的思考,而是功能不良的木工作品。假如他完全放棄自動釘槍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
帶著這個最終念頭,我的技師部分又重掌大權,而科學家部分則再次敬陪末座。
前下決定,然後,繼續下一步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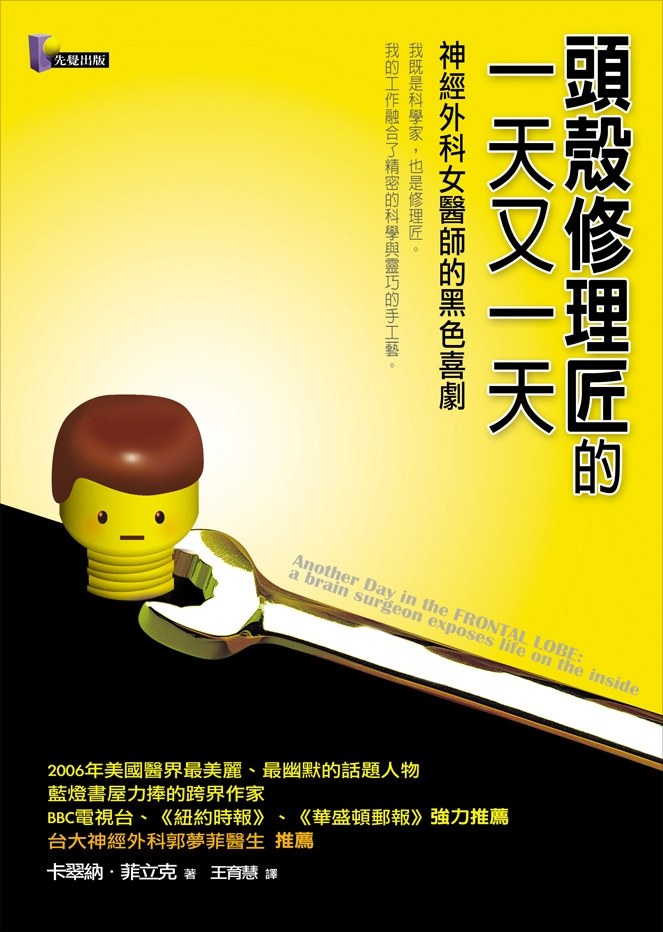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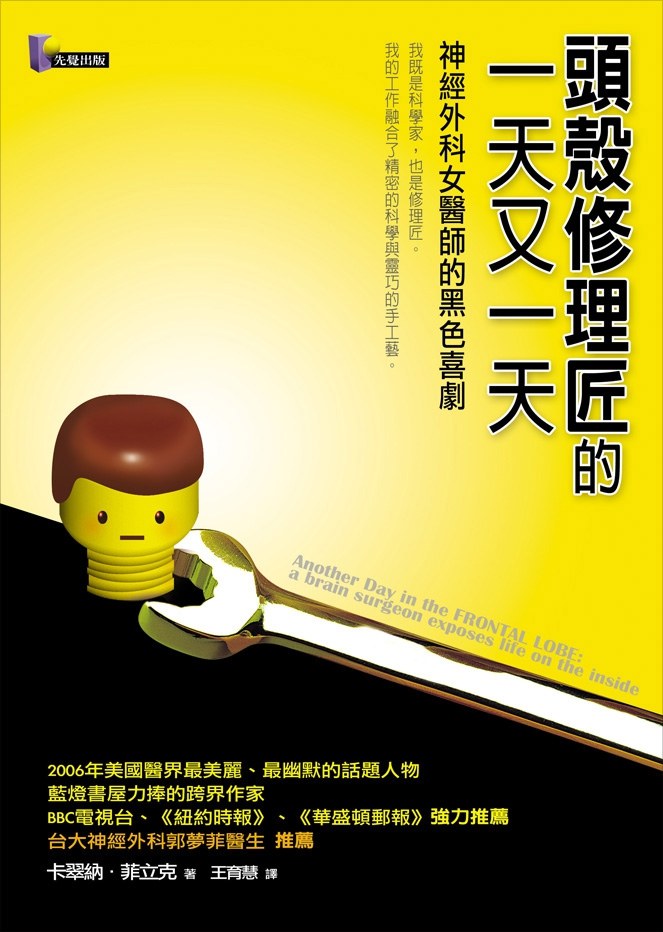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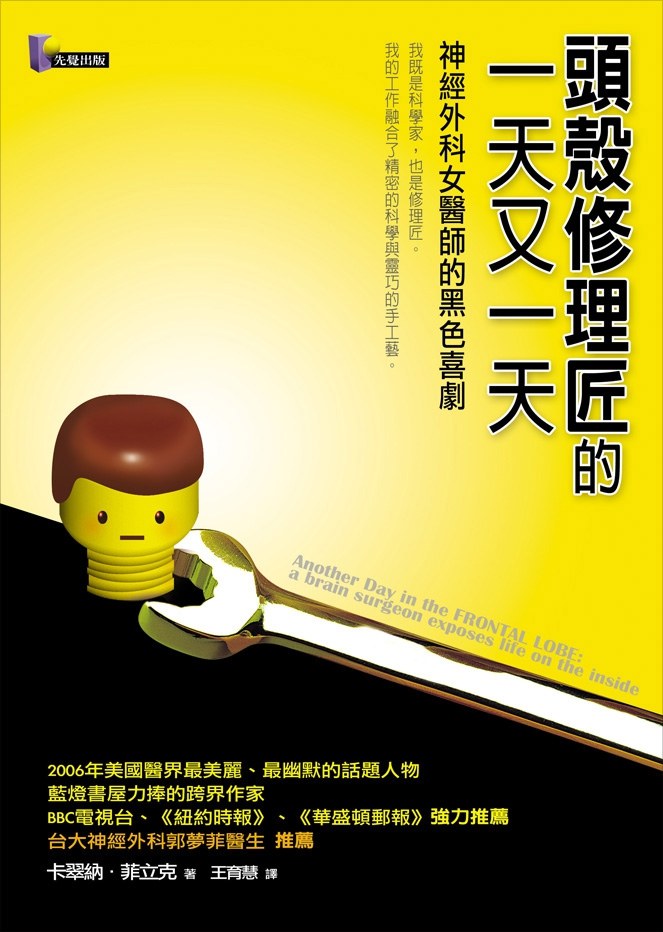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