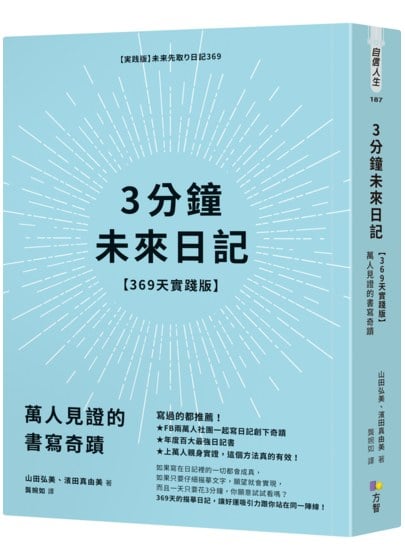close


書活網特推
已經購入X老師的星座運勢書了嗎?其實,我們都能看見自己的命運,親手掌握未來……故事性超豐富的硬底子小說。
內容簡介
★請進入「蕾絲占卜師官網」,要你目眩神迷 。
貝莉能寫,天啊!她真能寫!書中到處都是精彩的故事,讓你一刻都無法放下。
關穎對女主角深有同感,而且「了解來龍去脈後,既震驚又佩服作者的邏輯,我承認我被結局嚇到了! 」
*全美書店店長、讀書俱樂部毫不猶豫熱血推薦。
*上市一週即登上紐約時報、亞馬遜網路書店、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BookSense、出版者週刊……等全美各地暢銷書排行榜。
*獲選二○○八年八月美國獨立書商選書與年度最佳送禮書單。
*獲選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二○○八年八月最佳選書。
*獲邦諾書店「矚目新書」
錯並不在蕾絲,是占卜的人解錯了。
那天晚上,我們對蕾絲做出了同樣的解讀,雖然我們的選擇可能會不同,但無論如何,我的姊姊都無法復生了。
惠特尼家族的女性都有預知未來的天賦,能從蕾絲的圖案中看見自己與他人的命運。陶娜的雙胞胎姊姊因看見蕾絲中的某個影像而自殺,大受打擊的她從此遠離家鄉,精神恍惚地過著進出學校、醫院、心理醫師診所的生活。
此刻,因最疼愛她的奶奶失蹤,將她帶回以女巫歷史聞名的家鄉薩冷鎮。但返家後遭遇的一連串離奇事件,卻迫使她必須面對最不願面對的過去……
貝莉能寫,天啊!她真能寫!書中到處都是精彩的故事,讓你一刻都無法放下。
關穎對女主角深有同感,而且「了解來龍去脈後,既震驚又佩服作者的邏輯,我承認我被結局嚇到了! 」
*全美書店店長、讀書俱樂部毫不猶豫熱血推薦。
*上市一週即登上紐約時報、亞馬遜網路書店、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BookSense、出版者週刊……等全美各地暢銷書排行榜。
*獲選二○○八年八月美國獨立書商選書與年度最佳送禮書單。
*獲選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二○○八年八月最佳選書。
*獲邦諾書店「矚目新書」
錯並不在蕾絲,是占卜的人解錯了。
那天晚上,我們對蕾絲做出了同樣的解讀,雖然我們的選擇可能會不同,但無論如何,我的姊姊都無法復生了。
惠特尼家族的女性都有預知未來的天賦,能從蕾絲的圖案中看見自己與他人的命運。陶娜的雙胞胎姊姊因看見蕾絲中的某個影像而自殺,大受打擊的她從此遠離家鄉,精神恍惚地過著進出學校、醫院、心理醫師診所的生活。
此刻,因最疼愛她的奶奶失蹤,將她帶回以女巫歷史聞名的家鄉薩冷鎮。但返家後遭遇的一連串離奇事件,卻迫使她必須面對最不願面對的過去……
一個瀰漫著神秘感與小鎮趣味的故事,包藏著令人心痛卻充滿愛與力量的真理。真實與虛構世界的界線在書中如此模糊而迷人,你將心甘情願被它施展的咒語蠱惑……
【作者簡介】
布諾妮雅.貝莉(Brunonia Barry)
生長於美國麻塞諸塞州,曾於佛蒙特綠山學院與新罕普夏大學修習文學與創作課程,也曾於紐約大學修習劇本寫作,是波特蘭舞台設計公司的創辦人之一。
貝莉熱愛戲劇,第一份工作就是為芝加哥數家劇院擔任活動宣傳人員。之後在曼哈頓短暫工作後移居加州。為一些電影工作室承接各種專案,並持續向好萊塢知名劇作家羅伯特?麥基(Robert McFee)學習劇本寫作,後來成為麥基「劇本開發」小組的成員。
貝莉在美國各地從事劇本創作工作多年之後,與丈夫回到麻塞諸塞州,成立一家開發文字、影像與邏輯思考拼圖的創意公司。她和丈夫與愛犬目前就居住於麻塞諸塞州薩冷市,《蕾絲占卜師》是她的第一部小說。
【譯者簡介】
柯清心
台中人。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學士,美國堪薩斯大學戲劇系碩士。
現任專職主婦,兼職翻譯。譯有:《心靈私房書》《戰慄遊戲》《我就是要幸福,不行嗎?》《8的秘密》,以及《少年間諜艾列克》系列等書。著有兒童故事《小蠟燭找光》。
規格
商品編號:G0200001
ISBN:9789868461413
頁數:384,中翻,25開,平裝,ISBN:9789868461413
ISBN:9789868461413
頁數:384,中翻,25開,平裝,ISBN:9789868461413
各界推薦
★暢銷作家貴婦奈奈:
我一直很喜歡與占卜、女巫有關主題的研究或小說,《蕾絲占卜師》一次滿足我這兩種需求,而占卜的工具竟是我最愛的蕾絲,這讓我以後看到蕾絲都會出現不一樣的心情。
作者用三代母女的故事,編織著像蕾絲一樣,看似美麗卻複雜難解的情節。故事的結尾先是讓人一驚,接著讚嘆作者的邏輯與鋪陳功力,整篇故事真是太精采了!
★人氣閱讀部落格主「WC看看」:
揭開這片迷漫的蕾絲,我其實看到滿滿的愛。一個家族成員逝世所造成的重創,竟是由另一個家族成員的離去來完整,開端與終結,合而為一,而它帶領讀者沉浸回深刻的愛,也仍縈繞著神秘力量的韻味。加上結局的超級過彎甩尾,很容易理解全美各讀書會為何重讀起來興味盎然不減。
人生裡的每一個片刻,我們都在編織自己的蕾絲;同時也在任何一個靜止點,解讀心中的那片蕾絲。如果你曾經凝視過自己心靈的圖案,感覺那繁複但誠實、總會帶領你回到軸心的構圖,當然也能為這本書所觸動。——
★書評人譚光磊(灰鷹):
2008年8月底,《蕾絲占卜師》在萬千矚目之下,以嶄新面貌隆重登場,不僅入選獨立書商協會的選書、榮獲Borders 書店的「原聲」(Original Voices)新人大獎提名,更橫掃全美十大排行榜,成為暑假結束前最轟動的新人作品。
現在,這部迷魅動人的精采作品,就要以中文的形式和本地讀者見面,而《蕾絲占卜師》這個神秘難解的謎,就要由你來解,故事中女巫家族的創傷和記憶,也要由你來一一揭露。不過請記得:千萬不要跳看結局。
我一直很喜歡與占卜、女巫有關主題的研究或小說,《蕾絲占卜師》一次滿足我這兩種需求,而占卜的工具竟是我最愛的蕾絲,這讓我以後看到蕾絲都會出現不一樣的心情。
作者用三代母女的故事,編織著像蕾絲一樣,看似美麗卻複雜難解的情節。故事的結尾先是讓人一驚,接著讚嘆作者的邏輯與鋪陳功力,整篇故事真是太精采了!
★人氣閱讀部落格主「WC看看」:
揭開這片迷漫的蕾絲,我其實看到滿滿的愛。一個家族成員逝世所造成的重創,竟是由另一個家族成員的離去來完整,開端與終結,合而為一,而它帶領讀者沉浸回深刻的愛,也仍縈繞著神秘力量的韻味。加上結局的超級過彎甩尾,很容易理解全美各讀書會為何重讀起來興味盎然不減。
人生裡的每一個片刻,我們都在編織自己的蕾絲;同時也在任何一個靜止點,解讀心中的那片蕾絲。如果你曾經凝視過自己心靈的圖案,感覺那繁複但誠實、總會帶領你回到軸心的構圖,當然也能為這本書所觸動。——
★書評人譚光磊(灰鷹):
2008年8月底,《蕾絲占卜師》在萬千矚目之下,以嶄新面貌隆重登場,不僅入選獨立書商協會的選書、榮獲Borders 書店的「原聲」(Original Voices)新人大獎提名,更橫掃全美十大排行榜,成為暑假結束前最轟動的新人作品。
現在,這部迷魅動人的精采作品,就要以中文的形式和本地讀者見面,而《蕾絲占卜師》這個神秘難解的謎,就要由你來解,故事中女巫家族的創傷和記憶,也要由你來一一揭露。不過請記得:千萬不要跳看結局。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