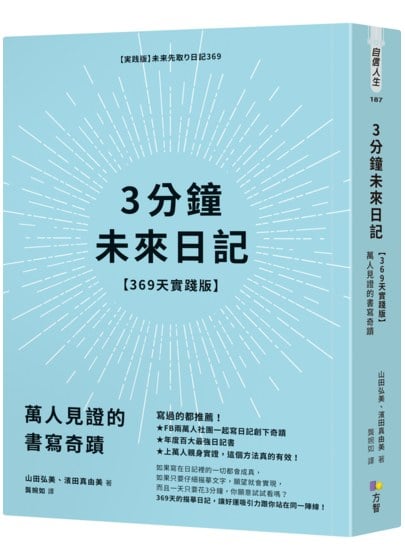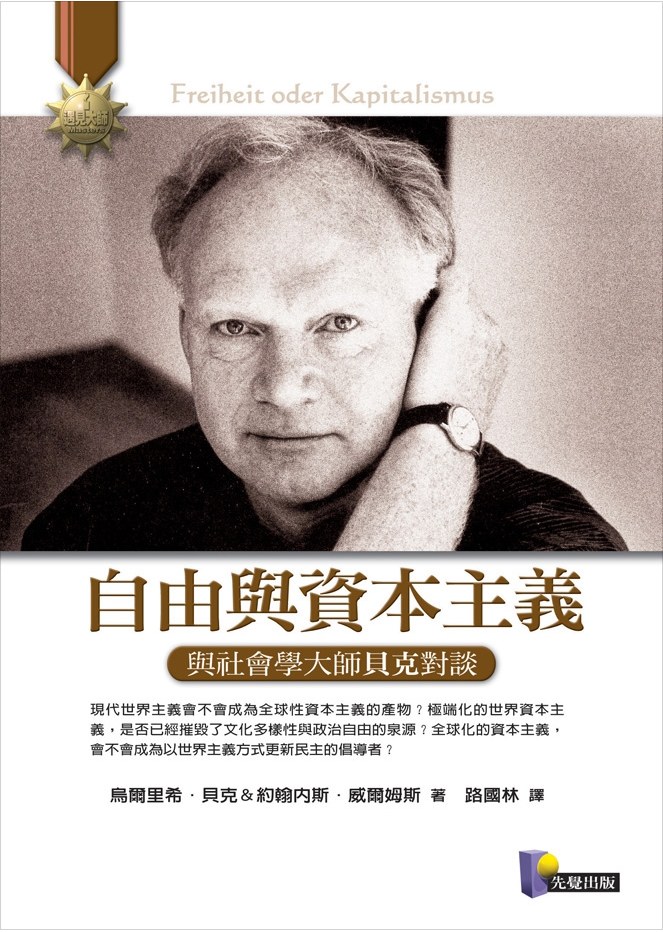
cl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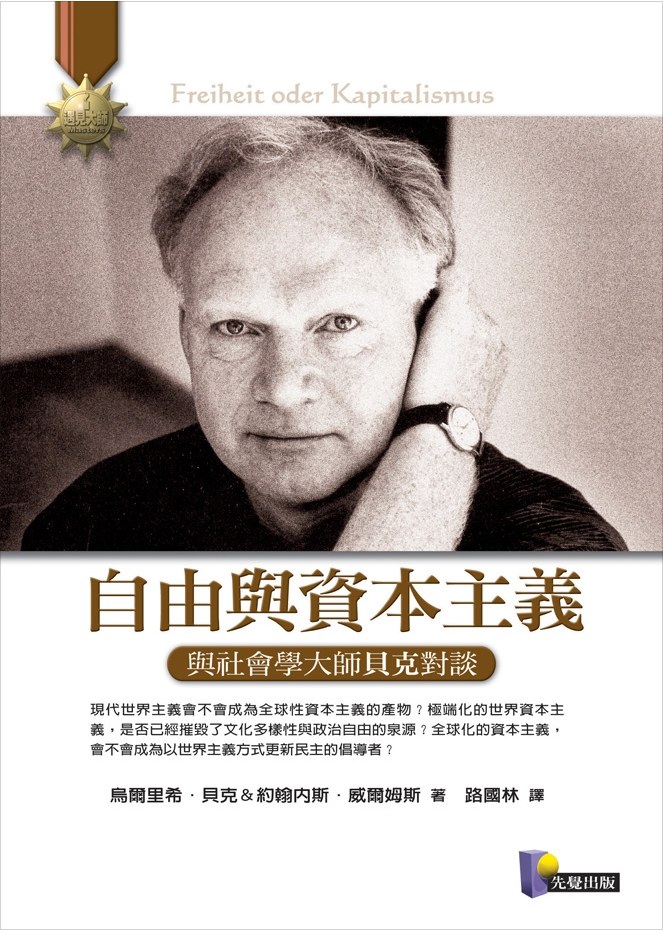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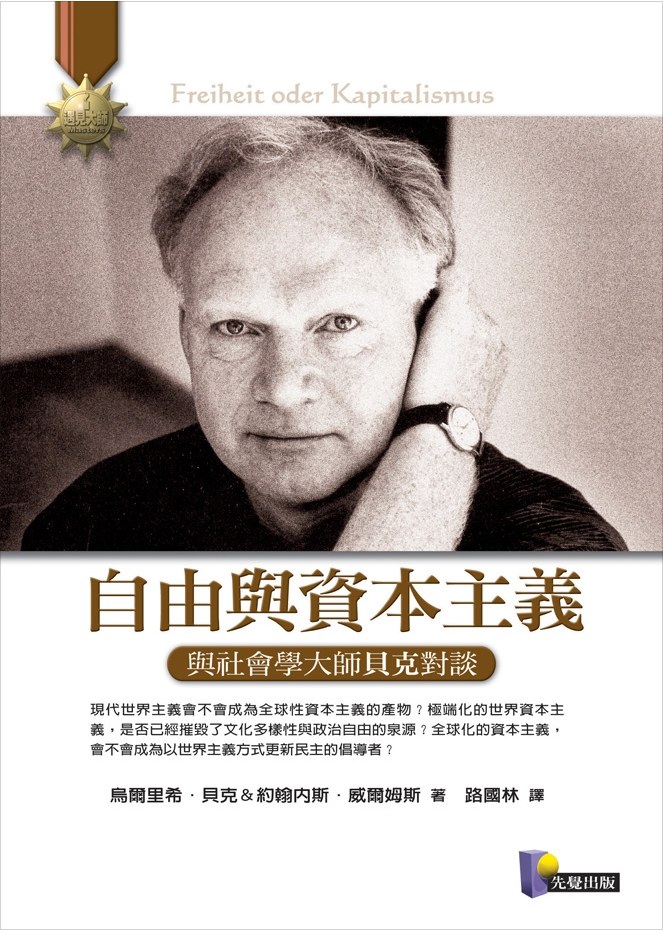
商品編號:P0150003
自由與資本主義─與社會學大師貝克對談
定價
$250
優惠價
79折 $198元
特惠訊息
內容簡介
在世紀之交,「全球化」的相關論述如巨浪狂潮,從世界席捲台灣。在百家爭鳴中,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所提出的「風險社會」、「全球化危機」、「第二現代」等概念,尤其獲得國際與台灣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社會學大師烏爾里希‧貝克以宏觀的視野和長期的研究,觀察到現代化的異化現象,以「風險社會」的概念點出「高科技」與「高風險」之間的關連,提醒世人應該以「整個全球」的視野,在開放而彈性的思維模式下,對社會風險的來源與後果進行風險管理。貝克更提出「第二現代」理論,主張現代化的發展必須轉變為以「反省」為主要內涵,在國際社會學界奠定大師級地位。
本書是德國資深記者與貝克的對話錄,在簡明而精要的對談中,為貝克的各項重要概念作一次總整理,是接觸當代社會學大師、進入貝克思想世界最佳途徑。
作者介紹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教授,長期從事社會發展和全球化問題的研究,並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和概念。貝克透過宏觀、敏銳的觀察,提出「全球主義」、「解民族國家化」、「世界社會」等趨勢,主張人類應以「整個全球」的視野,來處理諸如生態、核武、貧富差距等全球性課題。
貝克也指出近二個世紀的現代化所衍生諸如SARS、AIDS、禽流感、狂牛症、金融風暴等種種「副作用」,已經對人類造成不良影響。他與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法國社會學家拉許共同提出「第二現代」理論,主張必須進行以「反省」為主要內涵的「第二次現代化」,在國際社會科學界獲得注目。此外,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也點出「高科技」與「高風險」之間的關連性,主張世人應該在一個開放的、允許充分彈性的新思維模式下,全方位地認識風險的各種可能來源與可能後果,並加以管理。
主要著作有《什麼是全球化》、《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巨流)、《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商務)、《自由之子》、《全球化的政治》、《反思性現代化》、《世界社會的前景》等重要社會學與全球化論述。
約翰內斯.威爾姆斯/Johannes Willms
德國著名歷史題材記者和編輯,現任《南德意志報》執行編輯,著有《德國病》等在德國極具影響力之著作。
譯者簡介/路國林
中央編譯局馬列部譯審,譯有《全球化與道德重建》、《全球化與政治》、《不要恐懼全球化》、《尼采傳》等大量德國哲學、社會學和文化書籍。
社會學大師烏爾里希‧貝克以宏觀的視野和長期的研究,觀察到現代化的異化現象,以「風險社會」的概念點出「高科技」與「高風險」之間的關連,提醒世人應該以「整個全球」的視野,在開放而彈性的思維模式下,對社會風險的來源與後果進行風險管理。貝克更提出「第二現代」理論,主張現代化的發展必須轉變為以「反省」為主要內涵,在國際社會學界奠定大師級地位。
本書是德國資深記者與貝克的對話錄,在簡明而精要的對談中,為貝克的各項重要概念作一次總整理,是接觸當代社會學大師、進入貝克思想世界最佳途徑。
作者介紹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慕尼黑大學教授,長期從事社會發展和全球化問題的研究,並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和概念。貝克透過宏觀、敏銳的觀察,提出「全球主義」、「解民族國家化」、「世界社會」等趨勢,主張人類應以「整個全球」的視野,來處理諸如生態、核武、貧富差距等全球性課題。
貝克也指出近二個世紀的現代化所衍生諸如SARS、AIDS、禽流感、狂牛症、金融風暴等種種「副作用」,已經對人類造成不良影響。他與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法國社會學家拉許共同提出「第二現代」理論,主張必須進行以「反省」為主要內涵的「第二次現代化」,在國際社會科學界獲得注目。此外,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也點出「高科技」與「高風險」之間的關連性,主張世人應該在一個開放的、允許充分彈性的新思維模式下,全方位地認識風險的各種可能來源與可能後果,並加以管理。
主要著作有《什麼是全球化》、《風險社會——通往另一個現代的路上》(巨流)、《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商務)、《自由之子》、《全球化的政治》、《反思性現代化》、《世界社會的前景》等重要社會學與全球化論述。
約翰內斯.威爾姆斯/Johannes Willms
德國著名歷史題材記者和編輯,現任《南德意志報》執行編輯,著有《德國病》等在德國極具影響力之著作。
譯者簡介/路國林
中央編譯局馬列部譯審,譯有《全球化與道德重建》、《全球化與政治》、《不要恐懼全球化》、《尼采傳》等大量德國哲學、社會學和文化書籍。
規格
商品編號:P0150003
ISBN:986134019X
頁數:256,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86134019X
ISBN:986134019X
頁數:256,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86134019X
各界推薦
我們更需要大師 / 張之傑(圓神出版事業機構顧問)
人類的學名是Homo sapiens(智人),但人類的智慧有個別差異,更有族群差異,以後者來說,有些已參奪造化,有些尚草萊未闢,我們不禁要問:同樣的人類,怎會差異至此?
拋開人類學的種種學理不談,我們認為,關鍵有二:第一,經驗能否積累?沒有文字的族群,積累受到限制,不可能發展出較高的文明。第二,積累出來的經驗,能否整理、提煉出更高層次的智慧?這就需要大師了。
大師這個詞,一般指受人景仰的學者、藝術家或宗教領袖。按其影響力,可分為若干等級,有的跨越時代,有的冠絕一時。前者如孔子,上古文化要是沒有孔子的整理、提煉,中華文化將是另一番面貌,古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是有其道理的。後者如胡適,幾篇鴻文引起文學革命,將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推上國語文學,造成思想界的空前變動,喻之為新文化的播種者,誰曰不宜!
人們對大師的尊崇,往往具有宗教意味,思想方面尤其如此。一些宗教的創始者——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等,都是大師中的大師,受到億萬教徒膜拜。在儒家文化圈,孔子「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同樣受到教主般對待。即使是一般的大師,追隨者也將他們的一言一行視為金科玉律。宗教超越理性,以信仰為基礎,是人類最堅實的思想活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師是「信眾」共同樹立的紀功碑。
因此,大師的產生,多少和人類的英雄崇拜有關。二次世界大戰後,鑑於核彈的巨大毀滅力,武勇已不足恃,英雄崇拜跟著式微,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另一方面,自社會主義集團瓦解,共產國家的種種不堪暴露在世人面前,人們這才憬悟到:烏托邦根本就不存在,那些驅馳人們追求烏托邦的思想或言行,都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局。於是人類不再汲汲於追求理想,連帶著,人們不免要問:我們還需要大師嗎?
事實上,我們更需要大師。
第一,上世紀九○年代初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強,意識型態對抗固然已成過去,但文明衝突升高,恐怖主義蔓延,貧富差距加大,生態危機嚴重。在這人類的未來愈來愈撲朔迷離的時刻,我們或許已不再需要英雄,但較任何一個時代更需要大師的指引。
第二,近二十年網際網路興起,彈指之間就可召來無量資訊,所謂「資訊爆炸」,已不僅是個形容詞。在科幻史上,科幻永遠走在科技前面,但網際網路是個例外。連科幻作家都未曾思及的網際網路,使得世界為之改觀,其影響豈止提供日新月異的資訊!我們需要大師,在這新興資訊體系下,建構不同於往昔的知識架構。
第三,自五四之後,民族主義興起,中國走上寡頭政治,獨裁者「作之君,作之師」,成為宇內唯一的「大師」。如今台灣已經民主,但國際政治處境尷尬,意識型態分歧,面對的問題遠較從前複雜。我們需要大師,為我們指出,如何使我們的民主脫離民粹、趨向成熟?
第四,近十幾年來,本土化潮流沛然莫之能禦,不過和一般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我們的本土化並非用來對抗全球化,而是用來對抗中國意識和中國大陸。然而,台灣和中國意識或中國間的千絲萬縷,豈是一句口號所能釐清?我們特別需要大師,為我們找到不亢不卑的文化定位。
是的,我們較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更需要大師!
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本社特別企畫了一個新的書系——「遇見大師」。我們從譯介做起,書系前四冊,以對談方式介紹四位當代德國大師——哲學巨擘哈伯瑪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大思想家伽達默爾和著名社會學家貝克。德國是哲學大國,從德國開始,具有標竿作用。
這個書系終將回歸本土,介紹我們自己的大師,域外大師固然開闊我們的視野,但終究不如本土大師親切。我們相信,繼若干前輩學者、藝術家、宗教領袖之後,繼起的本土大師將接踵出現。
透過這個書系,大師謦欬如在眼前。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大師們高屋建瓴的眼識,猶如知識之海的北極星,是攀登知識高峰的鎖鑰。當然了,讀者的支持,是本社最大的鼓舞,我們將儘量做好這個書系,俾不辜負讀者的期望。
人類的學名是Homo sapiens(智人),但人類的智慧有個別差異,更有族群差異,以後者來說,有些已參奪造化,有些尚草萊未闢,我們不禁要問:同樣的人類,怎會差異至此?
拋開人類學的種種學理不談,我們認為,關鍵有二:第一,經驗能否積累?沒有文字的族群,積累受到限制,不可能發展出較高的文明。第二,積累出來的經驗,能否整理、提煉出更高層次的智慧?這就需要大師了。
大師這個詞,一般指受人景仰的學者、藝術家或宗教領袖。按其影響力,可分為若干等級,有的跨越時代,有的冠絕一時。前者如孔子,上古文化要是沒有孔子的整理、提煉,中華文化將是另一番面貌,古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是有其道理的。後者如胡適,幾篇鴻文引起文學革命,將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推上國語文學,造成思想界的空前變動,喻之為新文化的播種者,誰曰不宜!
人們對大師的尊崇,往往具有宗教意味,思想方面尤其如此。一些宗教的創始者——佛陀、耶穌、穆罕默德等,都是大師中的大師,受到億萬教徒膜拜。在儒家文化圈,孔子「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同樣受到教主般對待。即使是一般的大師,追隨者也將他們的一言一行視為金科玉律。宗教超越理性,以信仰為基礎,是人類最堅實的思想活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大師是「信眾」共同樹立的紀功碑。
因此,大師的產生,多少和人類的英雄崇拜有關。二次世界大戰後,鑑於核彈的巨大毀滅力,武勇已不足恃,英雄崇拜跟著式微,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個沒有英雄的時代。另一方面,自社會主義集團瓦解,共產國家的種種不堪暴露在世人面前,人們這才憬悟到:烏托邦根本就不存在,那些驅馳人們追求烏托邦的思想或言行,都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局。於是人類不再汲汲於追求理想,連帶著,人們不免要問:我們還需要大師嗎?
事實上,我們更需要大師。
第一,上世紀九○年代初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強,意識型態對抗固然已成過去,但文明衝突升高,恐怖主義蔓延,貧富差距加大,生態危機嚴重。在這人類的未來愈來愈撲朔迷離的時刻,我們或許已不再需要英雄,但較任何一個時代更需要大師的指引。
第二,近二十年網際網路興起,彈指之間就可召來無量資訊,所謂「資訊爆炸」,已不僅是個形容詞。在科幻史上,科幻永遠走在科技前面,但網際網路是個例外。連科幻作家都未曾思及的網際網路,使得世界為之改觀,其影響豈止提供日新月異的資訊!我們需要大師,在這新興資訊體系下,建構不同於往昔的知識架構。
第三,自五四之後,民族主義興起,中國走上寡頭政治,獨裁者「作之君,作之師」,成為宇內唯一的「大師」。如今台灣已經民主,但國際政治處境尷尬,意識型態分歧,面對的問題遠較從前複雜。我們需要大師,為我們指出,如何使我們的民主脫離民粹、趨向成熟?
第四,近十幾年來,本土化潮流沛然莫之能禦,不過和一般第三世界國家不同的是:我們的本土化並非用來對抗全球化,而是用來對抗中國意識和中國大陸。然而,台灣和中國意識或中國間的千絲萬縷,豈是一句口號所能釐清?我們特別需要大師,為我們找到不亢不卑的文化定位。
是的,我們較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更需要大師!
基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本社特別企畫了一個新的書系——「遇見大師」。我們從譯介做起,書系前四冊,以對談方式介紹四位當代德國大師——哲學巨擘哈伯瑪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大思想家伽達默爾和著名社會學家貝克。德國是哲學大國,從德國開始,具有標竿作用。
這個書系終將回歸本土,介紹我們自己的大師,域外大師固然開闊我們的視野,但終究不如本土大師親切。我們相信,繼若干前輩學者、藝術家、宗教領袖之後,繼起的本土大師將接踵出現。
透過這個書系,大師謦欬如在眼前。所謂「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大師們高屋建瓴的眼識,猶如知識之海的北極星,是攀登知識高峰的鎖鑰。當然了,讀者的支持,是本社最大的鼓舞,我們將儘量做好這個書系,俾不辜負讀者的期望。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