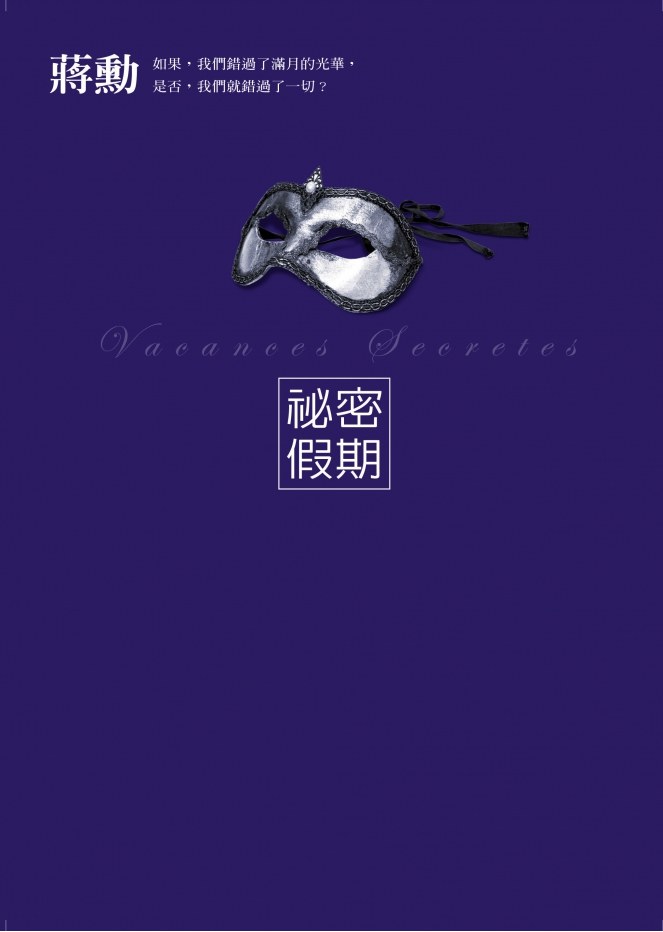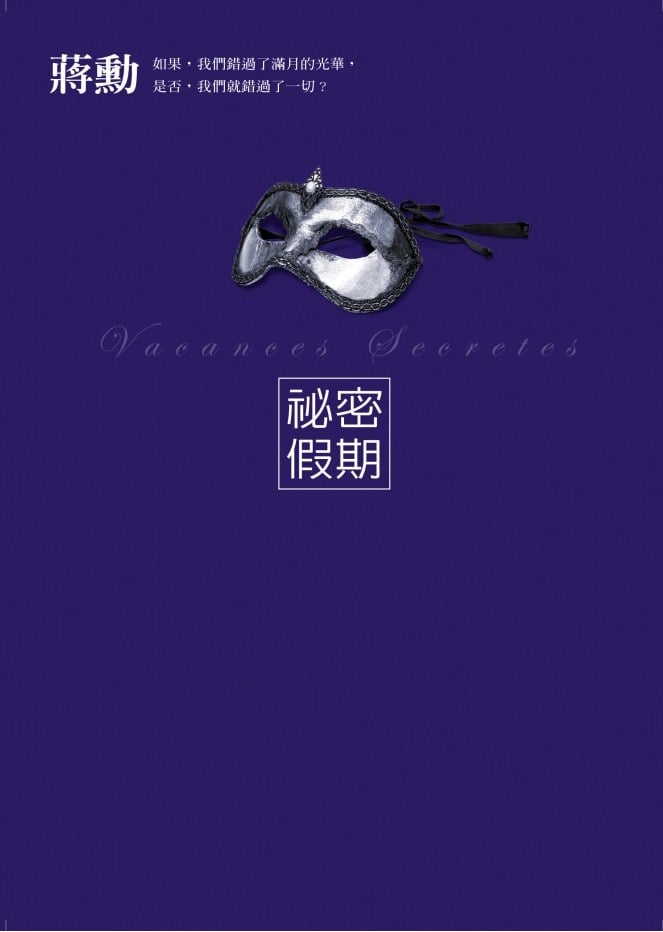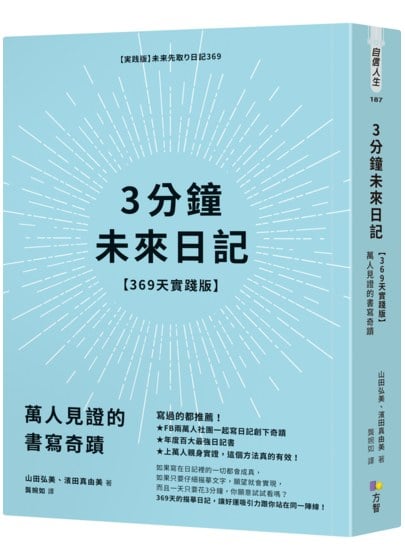1 杏子
許多橙黃帶紅色的杏子,許多夕陽燃燒起來的光,
一個不確定的約會,也許鴿子會帶來訊息……
我與他們都不相干。我坐在這個城市堆滿垃圾的角落。我看著因為感染傳染病一個接一個倒下去的城市居民。他們口沫橫飛議論著他人的種種時,那些憂鬱的病毒便藉著他們像霧一樣的口沫飛散到各處。病毒大約是0.06毫米,他們在陽光裡飛散開來,像隱匿不可見的細小精靈。病毒學家稱讚這種病毒結構精緻美麗如一朵綻放的玫瑰。病毒一旦從口沫散出,就像千千萬萬散布在空中的種子的飛絮,尋找他們可以依附生長的土地。他們附著在人類的身體上,等待人類好動的手來接觸。他們靜靜等候著,像童話故事裡最安靜溫馴的睡美人,等候愛人的撫摸親暱。
愛人來了。愛人沾染了滿滿的病毒,把病毒帶到最適宜於生長的地方,帶到潮濕溫暖的處所。鼻子孔洞四周的黏膜,眼睛邊眶濕潤的角落,當然還有嘴唇張開時一整個口腔富裕的環境。睡美人一一甦醒了。潮濕和溫度使他們甦醒。他們迅速生長分裂繁殖,從眼睛的邊眶、從鼻腔的黏膜、從一點點的口沫,分裂繁殖成上億兆的病毒。
睡美人甦醒後成為凶悍潑辣的殘毒者,他們擴張占據呼吸道、肺部,像凶狠的手,緊緊捏住呼吸的管道。他們又善於偽裝,使人類起而對抗的免疫系統找不到病毒,卻把自己肺部的細胞殺死。
病毒很無辜的說:人類死於自己的殘殺,與我們無關。
我坐在城市的角落,看見在陽光裡飛揚散播的口沫,看見成千上萬的病毒如春天的花絮飄揚。我知道,我的淚水即是繁殖病毒的溫床。這些溫熱的淚水啊!汩汩如湧泉傾瀉。我遏止不住地哭著,許多口沫飛來與我的淚水會合。我知道這樣的哭很快將殺死我自己。但是我停止不住,停止不住。
周芳坐在電腦前,等待開機後連接到她的網頁上。她在鍵盤上按下「Vacances
Secretes」幾個字。「祕密假期」,她看到一排行程:
七月二十八日羅馬許願池,中午十二時。
七月二十九日羅馬共和廣場,午後七點。
七月三十日佛羅倫斯,野豬銅像前,午後六點。
七月三十一日佛羅倫斯,上午十點半,烏菲茲美術館領主廣場前。
八月一日威尼斯,聖馬可廣場兩根石柱之間,午後七點。
八月二日威尼斯,聖馬可廣場,午後七時。
她看著詳細的行程,有點興奮,也有點恐慌。地方是她都沒有去過的,要見面的人也沒見過面。她繼續進入「祕密假期」的檔案中,畫面上出現Jason幾個字,然後是一張照片,大約二十幾歲的男子,大眼睛,咪咪笑著,戴了一頂帽簷很長的帽子,眉宇在陰影裡,所以不完全看得出長相。
「Jason,」她輕輕叫了一聲。
彷彿要確定那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但沒有人回應。電腦仍停留在那個戴帽子的男人照片上,笑咪咪的,好像在笑周芳。
Jason代表什麼呢?周芳想。
在網路上認識朋友,一開始只有透過名字去猜測一個人。
「你是什麼樣的人呢?」因為沒有見過面,沒有任何可以依據的確實資料,一開始只有憑名字去辨認一個人。
但名字也是假的啊!周芳笑起來。
周芳在網路上用的名字是「杏子」。那一天她從受訓的學校回家,路過市集,看到橙黃帶紅色碩大的杏子。她沒有學過杏子的法文,特別上前去看,牌子上寫著abricot。她買了一斤杏子,回家坐在電腦前,開了機,決定用這個名字來找尋網友。好寂寞的巴黎的日子啊!
兩年的受訓,課程很重。一個在異國的單身女子,過了三十歲,沒有機會結交法國的男子,也沒有機會參加台灣去的學生活動。她特殊的軍事單位派駐的身分,使她每天除了密集的語言訓練和專業的課程之外,幾乎一下課就回到住所,在高高的閣樓上,對著電腦發呆。這奇異的機器帶給了她很多快樂,好像她的領域忽然擴大了,不再只是這小到只有四十五平方呎的住所,不再是永遠沒有訪客的閣樓,她可以和幾千公里、幾萬公里外的人忽然之間促膝而談。
「我對妳只是陌生人。」Jason說。
「陌生嗎?」周芳回答:「那些街上的法國人才是陌生人,那些住在同一幢公寓的其他房客,在狹窄的樓梯上相遇,禮貌地說:Bonjour!或Bonsoir!那才是陌生人。我生活在一個懂語言而無法談心事的國度,生活在上千上萬的陌生人之中。」
「妳叫杏子,妳有日本血統嗎?」Jason問。
周芳吃吃笑了起來,她覺得網路交友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每一個人都盡量隱藏自己,用許多假的、別人不容易找到線索的符號來偽裝自己。但是,每個人又依憑著別人的假的符號,認真去猜測對方是什麼樣的人。
「Jason」,這個名字實在太通俗了,除了想像對方可能喜歡搖滾,喜歡好萊塢電影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思考的線索。
「所以我給你的『杏子』這個符號是比較真實的。對不對?」周芳又吃吃笑了起來,她回想到那天市集上橙紅橙紅的「abricot」。她又把這個水果的法文念了一次。
以後在網路上交談久了,她逐漸習慣Jason的書寫方式。他對很多事都有意見,主觀很強,善辯,喜歡分析時事。周芳在巴黎的生活除了受訓,可以說乏善可陳,她也因此從Jason的E-mail中得到許多有關台灣發生的新聞。
一隻鴿子飛來,停在閣樓朝西的窗戶邊緣,隔著玻璃,側著頭,用一粒紅豆般的眼睛向內窺探。
周芳把桌上隔夜的乾麵包掰碎了,打開窗戶,撒在窗台上。鴿子一點也不怕人,等周芳撒完了,低頭一一叼啄起來。
「今天鴿子來早了。」周芳回到電腦桌前繼續E-mail給Jason:「這隻灰色的鴿子,頸部有一圈亮藍色的羽毛,每天黃昏飛來窗台。牠像愛人一樣,忠誠守時。我也信守允諾,一定在窗台上撒些乾麵包。」
鴿子吃了一會兒,在窗台上踱步,左右來回走著,發出咕咕的聲音。
「羅馬,威尼斯的廣場也都有許多鴿子,你會喜歡鴿子嗎?你會像鴿子一樣守時嗎?」
Jason,我給這次的義大利假期訂了一個法文的名字:「Vacances Secretes祕密假期。」
周芳把E-mail傳出去之後,發現窗台上的鴿子已經飛走了。她走到窗邊,窗台上還遺留著少許麵包的碎屑。接近七、八點鐘了,初夏黃昏夕陽的光血紅燃燒一樣反映在窗戶上。
她覺得有些刺眼。夕陽的紅光使窗戶的玻璃變成了一面鏡子,周芳的上半身就照映在夕陽中成為重疊的畫面。周芳看著玻璃上的自己,圓圓豐腴的臉龐,披肩的頭髮,一對彎月形的眉毛。特別明顯的是她隆起飽滿的胸部以及渾圓多肉的臂膀。她看著看著,用手撫摸著自己的臂膀。
她穿的是一件橘紅無領無袖的洋裝,她把肩帶卸下來,可以更完整地看到自己從肩膀到手臂那圓潤的線條。領口隨卸下的肩帶掉下來,露出雪白豐厚的胸脯。她的手移到胸口,感覺到有一點加快的心跳。周芳閉起眼睛,在夕陽的光燦爛到極致時,對著玻璃叫了一聲:Jason。
2 Jason
生命裡改動一個字,或許是一次重大的改變。
改動一個字,可能從記憶中完全消失了嗎?
如同在鍵盤上按了「刪除」,徹底的「刪除」,再也找不到一點痕跡……
我可以從哪裡找回來消失的檔案?我在鍵盤上絕決地按下了「刪除」,一切都剎那間不見了。但是我按不到我記憶的鍵盤,我即使按到了,記憶卻不消失。我記憶的鍵盤失去了功能。我用力按著,刪除、刪除、刪除,記憶卻一一跳出來。每一個畫面都如此清晰,站在我的面前,逼近我,冷冷看著我說:你無法刪除我,我在你的身體裡,我在你的血液裡,我在你的細胞裡,你刪除不掉你自己。 我刪除不掉我自己嗎?
我尋找著刀子。我用刀切割手指。手指一一斷落,骨骼、皮肉、筋、一些搞不清是什麼的糊裡糊塗的東西。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記憶。記憶在哪裡?
記憶在哪裡?
記憶站立在我的四周,環繞著我,看著我,彷彿疑惑著我為什麼手裡拿著刀子。他們又檢視遺落在地上的我左手的手指,看著我繼續切掉左手的手腕、手肘、手臂。
在切割肩膀的時候我花了一些力氣,那個地方的筋骨特別頑強。我用力把刀嵌進骨節的間隙,肢解開糾纏的牽連,我毫不放棄,我要檢查每一個肢解開的片段,我要仔細檢查那些陰魂不散的記憶究竟隱藏在哪裡。
我處理腳趾和腳踝的時候,記憶忽然發問了,他們說:你最後是不是只剩下拿著刀的右手?
我最後是不是只剩下拿著刀的右手?
我開始害怕起來。我開始想像我切掉了腿,切掉了臀部,切掉了肚腹,切掉了纏結的腸胃內臟,切掉了空空蕩蕩的胸腔,甚至我切掉了最可能隱匿記憶的頭腦……
最後,只剩下停留在空中的一隻右手,握著一把刀……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切割嗎?
記憶環繞著支離破碎的我,看著我,充滿了無奈又憐憫的表情……
「Jason」
巫善祥在電腦上收信,是杏子從巴黎E-mail來的見面的行程。他心裡有些煩,匆匆瀏覽了一下並沒有細看。
他用密碼打開自己的筆記本,開始每天固定的日記:
「今天跟爸爸吵了一架。又是股票斷頭,要我每個月負擔六萬元的利息。我的薪水就全泡湯了。工作了一年,什麼儲蓄都沒有,就是為這個家還債,還債,還債。shit!
我一定要出去度假了,不然真要瘋掉。
但是錢怎麼辦呢?
找錢鈞罷!但是太久沒有聯絡了,錢鈞還顧念這分舊情嗎?
走一步算一步罷!」
善祥把電腦關掉,坐在電腦前發呆。
他打開白天上班的公事夾,上面印著一行字:法務部××局。
白天的工作很繁雜,要處理訓練單位裡一百多位學員的課程,每一位講師的接送,要把每一項課程的上課講義準備好,要安排不同課程需要用到的設備,幻燈機、錄影機、攝影機,稍有差錯,就要挨長官一頓削。
「巫善祥,心不在焉啊!」那個賊頭賊腦的朱組長,不時閃進來戳他一下。
「媽的!」他心裡恨恨的。
但是他外表很柔順。天生一張娃娃臉。雖然三十歲了,看起來不過大學剛畢業的樣子。
一雙齊整的眉毛,短短的鼻子,清澄而大的眼睛,紅潤豐厚的嘴唇,加上總是笑咪咪的,是頗能討人喜歡的長相。
「善祥,來吃點水果。」弄文書的趙大姐就把他當弟弟或兒子,每天中午看他胡亂吃一點泡麵,常常削了水果,或帶一個粽子給他。
「善祥,該交個女朋友了,老是這麼單身,吃也亂吃,生活也沒個規矩。」趙大姐說。
他知道別人是好心,但碰到這個心結,他還是尷尬著。一面吃水果,口中一面含糊地支吾著:「有個女朋友在巴黎,夏天放假,約了一起去義大利。」
他想到杏子,那個從沒見過面的網友,想到她說的「祕密假期」。
「祕密假期,」巫善祥靈機一動,「是應該設計一個『祕密假期』。」
他又在電腦上搜尋了一下,出現了一名裸體的男子像,同志熱門網頁。
他找到有關荷蘭一年一度同志大遊行的檔案:「八月四日,星期六,將有上萬同志從世界各地湧入阿姆斯特丹,屆時旅館爆滿,請務必早早訂房。」
「八月四日下午,在Waterlooplein的運河區有遊船表演,有白色派對,白色派對即每人均須穿白衣白褲。」
他把幾段相關的文字都下載列印了下來。用紅筆很認真勾出重點。
「跟杏子在威尼斯分手,八月三日直接飛荷蘭,剛好參加世界同志大遊行。痛痛快快玩三天,六日回台灣,七號到!」巫善祥鎖著眉想了一下:「這樣除了十天的例假,還得多請一天的假。」
他有些開心起來,覺得是一個完美的安排。
「只差錢鈞的加入了!」他心裡盤算了一下:「錢鈞七月在伊斯坦堡有個會,邀他會後一起去義大利,他負責機票、旅館、火車票,一切就沒問題了。Perfect!」
他脫掉衣服,走到浴室沖了一個澡。他從小被父親嚴厲要求運動,每晚上床前一定至少做五十個伏地挺身;雖然這一年局裡的工作忙,運動有些荒廢了,但一身鼓鼓的肌肉還是十分漂亮。
「這是被錢鈞讚美過的身體。」他在鏡子裡看了一眼。一道細細的水流從兩塊隆起的胸肌間的隙縫往下流動。
他圍著大毛巾,跨過一地亂丟的衣物,比較確定地告訴自己︰「這個祕密假期裡要有我,有杏子,有錢鈞!」
應該給錢鈞打一個電話了。他看看時間,夜裡十一點。打到家裡,怕錢鈞的老婆會接。
還是打他手機罷!
一陣子沒和錢鈞聯絡,找到號碼,按了「撥出」鍵,響了兩聲,轉到語音信箱:請在嘟聲後留言。「喂,好嗎?我是善祥,請給我回電。」
3錢鈞
從旅館三十三樓的高度看出去,城市港灣夜晚繁華的燈光亮成一片。
從遠處航行而來的巨大船隻或要航行向遠方的巨大船隻交錯而過,
時間或空間只是不可解的宿命……
我沒有辦法解釋自己迷戀港灣的原因。小時候會離家坐火車一個人到距離最近的海港。下了火車,沿著港灣碼頭邊的路走。鹹鹹腥腥,帶著魚體海藻在日光下曝曬濃烈氣味的海風,一陣一陣撲面而來。港灣的海水上浮膩著一層亮晃晃的油漬,是從船舶底層滲漏出來的引擎機油吧,在水面上浮蕩,隨著日光映照,搖曳成彩虹一樣炫目斑斕的圖紋。我看久了,總覺得是海底人魚一類童話生物噓吸出的迷幻符咒,可以引領我進入神祕瑰麗的深海,可以在珊瑚珍珠銀色貝殼的洞穴裡做一個長久不醒滿是彩色的夢。
港灣沿路都用粗大結實的鐵鏈圍起。鐵鏈日久銹蝕,拴結鐵鏈的水泥樁上都沁蝕了褐紅色像舊血跡一般的鐵銹痕跡。有人坐在鐵鏈上垂釣,打著赤膊,赤黑油亮的肉體,像一塊火成岩,杵立在驚濤駭浪的海邊。
我常常被低沉苦悶大船鳴叫的汽笛聲驚醒。
我不知道自己在海邊坐了多久,那些像火成岩石塊一樣一動也不動的垂釣者,那些銹爛的鐵鏈,那不停在水面上搖晃的浮動油漬的彩虹般的光,那些大船出海或歸來時低沉苦悶的汽笛鳴叫,在我恍惚的睡夢中歷歷在目的景象,為何當我醒來,景象仍然一樣,好像天長地久沒有任何改變。
我一次又一次來到海邊,坐在碼頭邊眺望大海,我是在等待揚帆出海?或者我是在迎接守候遠洋歸來的自己?
我那時候只有九歲,我無法搞清楚離家坐在港灣邊發呆的意義。
大船過去,港灣裡會震盪起巨大的波濤,驚濤駭浪,一層疊一層,盪漾開來,向四方推滾。
我覺得那些大浪就要擊打到我身上,我覺得那些驚天動地的波濤,即將把我震碎,震到粉身碎骨。
有飛濺而來的浪沫噴撲到我臉上,我坐著不動,我靜靜等候滅頂的大浪襲來,我靜靜等候崩解、潰散、沉沒、在浪花迴旋裡消失,無影無蹤……
錢鈞把手機忘在台北。他到高雄開一個會,結束了,一個人坐在旅館第三十三樓的窗邊,眺望一片亮著燈光的海港。
他剛撥了一個電話給瑩如,瑩如說:「診所沒事,該做的都做好了,別擔心。」
擔心什麼呢?結婚二十五年了,什麼時候擔過心?
錢鈞從冰箱拿出一瓶小瓶的sauvignon紅酒,倒進杯子,拿到窗邊,望著港口發呆。
他想起了巫善祥,想起四年前與他邂逅的那個奇特的晚上。
那次是為了來高雄「打書」。出版社的人叫做「打書」,但是對錢鈞來說,一個成功的醫生,業餘寫詩,出一本詩集,不過是好玩,並不那麼在意銷路。
「打書,可以不必了罷!」錢鈞想拒絕。
但是拗不過出版社,只好南下辦了一場演講、簽名會,回答一些讀者有的沒的各種問題。
寫詩弄到要「行銷」,有點倒胃口。晚餐間錢鈞又被鬧酒,多喝了幾杯,回到飯店,有點躁悶,一時不想睡,就跑到旅館地下樓的書店看書。
四年了,錢鈞仍然覺得那個邂逅這麼像一場夢。
「是幻由心生罷!」有時他這樣嘲笑自己。
「如果我們的婚姻有了外遇呢?」他和瑩如二十週年的結婚紀念日,他拿著一杯紅酒,挑逗地問著瑩如。
「你是說你,還是我?」瑩如也笑著反問。
「妳?」錢鈞搖搖頭:「不可能,妳所有的心都在這個診所了。這二十年,妳想想看,妳離開這診所幾天?我們連一家人去度個週末假期的旅行都屈指可數。」
「以前診所忙,兒子又小,怎麼走得開?」瑩如試圖要解釋。
「現在呢?」錢鈞苦笑著:「診所還是忙,兒子十八歲了,整天不在家。」
「妳從來沒有擔心過我會有外遇嗎?」錢鈞繼續追問。
「不會。」瑩如很篤定地回答。
「為什麼?」
「你所有的熱情都在寫詩,你對我的熱情,對醫學的熱情,都遠不如寫詩。」
「怎麼說?」
「那篇書評這樣結論: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瑩如有點調侃地看著錢鈞。
「浪漫主義者的戀愛,也只是為了寫詩罷。」
「哈——」錢鈞笑起來:「這好像是控訴!結婚二十週年紀念的控訴!」
「也可以是讚美。」瑩如快樂地說:「我們從學生時代相識,我們的戀愛是很文藝青年的戀愛。結了婚,生了孩子,我害怕你的浪漫夢想會破滅,盡量擔下診所的擔子。這幾年我不擔心了,我發現,只要你寫詩的激情在,你不會破滅,你在寫詩裡營造了一個完美的夢想,所有現實的冷酷,醜惡,煩雜,髒穢,都被排除在外。」
「所以——」錢鈞有點像孩子撒賴地做了一個沮喪的表情:「我不會有艷遇了!」
「瑩如,妳錯了。」錢鈞有一點苦楚地望著大片玻璃窗上夜晚高雄的天空,黑黑的,卻反射著不知道哪裡映照過來的鐳射和霓虹的光線,一片紛亂。
那個夜晚,他站在書店的旋轉樓梯旁,這是一間兩層樓的書店,中間打了一個洞,用旋轉梯連接起來。
一個青年從樓梯上下來。頭髮短短的,一臉陽光曬紅的膚色,笑咪咪的。穿了一件白色背心,寬肩厚背,胸前和手臂的肌肉都鼓鼓的。從樓梯上咚咚咚下來,藍色泛白的牛仔褲,緊緊包裹著大腿,一雙短筒靴子。他站定了,正好接觸到錢鈞的目光,錢鈞心一震,「好明亮的年輕人,一身都是陽光——」
青年朝錢鈞若有若無笑了笑,繞到攝影書區,錢鈞看他打開一本拍攝人體的攝影集。
錢鈞手上正巧拿著下午演講時自己新出的那本詩集。他覺得酒湧上來,頭腦熱熱的,有什麼不可遏止的東西在心裡洶湧。
錢鈞走過去,把書遞給那青年,說:「可以送你一本書嗎?」
青年靦腆地笑起來,臉上一層紅暈,但似乎並不意外,他接過來說:「為什麼送我書?」
「我剛出版的詩集。」錢鈞仍然覺得身上熱熱的。
「情不自禁——」青年看了一下書名。笑著說:「我喜歡這個名字。」
「我叫錢鈞。」他覺得應當自我介紹。
「我知道你。」青年說:「報上說,成功的醫生,成功的詩人。」
「活著,應該尋找失敗——」錢鈞忽然想起自己的詩句:「尋找可以打敗自己的人!」
「我叫巫善祥——」青年伸出手,介紹自己說:「巫婆的巫,善良的善,吉祥的祥。」
「高雄人?」
「嗯,」青年猶疑了一下,閃過一抹陰影,說:「在當兵。放假,不想回家。」
「我能問為什麼嗎?」錢鈞覺得萍水相逢,好像不應該探人隱私。
「我在台北讀大學,念法律。畢了業,考研究所沒考取,爸爸在我房門上貼了大大一個毛筆字『恥』。恥辱的『恥』。我當兵半年了,放假了就在外面亂逛,就是不想回家。」
「出去走走嗎?」錢鈞覺得書店裡人太多了。
「好,去哪兒?」
「我對這個城市不熟!」
「我帶你去老鹽埕區的酒吧喝酒!」
高雄的風也是熱的,白天的暑氣從地面上蒸騰上來,海洋的濕氣使風沉甸甸,好像黏在皮膚上。錢鈞坐在巫善祥的摩托車後座,覺得街市的繁華都很恍惚。閃爍的霓虹燈,吵嚷的人潮,呼嘯而過的飆車族,坐在街道兩旁小攤子上吃食的食客,老闆一面在砧板上剁著豬腳,一面狠狠地招徠客人:「來坐啊——」
善祥的車子騎得很慢,在行人中穿梭,像滑翔一樣。錢鈞許久許久沒有騎摩托車,在後座,有一點僵直,兩手緊緊抓著自己身後的橫槓,腳也不知道該往哪兒放。
善祥回過頭,用力抓住錢鈞的小腿,放在踏板上,大聲說:「抱著我的腰,小心,要騎快了!」
錢鈞的小腿上留著那實實在在手掌抓過的力量。他奇怪著這麼直接的肉體上的記憶,彷彿就留在肉體上,不再消失了。
「抱著我的腰啊!」善祥又回頭叮囑。
錢鈞還是沒有抱他的腰,而是兩手搭在他的肩頭上。他可以感覺到他肩頭骨骼和肌肉用力和放鬆的狀態,感覺得到轉彎、加速、煞車時那臂膀用力輕重不同傳達出來的肉體變化。
「我被肉體打敗了——」錢鈞搖晃著杯子中紅色透明的液體,一種混雜著陽光、雨水的葡萄發酵氣味瀰漫開來。
在善祥的後座,發現他頸部幾塊圓圓的汗斑。因為太靠近了,那年輕男子身體在暑熱中散放的氣味,一種鹹腥帶著熱度的肉體活潑的氣味,使錢鈞覺得感官上奇異的亢奮。
「到了!」他煞車很猛,錢鈞整個人向前衝貼緊善祥的後背。
善祥把安全帽鎖進後座的貯物箱,揹起背包,一面鎖車一面用下巴指一指:「那邊!」
錢鈞看過去,一個裝飾了棕櫚樹的酒吧,幾個紫藍色霓虹燈圈成的店舖招牌:老船長,一閃一閃的。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