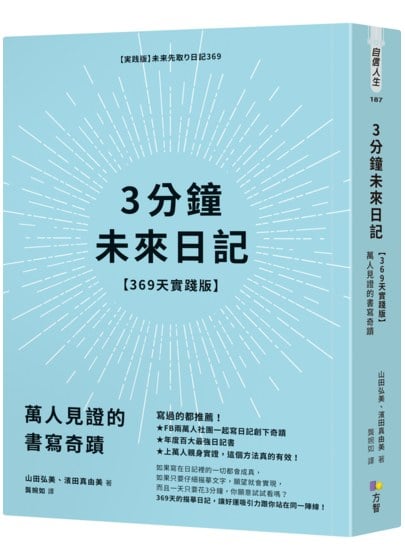內容簡介
愛與理性,是可以並存的嗎?
為什麼當他意圖摧毀心中的深愛,竟也同時摧毀了自己的理性?
如同人意圖影響天氣,卻造成了旋風與海嘯一般……
★美國才女橫掃國際文壇經典之作。美國亞馬遜最佳推薦書、紐約時報&各大媒體年度選書!
★書評讚譽「極具村上春樹味道」,結合波赫士的博學風趣,與辛普森家庭的獨特幽默,談的卻是愛與理性的真諦。
★李立亨、鄧惠文、貴婦奈奈一致推薦!
去年十二月,一個長得跟我妻子一模一樣的女人走進我的公寓,隨手把身後的門關上。外表看起來一模一樣,但卻不是我深愛的妻子芮瑪……
事業有成的他,嚴重懷疑妻子是個冒牌貨,並打算用一切方法去證實自己的想法無誤。
天才女作家葛茜透過一幕幕愛情心理懸疑場景,一波波隱形憂傷的轟炸,精湛描寫李奧醫師意識到妻子神秘失蹤後,如何拼湊、回溯、追索生命中曾有過的真愛足跡,並巧妙運用大氣變化解讀愛的真諦:如果我們無法預測明日的天氣,又怎能準確預知愛情的未來之路?
看完全書,我們不禁要問:愛與理性,是可以並存的嗎?為什麼當他意圖摧毀心中的深愛,竟也同時摧毀了自己的理性?如同人意圖影響天氣,卻造成了旋風與海嘯一般……
作者介紹
莉芙卡‧葛茜(Rivka Galchen)
自西奈山醫學中心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於南美洲公共衛生機構工作一年;之後以羅伯‧賓漢獎金﹝*Robert Bingham Fellow,是美國筆會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頒發給傑出處女作小說家所設立的獎金﹞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完成藝術碩士學位。
才華洋溢的葛茜,不時在國際性醫學雜誌發表文章,並於2006年獲得朗納‧賈佛基金會(Rona Jaffe Foundation
)作家獎項殊榮。
《我們之間,大氣干擾》是她的第一部小說,出版前已在2007年倫敦書展造成旋風;2008年5月出版後,不僅獲得「紐約時報」書評頭版報導,更被列為夏季必讀佳作!此外,她以身為美國皇家氣象學會成員的父親之名齊維(Tzvi Gal-Chen)嵌入書中一角,堪稱一書寫創舉。
這部作品除了入圍許多小說獎項決選、加拿大國家級總督文學獎(Governor
Generals Award)的提名,更榮獲亞馬遜網路書店最佳推薦書、紐約時報年度選書、美國沙龍知識網年度十大好書、克里夫蘭報年度好書、苛評雜誌年度好書等肯定。
<關於譯者>丘淑芳
台灣大學外文系及外文研究所碩士。
畢業後曾任聯合報編譯、新埔技術學院講師,二○○○年移民加拿大,考取加拿大認證筆譯員資格,開始從事社區與醫療口筆譯工作,現專事譯書,譯著有《第二十個妻子》《醜聞筆記》《地球玩一年》《歡喜過一生︰歡笑、喜樂與醫治》。
規格
ISBN:9789861333151
頁數:320,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789861333151
各界推薦
五十一歲的精神科醫師李奧一覺醒來,赫然發現一個很像妻子芮瑪的女人,抱著一隻黃色的小狗走進他的生活。
卡夫卡《蛻變》的主角醒來變成蟑螂,我們隨著這隻小強在天花板,俯瞰人生的怪誕與痴狂。《我們之間,大氣干擾》讓男主角的女主角出現了分身,讓我們用他的眼睛,開始點滴回味起睡覺前還在身旁的她,為什麼曾經那麼迷人。
《蛻變》裡的「我」,先是受驚,然後變得辛酸,最後只能接受這個變化。本書作者莉芙卡.葛茜,讓「我」先存疑,接著想方設法的去求證,最後才赫然發現自己,好像並沒有真正認識自己的另一半。
這本熟男回顧(和預演)情人(準備)教會他所有的事的書,把我們帶進了一個被「大氣干擾」之後的愛情世界。
永遠愛對方?Yes, We Do!
李奧有個精神病人哈維,堅信自己專門在替「皇家氣象學會」處理一些「大氣方面的工作」。芮瑪建議哈維飾演學會的特務,她擔任下指令的博士,好讓哈維相信他們真的理解他,進而願意配合醫院的療程。
哈維突然失蹤兩天之後,「冒牌」的芮瑪接著出現。雖然這個女人知道李奧有偏頭痛的毛病,說話也帶著芮瑪特有的阿根廷口音。但是,他知道她不是他的她。會不會,這一切都是精神醫師自己的精神漫遊?
可是,黃色小狗開心的舔著他的腳。這,這也不真實得太真實了。
李奧在圖書館尋找皇家氣象學會資料之後發現,芮瑪所曾假冒的齊維博士,不但真有其人,而且同樣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李奧想起他在匈牙利脆皮點心店,鼓起勇氣跟年輕芮瑪搭訕的許多細節。我們一方面感受到初戀的甜蜜,一方面也在心中出現電光石火般的念頭:芮瑪會不會是齊維博士的女兒呢?
李奧回想起他們交往過程的種種,以及婚後生活的點點滴滴,這讓他更堅定了想去芮瑪故鄉尋找她的信念。有首歌曾經這麼唱著說:「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麼?」這一刻,我們跟李奧一樣,我們只會想到對方有千百般的好。
現在,我們不但願意,而且我們「要」永遠愛對方。我們願意這樣做,只求生活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此刻的我們,已經從結婚典禮上面的I Do,集體化的改成We Do。
把一種行業寫得如此有趣
電影「美味關係」裡,年輕茱莉亞,煮遍美食家茱莉亞食譜中的每一道菜。她的行動,恰恰也成了檢視生活態度的放大鏡。按照真實故事寫成小說的原著,讓大螢幕前面的你我,感受到「烹調」這門功夫的精到與細微之處。
日本剛得到去年奧斯卡最佳外片獎的電影「送行者」,讓我們看到日本葬禮中禮儀師工作的許多細節。圓神最近出版的《心的誦讀師》,講的是可以看到書中情節立體畫面的人的故事。另外一本《火的秘密》,描繪的是西洋棋世界高手所遇到的恩怨情仇。
這兩本書跟兩部電影,帶我們走進四種不同嗜好與工作,所面對的另一種世界。《我們之間,大氣干擾》從天氣出發,以氣候多變化的可能性,一片片為我們重組這對被大氣干擾的夫婦的人生拼圖。
特殊行業的許多理論、想法、爭辯,以及行為和判斷上面的講究,為閱讀時光增添了許多知識上的光芒。我們因為作者的博學,而願意相信這些虛構出來的奇思異想。雖然,我們此時可能也想問,為什麼,台灣怎麼就很少出現這種可以把一種行業寫得很有趣的小說家呢?
但是,哎呀,我們還是打開霧燈,快快翻頁下去,看看李奧醫師還會遇到什麼讓他既惆悵,又會小驚小嚇的迷霧吧。
文學也可以像電影那樣分割成好幾個畫面
李奧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咖啡館,遇到長得很像芮瑪的服務生。為了如果她萬一真的是她的一絲可能性,年已半百的李奧在帳單上面寫下:我愛妳。
這聽起來實在很可愛。不可愛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還有另一個冒牌的芮瑪。這個服務生是她的同學,服務生要她跟他說,她對他沒有興趣。
我們能說什麼呢?原本是假的,現在變成真的。原本是真的,現在卻變得越來越不真實。芮瑪假冒的博士、芮瑪的母親、芮瑪的分身,還有哈維跟所謂的皇家氣象學會,此起彼落的出沒在李奧身邊。我們的主人翁,眼看就要被謎團的大雷雨給淋成落湯雞了。
故事的發展,實在大出我們所料。哈維給李奧發來他所想像出來的「情報」,齊維博士也按照他們過去使用過的「劇本」在給李奧發簡訊。這一切,讓我們驚喜的發現,文學也可以像電影那樣分割成好幾個畫面,而且是發生在同一個時間。
愛情,嘿嘿嘿,愛情,就是有辦法讓一切都變得有可能。不是嗎?
我們所愛的人,究竟是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人
隨著李奧的足跡,我們感受到愛情的甜蜜,我們也明白愛情跟天氣一樣喜怒無常。
李奧所面對的困境,究竟是夢,是精神分裂的狀態,或者是假做真時假亦真的巧合呢?芮瑪去了哪裡?她到底會不會回來呢?或者,芮瑪會不會根本就是李奧想像中的人物呢?我們是不是真的認識我們的愛人?或者,我們所愛的人,究竟是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人。
等到我們掩卷嘆息時,我們應該都會想要感謝作者,謝謝她用溫暖而優雅的微風筆觸,讓我們對愛,對永遠,都願意保持憧憬。
(本文作者為上海世博會「城市廣場藝術節」總導演)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 / 貴婦奈奈
老梗的愛情故事該用什麼主題包裝才能給出新時代的詮釋?用天氣如何?了不起。就算科學再進步,我們都無法準確的預測天氣,又能仰賴什麼標準洞察人心呢?即使親密如枕邊人,也沒人敢說自己百分之百了解對方。
人生就是這樣,自以為懂,其實什麼都不懂。
看完這本書,我想起以前心理治療臨床督導對我們耳提面命的話──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I know I dont know)。
(本文作者為諮商心理師&人氣格主.暢銷作家)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