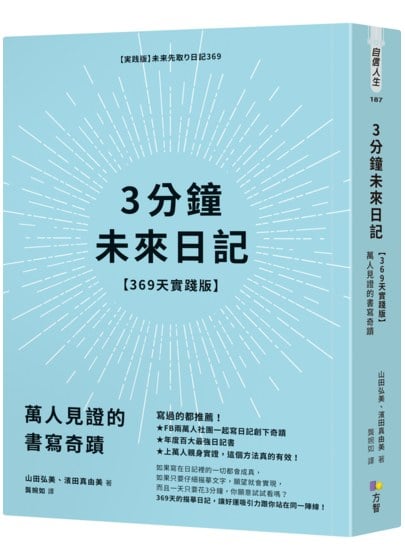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每個進入俄國的旅人,行囊中不可或缺的一本書
「布爾加科夫是最偉大的當代俄國作家之一,也許正是最偉大的一位!」 獨立報
「不是苦澀的諷喻,而是充滿狂野的生命之愛!」 新德國
莫斯科市民票選「最了不起的20世紀俄國作家」No. 1,當代俄羅斯人最喜愛的作家──布爾加科夫
深刻媲美《浮士德》,偉大啟迪《魔鬼詩篇》,精采堪稱《魔戒》《哈利波特》等奇幻小說之祖!
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歐茵西,導讀推薦!
【本書簡介】
「布爾加科夫是最偉大的當代俄國作家之一,也許正是最偉大的一位!」 獨立報
「大師之作!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 紐約時報
「本書令人心醉神迷!」 世界週刊
「在俄文文壇上,布爾加科夫的形象至為特殊。他的筆下充滿天馬行空的奇幻變化,藝術魅力豐富,思維深刻,堪稱魔幻文學的經典代表。」 台大外文系教授 歐茵西
人連今晚的事都無法篤定,又如何掌握得了自己的命運?──撒旦
本書描述魔王捉弄莫斯科人民,富有深厚的警世意味和魔幻哲理,創作過程極其傳奇。
布爾加科夫以兩年時間完成15章的寫作,但在政治鬥爭氣氛下遭文學界打壓時,卻將手稿付之一炬。之後,在生活困頓、親友疏離、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持續寫作12年,八易其稿,直到身患重病還在努力修改。因為政治壓迫,此書脫稿30年仍不能出版,但在1966年解禁問世後,立即轟動文壇,暢銷20年,議論反響歷久不衰。
布爾加科夫的想像力及技巧令人嘆為觀止,文學後輩難以望其項背。《大師與瑪格麗特》初看神鬼、歷史、愛情三條主線交叉鋪陳,再看卻有重重伏筆,故事中又有故事。全書一氣呵成,既有推理懸吊人心的快意,又能啟發讀者對精神信念的思考。在宣揚無神論的蘇聯時代,布爾加科夫以此書大膽高呼對宗教信仰的堅持,寓意深長,更犀利透視善惡、愛恨、生死,揭露藝術家的創作本質,涵括多重美學風格與命題。
本書多次受改編為戲劇、電影與音樂作品,更於2005年底改編為電視影集,播映期間在莫斯科的收視率曾突破50%,令世人驚豔於這部小說的永恆魅力。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 布爾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
莫斯科市民票選「最了不起的20世紀俄國作家」No. 1,當代俄羅斯人最喜愛的作家。
1891年生於基輔,父親是神學教授,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喜愛文學、音樂、戲劇,曾夢想當歌劇演員。九歲時初讀《死靈魂》,便深深愛上果戈里獨特的諷刺藝術風格。中學畢業後,他考入基輔大學醫學院,十月革命時已在一所國立醫院工作了一年半。行醫之餘,他也為地方報刊寫些文章,為劇院寫些宣傳性劇本,初步顯露出幽默和諷刺的才華。
1920年他放棄醫生職業,開始文學生涯,以親身經歷寫出一系列發人深思的短篇小說和小品文,揭露並嘲諷當時種種不良的社會現象,以深入而細緻的觀察、風趣辛辣的筆觸贏得讀者的喜愛。
布爾加科夫經歷二○年代蘇聯政治思想的鬥爭,這段時期所寫的作品都遭到查禁沒收,但他並未被擊垮,仍書寫不輟,於1928年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甚至1940年於莫斯科逝世前,仍不忘對這部作品進行口述刪修,以求完美。但此書遲至1966年十二月才由蘇聯大型文學刊物《莫斯科》首次發表,自此成為俄語文學的一大代表作。影響之鉅,八○年代蘇聯太空人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即以「布爾加科夫」命名。轟動歐美與阿拉伯世界的作家魯西迪也曾表示,《魔鬼詩篇》的創作深受《大師與瑪格麗特》所啟發。甚至流行音樂界如「滾石」「珍珠果醬」合唱團的作品亦從小說中取材。
規格
ISBN:9789861371092
頁數:496,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789861371092
各界推薦
【導 讀】
布爾加科夫的魔幻藝術 / 歐茵西
在俄文文壇上,布爾加科夫的形象至為特殊。他的筆下充滿天馬行空的奇幻變化,藝術魅力豐富,思維深刻,堪稱魔幻文學的經典代表。
布爾加科夫(Michail Afanasevič Bulgakov,1891-1940)出生於烏克蘭神學教授家庭,宗教和聖經的浸潤甚深,是《大師與瑪格麗特》靈感的重要泉源。一九○九至一九一六年就讀基輔大學醫學系,畢業後,在斯摩連斯克(Smolensk)及基輔鄉間行醫,培養了入微的觀察力,也是早期作品的素材。《一名年輕醫生的筆記》(Zapiski junogo vrača, 1926),記述行醫見聞,對當時俄國社會的頹廢與徬徨,有非常敏銳的觀察。共黨政權建立後,社會遽變,他棄醫從文,遷居莫斯科,在報社和雜誌社工作,並開始投稿,漸有文名。
一九二四年完成第一部小說《白軍》(Belaja gvardija),以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基輔城為背景,寫一次大戰末期,德軍倉惶撤退,烏克蘭反共白軍與紅軍陣營的激烈戰鬥。白軍堅持信念,卻不能不面對失敗,感情真實動人。但因左派文人群起攻伐,只陸續發表過其中片斷,全書逾四十年後(一九六六年)才獲准出版。寫於一九二五年的《魔鬼行徑》(Djavolijada)、《致命的蛋》(Rokovye jaica)、《齊齊科夫奇遇記》(Rocho ždenija Čičikova)和《狗心》(Sobačje serdce)開始以類似果戈里的怪誕筆法,勾勒畸形的官僚、荒謬的事件、貧窮的小人物、黑暗的社會。《致命的蛋》和《狗心》被視為最佳代表作,是對共黨制度與蘇聯社會的露骨嘲諷。
《致命的蛋》敘述動物學教授伯希科夫(Persikov)發現一種具有強大生長功能的紅外線,共黨黨員洛克(Rok俄文原意厄運)不顧伯希科夫教授反對,建議政府以此紅外線大量養雞。遂由洛克負責該計畫,向外國訂購雞蛋,卻因某單位疏失,洛克收到的是伯希科夫所需的鴕鳥蛋、蟒蛇蛋和鱷魚蛋,雞蛋則於稍後送至伯希科夫實驗室。數小時後,無數的鴕鳥、蟒蛇和鱷魚到處行走,吞噬了洛克的妻子,瘋狂攻擊居民,然後朝向莫斯科前進。政府出動軍隊、警力和飛機,都無法制服牠們,引起全國恐慌。此時,八月盛暑,強大寒流突然來襲,鴕鳥、蟒蛇和鱷魚立刻停止活動,進入冬眠狀態,才被全數殲滅。《狗心》敘述醫學教授菲利普收容莫斯科街頭一隻瀕死的流浪狗,他將一名流氓的腦下垂體移植到狗身上,成了狗心人腦的變形人。這個「人」竟酗酒、偷竊、穢言、忘恩負義……種種猖狂惡行迫使醫生必須在狗心的善良、忠誠等美好特質未完全消失前再度施行手術,將狗腦移回狗身,讓牠還原。布爾加科夫筆下,這狗心狗腦顯然遠比人心人腦更有正面價值。當時蘇聯政府積極鼓吹新時代,建設新社會,創造新人類,器官移植是熱門的科學研究之一。布爾加科夫書中的諷刺卻遭忌諱,共黨內部贊成與反對雙方幾度爭論,決定禁止刊用。一九六八年,該小說在西歐首度發行。八○年代中期戈巴契夫推動開放,莫斯科劇院將其改編為戲劇,一九八七年首演,轟動一時。
一九二六年起,十餘年間,布爾加科夫寫了約三十部劇本,多是諷刺喜劇,刻畫悲哀的命運、醜惡的人性、不切實際的夢想、人與社會的衝突。因對共產意識和制度多所批判,大部分不准演出。如《土爾賓一家的歲月》(Dni Turbinych,1926)改編自小說《白軍》,經一再修改,強調了布爾雪維克的最後勝利,才終於搬上舞台。《左伊卡的住屋》(Zojkina kvartira,1929)譯為法文,在巴黎首演。《紫色島》(Bagrovyj ostrov,1927)演出數場後即遭禁演;《逃亡》(Beg,1928)首演日前一天取消許可。種種打壓使布爾加科夫的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向高爾基求助,甚至上書史達林。一九三○年四月,派任莫斯科藝術劇院助理導演。一九三○至三六年間,先後演出他改編果戈里的《死靈魂》、描寫普希金之死的《最後一天》(Poslednije dni)、寫莫里哀的《偽善者的奴隸》(Kabala svjatoš)。一九三六年轉職波修瓦劇院,三八年改編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一九四一年該劇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演出。
布爾加科夫逝世於一九四○年,病榻上完成長篇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Master i Margarita, 1929-1940)。此作費時近十二年,可能因預料無法通過審查,布爾加科夫決定為未來的讀者而寫,因此下筆銳利,更大胆、更深刻地嘲弄了當時的莫斯科市儈,並更直接地闡述了自己的哲學、宗教和道德觀。
《大師與瑪格麗特》寫魔鬼化身外國教授沃藍德來到一九三○年代的莫斯科,發生種種稀奇怪異的事件。內容寓意類似《浮士徳》,魔幻筆法可與《魔戒》或《哈利波特》產生聯想。沃藍德遊走三○年代的莫斯科現實時空,他能預知未來,向飛揚跋扈的莫斯科文協主席白遼士和年輕詩人伊凡證明,上帝是存在的。魔鬼原是「惡」的代表,卻一再譴責惡,幫助善良的人。正如列於小說首頁的歌德《浮士德》之言:「我屬於力的一部分,它總想作惡,卻又總施善於人」,布爾加科夫強調了自己對善的信念。因為是魔鬼──惡之神,沃藍德又能遊走不同的歷史時空。他目睹比拉多審判耶穌,聽李斯特彈琴,同時在莫斯科表演魔術,捉弄貪圖錢財俗物的人們。比拉多因為懦弱,背叛了正義和良知,釋放強盜,處死耶穌,從此一千多年以來,靈魂備受痛苦煎熬,不得平安。讀了大師的小說,比拉多才獲得寬恕和解脫。布爾加科夫以此重申對俄羅斯傳統宗教信仰的堅持,在積極宣揚無神論的蘇聯時代,意義特別深長。此外,沃藍德遊走於超自然時空,使瑪格麗特回復青春,將大師從精神病院救出,讓大師與瑪格麗特的靈魂飛越麻雀山,飛向永遠的安寧。布爾加科夫否定世俗,嚮往永恆,對愛恨、善惡、生死的思考十分深刻,讀者需要沉澱回味。回春術及精神病院的描述則再現布爾加科夫的醫學素養:回春術與今日普遍流行的美容醫療有些相似之處,精神病院醫師的病症診斷和用藥,更需專業背景。此外,布爾加科夫書寫人物心境與風景,用筆絢麗,書中處處現實與神話交融的藝術手法,也值得仔細欣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布爾加科夫逝世二十六年,《大師與瑪格麗特》首次在俄國出版,立刻引起轟動。一九六七年一月再版,次年法文版問世,一九六九年譯為德文。布爾加科夫終於以「魔幻大師」之譽走上世界文壇。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