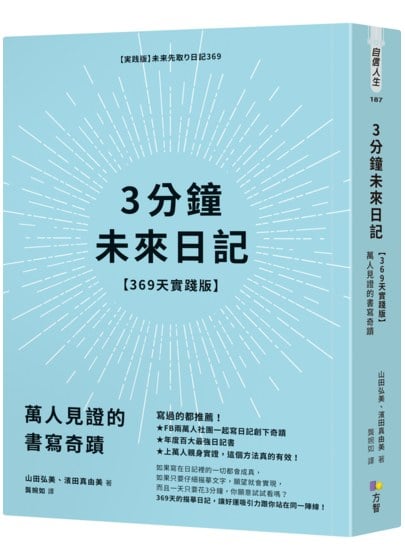內容簡介
★歐洲驚創1000,000冊銷售佳績!受歡迎與讀者推薦指數僅次於史迪格‧拉森!
★荷蘭家喻戶曉的文壇才女,值得愛書人追隨的懸疑驚悚小說家。
★這部小說讓人重新定義unputdownable,越警告越想一路看到底!荷蘭50萬讀者迅速買單,德國讀者緊跟在後崇拜嗜讀。
★王浩威、韓良憶、鄭華娟……看好推薦!
回憶可以殺人!
直到第九年的同學會,我才真正明白,
她的缺席,竟是我的救贖……
九年前,莎賓十五歲,她的兒時好友伊莎貝兒莫名失蹤,從此下落不明。莎賓也就此出現記憶缺口,怎麼樣也想不起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直到最近,報紙上的一則「同學會」公告,讓莎賓再度跌落記憶拼圖的漩渦,不斷想起伊莎貝兒,當年的片段畫面也開始無預警自腦際閃示不停,讓她既痛苦又像上癮般地回想著──
進入中學後,伊莎貝兒漸漸與她形同陌路,甚至聯合其他女生霸凌她。
那天,莎賓遠遠跟在伊莎貝兒身後,看著她跟另一個男人走進黑暗沙丘森林……
失落的記憶與夢中那個模糊的身影,會不會竟是一把雙面刃,既是莎賓努力尋回自我的最佳戰友,也可能是當下平靜生活的背叛者?!
荷蘭犯罪小說天后首部登台佳作,精彩描寫犧牲的可怕,深度刻畫記憶與友誼的本質。
當失落的記憶一點一滴浮現,真實的世界卻一片片崩解……
廣受國際讚譽的青春心理懸疑佳作
‧這部描述動人的心理驚悚作品,引爆一股出乎意料的吸引力。──明鏡週刊(Der Spiegel)
‧讓人無法放手,驚心動魄。──柯夢波丹(Cosmopolitan)
‧正如所有優秀的驚悚小說一般,此書令人享受之處不在於追索凶手是誰,而在於主人翁生命中的點點滴滴,以及暗藏其中的焦慮……她筆下刻不容緩的氛圍貫穿全書。范德魯格在荷蘭家喻戶曉,也是一位值得追隨的驚悚小說作家。」──年代雜誌(Age)
‧寫得好!范德魯格的確把這宗謀殺案描寫得十分精采!──紐西蘭‧週末先鋒報(Weekend Herald)
‧莎賓是個引人共鳴的角色,她的苦難……使讀者久久無法自己。荷蘭犯罪小說天后范德魯格的作品,忠實細述受到迫害及其可能後果的恐怖。」──澳洲‧阿德雷市廣告人報(Adelaide Advertiser)
‧令人驚豔的驚悚小說,餘味猶存。──婦女時代(Woman’s Day)
‧在作者所營造出的緊張氛圍中,真相緩慢而令人毛骨悚然的聚焦。──週日電訊報(Sunday Telegraph)
‧荷蘭知名作家引人入迷的驚悚佳作,出乎意料的高潮。──甜心雜誌(Cherrie Magazine)
‧誠摯推薦給神經夠強、心臟夠棒的犯罪小說迷。──《Glamour》雜誌
‧安靜的心理小說,關於一個女孩、一樁謀殺,以及校園邊緣人的悲楚。──《Woman》雜誌
‧一窺受盡折磨的心靈,《同學會的缺席者》最後的高潮令人極度不安,妮基‧法藍齊和米涅‧渥特絲的讀者會非常喜愛!──暢銷書《Skin and Bone》作者Kathryn Fox
國際讀者好評不斷
‧這部小說超越了一般小說只在追查凶手是誰,而是更深入探討記憶和友誼的本質。它的魅力在於,你會不由自主一直讀下去,被書中的角色和轉折所吸引,一心等待著結局揭曉……然而,結局令人不安! ──英國讀者‧琪特
‧在小說情節的每個轉折處,都出現新的可能性和更多的疑問。你會禁不住同情莎賓,也想跟她一起找出九年前事發當天的真相。讀到結局,才恍然領會這是一部布局精巧、可讀性高的小說。──英國讀者‧費雪
‧身為推理迷的大讚嘆:《同學會的缺席者》是截至目前我所讀過的精彩作品之一,你絕對無力也不想將它放下!──德國讀者‧布勞依芃
‧結局令人吃驚的青春小說。我對這本書傾心不已,堪稱一流創作!除了結尾讓我震驚,最有趣的是,我發現自己也跟著書中情節回憶過往……這書的確值得推薦!──德國讀者‧柯奈莉亞
‧我超級喜歡這本小說!作者一路引人進入迷途,我一路追索真凶是誰。兼具娛樂效果且值得一讀。──德國讀者‧雷塞拉特
‧我自己在十幾歲的時候也是校園暴力的受害者,幸好沒有像書裡那麼慘。這不是典型恐怖小說或犯罪小說,但曾在求學時期因為某些同學跟大家格格不入,就以欺負、折磨他們為樂的人,都應該一讀。我特別佩服莎賓,雖然受那麼多苦,卻始終對伊莎貝兒和她的命運抱持同情,我覺得真的很了不起。──奧地利讀者‧書蟲
‧超好看!結局出人意料的精采好書。刻畫動人的人物、高潮迭起,多重情節張力交織出的好故事。期待能讀到作者更多作品。──奧地利讀者‧大都會植物
‧不全然是一本恐怖(驚悚)小說,但我覺得寫得很好,結尾很精采。我對主角很有共鳴。──奧地利讀者‧艾薇
作者介紹
希蒙娜‧范德魯格(Simone van der Vlugt)
2009(c)Merlijn Doomernik
1966年生於荷蘭。原為荷蘭深受好評的童書作家,後來轉型書寫驚悚小說。
《同學會的缺席者》是她最負盛名的成人小說,為NS Publieksprijs獎決選作品(年度最受大眾喜愛和評審欣賞的書籍評選獎項),從此以驚悚小說創作聞名國際。她說:
「我一直認為自己有本事可以寫驚悚小說。我從十八歲開始就為之著迷,當時的我貪戀地讀著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小說,也嘗試以此為寫作方向……我所有作品的共同之處在於,寫作時我彷彿親身經歷這些事件,藉由主角表達我的感受和思緒。也許有些人認為這麼做有其侷限之處,但我認為此舉最能保持角色的整體性及多樣化:也就是運用真實的生活體驗。
「寫作時,彷彿我就是書中的主角。當然並非全然如此,但從情節中可一窺與現實生活雷同之處。我不是莎賓,但我們都有共同點。本書中的犯罪案件甚至不是中心焦點,這一點對我很重要,因為就算讀者知道凶手是誰,故事的力量本身仍然需要具有足夠的吸引力,才能讓他們繼續讀下去。
「對我而言,角色仍然是最重要的元素。如同我所寫的童書一般,我最感興趣的是主角所經歷的旅程。你可以看到莎賓從一開始到結尾所經歷的發展,我希望讀者看到發生的事件如何改變、影響一個人。
「我的書裡沒有英雄,每個人都必須流下汗水。就許多方面而言,感覺上這好像是另一場初次登台。在荷蘭作家很容易被貼上標籤,『一日為童書作家,終身為童書作家』,人們不建議你嘗試改變,他們說:『這本書最後會淪落到垃圾桶裡,不然就是印刷數量很少。』然而對我而言,這是我必須做的事。我不想到了八十歲才後悔沒有嘗試過。而且,我也做好丟臉的心理準備,這對作家而言是很重要的特質。必須勇敢,必須勇於冒險。這本書並沒有只印少數幾本,我很高興當初固執己見。」
范德魯格的另外四部小說也在荷蘭獲得空前迴響,德國海恩出版社(Heyne)更一口氣買下她五本小說的出版權。目前,她與丈夫和兩個孩子住在荷蘭的阿克馬市。
譯者簡介
/ 陳靜妍
專職譯者,譯作包括《水泥中的金髮女子》《瀑布》《馬奎斯的一生》等。
規格
ISBN:9789861371283
頁數:320,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789861371283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