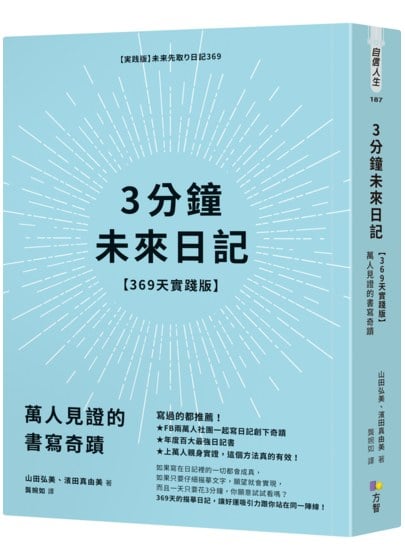內容簡介
宛如張愛玲,讓人愛到心痛,卻無法釋卷
家國萬里,關山如雪,亂世驚夢,半生繁華,她與他終究是情深緣淺,長恨如歌……
※華文地區青春愛情小說天后經典大作,原著翻拍電視劇引發旋風!
※作品長踞當當網熱搜風雲榜、百度搜搜風雲榜、暢銷書排行榜,讀者4.5顆星高度推薦!
我要給妳世間女子都仰望的幸福,我要將這天下都送到妳面前來。
慕容灃凝視她半晌,忽然在她鬢旁輕輕一吻,靜琬一時怔忡,竟沒有閃避。
他微笑望著她,說:「我可不是瘋了?才會這樣發狂一樣喜歡著妳。」
為了相救未婚夫許建彰,尹靜琬隻身前往承州,卻意外與裂土封疆的軍閥慕容澧互生傾慕之心。在許尹大婚之日前夕,慕容澧冒險深入敵境,只為帶靜琬離去。情之所至令她棄婚出走,心甘情願地隨他奔波輾轉於烽火之間。
然而兩情繾綣抵不過萬里江山,慕容澧與程家的政治聯姻終於迫她離家去國。此去經年,重來相見,戎馬半生換得天下在握,卻痛失一生摯愛……
這是一部連文字都跟著哭泣的愛情故事,悲情小天后匪我思存傾情演繹的這部生死之戀,以一種最淒美的方式詮釋了:愛情,就是至死不渝……
通路、媒體、三百萬讀者的全面捧心推薦匪我思存!
匪我思存是我迄今爲止見過最具文學性的愛情小說作家。她的文字很容易流行,卻很難被模仿。那種雅致而流暢的字句彷彿渾然天成,而自由肆意的想像力則爲她的字句增加了戲劇性。文學與暢銷的結合點被她拿捏得很準,單這一點,她就是個天才。
——《知音》雜誌主編 夏鍾
沒有商戰的爾虞我詐,沒有深宮的勾心鬥角,天后級的文字水準。—中國第一大網路書店「當當網」
把「人間無奈,有情皆虐」的感受寫得入木三分,當代佼佼者非匪我思存莫屬!
—讀者‧Plumeria
匪我思存的故事,讓人恨不得立即抛下繁冗瑣事,飛奔去談一場戀愛。這種情懷彌足珍貴,超越身分與權勢,可遇不可求。—讀者‧青青
匪我思存的書永遠都出人意料,彷彿隨著她的文字,就能走過當年的青蔥歲月,走過當年的似水年華。—讀者‧飛翔時光
【名人推薦】
● 這是一本很有味道的悲書。匪我思存厲害的地方是描述細節的功力,種種細節帶領讀者進入小說的情境,彷彿真的聽到、看到、摸到那時代……《來不及說我愛你》會讓人想再看第二次,不是為了再哭一次,而是為了再次回味她文字的魅力。──作家 倪采青
● 這部民國小說匪大寫得通透哀豔,似有張愛玲般窺破紅塵,寫盡世情之風。尹靜琬和慕容灃浪漫邂逅的旖旎刻畫,戰爭局勢的客觀分析,以及人物的描繪都讓人愛到心痛……──讀者 小蟬
● 匪大的作品中最喜歡的女主就是尹靜琬,欣賞她、憐惜她,於是終究還是感傷的,被匪大賺取了無數的眼淚…… ──讀者 艾莉
● 她的文筆好,思路更是廣闊。初看,只覺得頗有張恨水的文風,但看到後面,又覺得與時下盛行的穿越小說相比毫不遜色。──讀者 弗隆
● 匪大對我們內心最為脆弱的那部分瞭若指掌,她的筆觸永遠都能深入悲痛的神經,讓我們為之一痛。大愛這本書呀!──讀者 小倚
作者介紹
悲情天后第一人 匪我思存
對於在網路上追小說的人來說,「匪我思存」是個重量級且神秘的名字,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的她,筆耕至勤,短短數年已出版十八部小說,累積銷量已經獲得千萬讀者的肯定,也是網路書店單本三百萬銷售紀錄保持人。她卻仍堅守原本的會計工作,將現實與小說世界的一切分得很清楚。她是這樣說的:「無關乎名利,我只是喜歡徜徉在作品裡的純粹,一如讀者。」
許多人認為網路小說良莠不齊,產量多往往與劣質畫上等號,但匪我思存是個例外。匪我的人物飽滿,情緒及場景的描摹細緻,牽引力十足,不管連載多久,總是能讓網友追著讀完。文中場景器物,一釵一鈿,一裙一袂都詳加描摹,其仔細的程度,每當她的小說要改編的電視劇時,都會讓道具人員咬牙切齒!
筆名取自詩經的「匪我思存」,其文字也如詩經一般優雅,有著渾然天成的耽美古典憂鬱,令人越讀越捧心、越神傷。無怪乎有讀者會說:「匪我思存的故事,會讓人恨不得立即抛下繁冗瑣事,飛奔去談一場戀愛。這種情懷彌足珍貴,超越身分與權勢,可遇不可求。」
作者官網: http://blog.sina.com.cn/fwsc
規格
ISBN:9789861334059
頁數:264,中西翻:1,開本:1,裝訂:1,isbn:9789861334059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