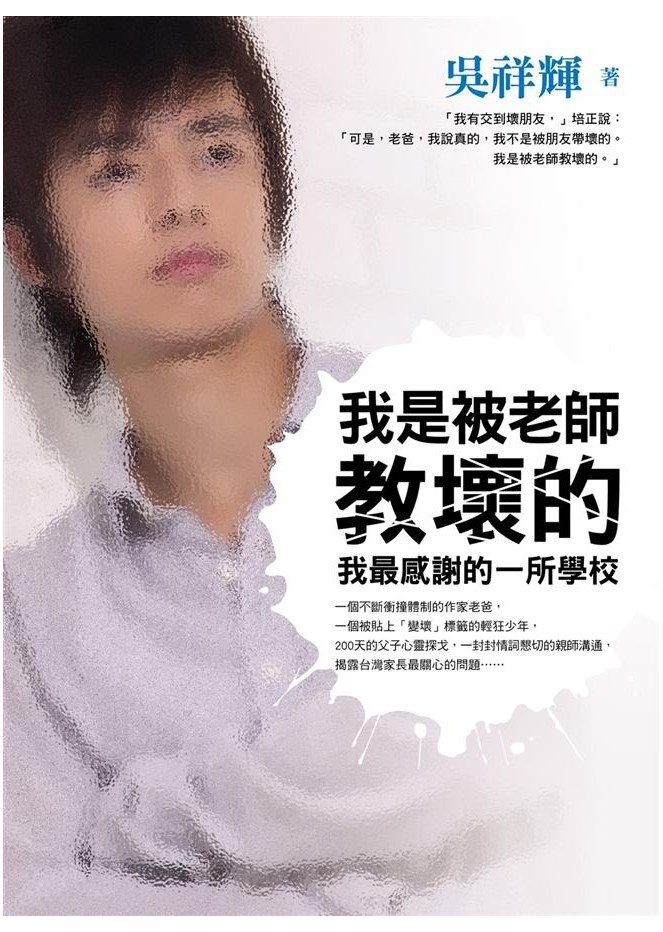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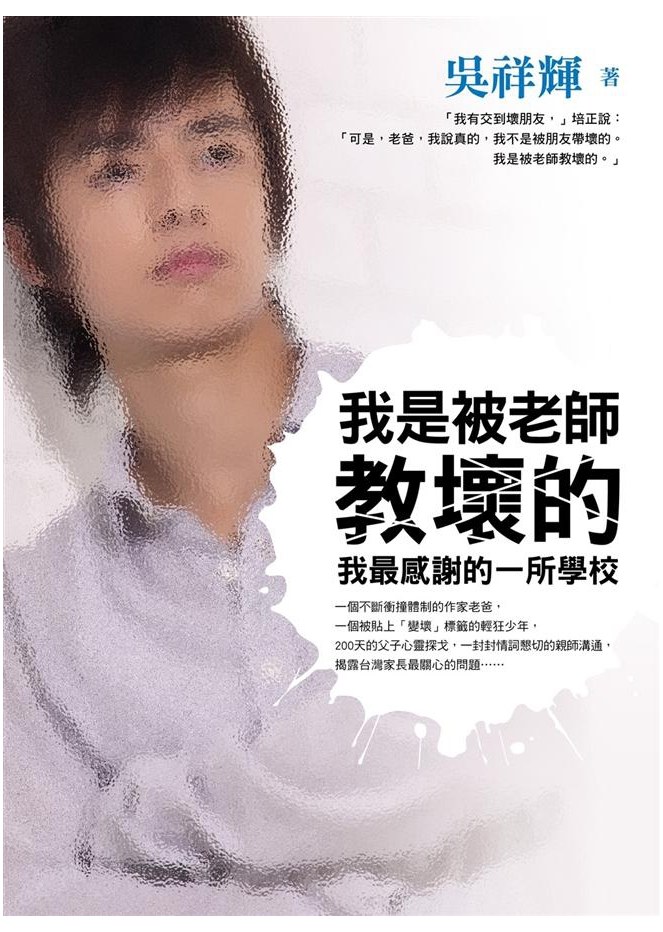
相關專欄
內容簡介
★2009金石堂知識學習類Top20
2008
博客來親子共享類Top30
金石堂心靈健康類Top50
「我有交到壞朋友。」培正說:「可是,老爸,我真的告訴你,我不是被朋友帶壞的。我是被老師教壞的。」
一個不斷衝撞體制的作家老爸,一個被貼上「變壞」標籤的輕狂少年,
200天的父子心靈探戈,一封封情詞懇切的親師溝通,
揭露台灣家長最關心的問題……
翻閱一個十四歲少年的「兒童檔案」。想從「歷史紀錄」中,激盪出幫助他的靈感。
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他的表現都是一等一。
檔案中沒有他五年級以後的紀錄。他同期的笑容和檔案,一起消失。
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 * *
學務主任突擊檢查一○八教室,搜查違禁品。項鍊、耳環、化妝品、PDA、MP3……都是「違禁品」。但大家都知道,「信」才是真正的搜查的第一目標物。
她寫給培正的信被搜出。學務主任不懷好意地笑看培正,一副人贓俱獲的得意之情……
信封被打開的剎那,暴怒聲驚動四座:「你敢看我的信。那是我的隱私!」培正怒拍桌面:「有種你就拆開來看!」
* * *
快快樂樂、免於恐懼地受教育,是孩子的天賦人權。
孩子轉入新學校後,看著他臉上的暴戾之氣已逐漸消失,線條變得柔和,以為他能在這裡平順度過轉性的日子。沒想到,他的傷痕已沉,夢魘未除。
我決定要放掉所有預定的行程,陪他走一段不知會有多長的「心靈復健」之路。
我感到慶幸。有這樣的學校和您這樣的老師,孩子也許「有救」了。
作者介紹
培正眼中的作家老爸
他是我爸爸,是個狠角色,
在社會上佩服他的人太多了。
他有他自己明確的目標,
無論是以前在選舉在政治,或者是現在投入寫作,
只要是他做的事情,一定都會全力以赴。
我作為他的兒子,也一樣的佩服他。
在台灣你可能找不到第二個像他一樣的人了,
非常的宇宙不同,他也是個好爸爸,
對老婆好,對三個兒子也都很好;
努力工作賺錢養家,真的是個好丈夫。
好作家好政治家好丈夫好爸爸,
你說,台灣找不找得到第二個他呢?
實際生活裡的作家老爸
吳祥輝,1954年生,台灣宜蘭人。
七○年代以《拒絕聯考的小子》一書勇敢衝撞台灣的教育體制,轟動全台。
爾後進入平面媒體,從事寫作,並參與黨外運動和選舉公關等事務,但仍堅持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的信念。
近年勤走異鄉,以國際觀點理性觀察,書寫完成《芬蘭驚艷》《驚歎愛爾蘭》二書,再登創作高峰,獲邀相關主題講座近二○○場,成為新一代的教育關懷者。
《我是被老師教壞的》是他以切身經驗,分享他如何因材施教「陪伴」兒子成長的故事。除了道出扭曲的多元價值包裹著升學主義的一元思想,如何扼殺著教育食物鏈中的最弱勢——青少年,更與所有父母分享全台灣最「適情適性」的學校,期盼全民共創台灣教育新典範。
u相關講座預約請洽:brianwu211@yahoo.com.tw
本書所述為真人實事,但為顧及書中人士之隱私,除主人翁外,所有人名均用假名呈現。
規格
ISBN:9789861332529
頁數:240,開本:1,裝訂:1,isbn:9789861332529
試閱
<作者序>
「我鼓勵你把這些故事寫出來。我會幫助你。你想知道學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說給你聽。」十四歲的少年這樣告訴他的作家父親:「讓那些沒有信心,不快樂的小孩知道,有個作家在關心他們。對他們會是很大的鼓勵。」
他的動詞和心願都很特別。在他的「鼓勵」和「幫助」下,這本書終於完成。
他想激勵同儕的赤子之心,但願我能多少替他實現一點點。
<序篇>
親愛的黛依老師:
翻閱一個十四歲少年的「兒童檔案」。想從「歷史紀錄」中,激盪出幫助他的靈感。
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他的表現都是一等一。
「個性積極,態度落落大方,學習興趣濃厚,熱心助人。」
「活潑好動,學習認真,對於疑問能主動提出,對自己的缺點也能積極修正。」
「天資聰穎,領導力強,數學能力尤強。」
「上課態度積極進取,學習慾望強,天資聰穎,個性活潑大方,頗具領導力。」
這都是老師的書面評語。完全保存原樣,一字未易。每年級只選一學期,是避免相似性的資訊過度重複而已。
相對應的是各科成績。德智體群美五育總評,四個學期獲得二十個最高級評等(90~100分)。大滿貫。
每年分科不一,評等方式不盡相同。四個學期共有五十五個分科評等欄位。他獲得五十個最高級和兩個次高級(80~90分)評等。
還有十七張校長所發的獎狀。像「整體表現優異」「拾金不昧」「數學科期中評量表現優異」「數學科期末評量表現優異」等等。
檔案中還有紅包裝著的獎學金五袋。「作文第一名獎學金二百元」「作文第二名獎學金一百五十元」「徵文比賽佳作獎學金一百元」等。百元鈔票和五十元硬幣都還在紅包袋裡。逐次檢定合格的證書和專業競賽的獎狀更有二十張之多。像「小泳士證書」「心算三段檢定合格」「全國珠算暨數學比賽珠算組第三名」「全國珠算暨數學比賽數學組第三名」等。他還彈得一手鋼琴。這些都是他在校園外的學習成績。
他「玩」心很重。每天快快樂樂去上學,回到家的對話起頭都是:
「今天好不好玩?」「好玩!」
「今天快不快樂?」「快樂!很快樂!」
從小他就被父母教導:「笑咪咪!看到人就要笑咪咪!跟人講話,眼睛要放電!笑咪咪!要放電喔!」他都說好,也都能做到。
他超級愛笑。聽句話或看段影片,可以笑到像個神經病,久久不能停。問他笑夠了嗎?拜託停一下。他總是邊笑邊答:「我也不想繼續笑。可是凍未條。太好笑了。」
他喜歡唱歌,常常跟著兩個哥哥學唱西洋歌曲,日本歌、韓國歌、香港歌。不過,他唱起來都差不多,很難聽出是在唱哪一國的。每首歌都唱得像唸經,是共同的特色。
「弟弟,我們家有死人嗎?」二哥這樣問他。他就開始哈哈笑。
「弟弟,我覺得你還是唱國語的就好。」大哥再補上一腳。
他已經笑到滾在地上。真的有這麼好笑嗎?可以笑成這樣子?實在太好笑。
檔案中沒有他五年級以後的紀錄。他同期的笑容和檔案,一起消失。
這會是一個什麼故事?
祥輝敬上
第一部
1
這個十四歲又五個月大的少年,向我回憶他五六七年級的往事。事隔三兩年,他已能用輕鬆的心情描述。我摘要他的「口述歷史」:
「同學不乖,叫去屋頂罰曬太陽。不必上課,一次一小時。連下課時間。」
「發考卷邊走邊叫同學名字,同學要馬上站到他前面。成績好的,他把考卷給他。成績差的,他就不給。直接把考卷扔在地上。叫學生自己撿。」
「還有更過分的,我們教室在三樓,他會走到走廊,把考卷或連絡簿丟到一樓。發完考卷或連絡簿,他才說:沒有發到的,自己到樓下撿。」
「全班太吵,被罰跪著考試。有家長向學校反應,老師知道後,對全班說:『是你們自己要跪著寫的。我又沒叫你們跪?你們怎麼怪到老師頭上?』」
他說的是五年級的男性班導師。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對孩子說話的語氣很直接:「排好!」「站好!」「不要講話!」「聽到了沒有!」。
非常明顯地,他的功課一落千丈,朋友激增。敢嗆老師的,被老師憎厭的同學都成為他的「好朋友」。他們那夥孩子如此稱呼自己的班導師:「屁」一個。「那個屁啊!」
現在他已經會苦笑地說:
「他是個敢做不敢當、會撒謊、喜歡侮辱學生的老師。」
「現在我學會了。自己不乖,不要把錯怪到別人身上。」
五年級下學期,家裡替他轉學,遠離不再讓他快樂的學校。新學校接手的林老師兢兢業業,卻得面對一個「總是抱怨和遷怒」的孩子。沒想到,老師也會成為上一位老師的受害者。
真正的惡夢從七年級開始。故事發生在宜蘭一所著名的私立住宿學校。事隔一年,遷地為良後,他已能坦然面對。
「我問他,我戴個戒指也不行?事情就這麼大?」他頂撞學務處江主任,學務處當年稱為訓導處。
「誰叫你是一○八的。」主任說。
「一○八是怎樣啦?就不是人嗎?」他直接嗆回去。
這私立學校按入學考試成績分班。雖然,對外都說常態分班,但是,校長、老師和同學,都知道真相。私下裡也互不隱瞞。數資班、英資班和全資班都有。
「我們學校現在很多人讀,寧缺勿濫。你們一○八的幾個問題學生,給我小心點。我會天天盯著你們,找到機會就會讓你們走。」
「幹你娘!」十三歲的孩子當場發飆。結局是小過兩支。這是「念在初犯,從輕發落。」按校規,侮辱師長記大過一支。
這樣的反應很不成熟。但是,面對這種可惡的師長,十三歲的孩子還能有什麼成熟的反應?他媽媽說的話最經典:「兒子,你這樣反應,讓我很擔心。但是,你如果不反應,媽媽會很傷心。可以讓我不要擔心、也不要傷心嗎?」
我請他把過去七年學生生活中的「惡師」,列個「排行榜」。他說只有兩個。連五年級的班導他都淡淡地略過。這位學務處江主任被他評為首惡;排名第二的惡師叫禿頭,他總管教室和宿舍之外的地盤。
他舉一個和他同夥的崔姓學生,在餐廳遇到禿頭的例子。
「安靜,不要講話,不要走動。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禿頭說,「在餐廳我最大。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就照著做。」
「需要這麼臭屁嗎?」崔同學小聲說,卻被禿頭聽到。
「站起來。」禿頭咆哮著,「你不服氣嗎?你想怎樣?」
崔同學拿起餐盤,往禿頭砸過去。餐盤上的食物散落滿地。記大過一支。
當然,這都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早已冰凍三尺。師生之間互相憎惡已久。
現在,他說著說著,毫無怨氣或怒氣。神態和語調都很輕鬆。
「學校大,又漂亮,制服也很好看。籃球場很多,籃框都是新的。教室開冷氣,桌椅很新。他們給學生最好的讀書環境。」
「可是,我們的心裡什麼也沒得到。」
「高段班有錯,大事可以變小事。高段班當然沒有小事。低段班小事絕對是大事。他們看人處理事情。」高段班是成績好的班。低段班是成績差的。成績歧視是這個學校的體制運作本質。
「有別班的老師這樣跟全班說,沒辦法,既然在這學校教書,就要遵照學校的規定。希望大家能夠配合老師,給老師一個面子,賞老師一口飯吃。」他還補充說,這種老師會獲得同學認同,至少這種老師很誠實。
他把「寧缺勿濫」「表裡不一」擺在一起,烙下這個學校在他心靈的深刻印記。
七年級沒讀完,他又被家長轉學。轉到您們手上。他是我最小的兒子,培正。
感謝您們,讓他擁有一個不錯的新開始。
2
感謝秋假前您打來的那通電話。
「培正和同學起衝突。打女生。」
聽到這個消息,我是九分震驚,一分納悶。因為,自從他野掉之後,我就對他立下一個停損點:絕對不能打女生。因為,小女生絕不會找小男生「釘孤支」。他頂撞,辱罵老師被記過,我表面上訓誨他,心裡其實是另外一回事。
老師為什麼不能「頂撞」?老師一個成年人,為什麼沒有能力承受一個孩子「頂撞」?老師為什麼會被「頂撞」?我看過「師必自侮,而後生侮之」的往事,比學生找老師碴的多太多。
高雅地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里斯多德)最實在地說:老師的言教或身教,不是用來磨練孩子的「忍耐程度」。老師必須忍耐孩子的不成熟。孩子卻沒有忍受老師的義務。
更根本地說,教育者和受教者是對等的合作角色。當學生「頂撞老師」要被記過,老師「侮辱學生」又該受什麼處分?「頂撞」這個封建詞,早該被從校園中揪出來「處死」。
台灣的教育一直是「賣方市場」,而非「買方市場」。用社會文明進化,消費者權益不再任由供應方宰制的角度來看,學校是台灣最落伍的地方。有的學校很可怕,連家長都直接介入校務。家長成為教育伙伴是種進步。但是,買方指的不是家長,而是孩子。
家長不懂法理,以為自己是「付錢的大爺大娘」。法理真的不是這樣。兒童和青少年都有被教養的「權利」。「付錢」是家長的義務。不履行就是「棄養」或「無力扶養」。看到許多家長到學校裡,把義務當成權利享。這種猖狂是由於學校只有圍牆,沒有肩膀。台灣教育真是嗚呼哀哉,尚饗。
如果培正是和男生打架,又是另一回事。男孩子打架當然該慎重處置。可是,打架記過的「法理」是什麼?「禁止使用暴力」?很好。偏偏學校裡最經常訴諸「肢體暴力」和「語言暴力」的都是師長。
培正打女生!我的天啊!!我立刻辭別正在一起談事情的朋友,趕到學校。您們還聚集在教室的某個角落「處理善後」。兩造隔桌對座,身旁各圍著一些「支持者」。所有的人都默默無語。您帶著大家,好似正在「懺悔中」。
我先請問坐在培正對面的女孩叫什麼名字。「安琦。」她說。
「安琦,可以告訴我衝突的經過嗎?」
她個子很高,平靜地說:「今天我把時空錯置了。」就只有說這麼一句話而已。我馬上就喜歡上這個第一次見面的女孩子。小小年紀竟然有這種高段的敘事能力。只用一句話,就同時深刻地表達「自我檢視」和準確的「情境描述」。真恭喜她和她的父母。
接著,肇事者和您讓我了解事件原委:
您在上課。全班亂哄哄的。您拜託了幾次「安靜一下」「不要講話喔」,沒人理妳。
培正看不下去,對全班大吼:不要講話啦!
安琦一聽,就對他嗆聲:「你自己還不是愛講話,憑什麼講人家!」
培正一怒之下,衝過去,用手臂鎖住安琦的脖子。然後,被同學們拉開。
以前剛轉過來時,培正還是老樣子,上課愛講話。後來,就漸漸比較安靜聽課。當天,他沒講話。安琦用過去的印象嗆他,他才當下抓狂。安琦說「時空錯置」,我想是這個意思。
培正轉入之前,是個已經被「激怒」的孩子。就像我們身上有什麼地方受傷,絕對禁不起別人碰。別人一靠近「傷口」,就會有防備的本能性反應。
幾個孩子替培正說話:「培正是為了幫老師。」
唉,又是老故事。老掉牙的「人性故事」。每次他爆發衝突,朋友就越交越多。贏得某些男生友誼,也贏來某些女生的「愛慕」。這當然不是他引爆衝突的本意,但卻會獲得「正當性」和「正義感」的鼓舞。
3
我來插播一段自己的故事,也許有助於您了解培正這個孩子。
話說當年,蔣介石總統去世。當時,我正在當兵。躬逢其會被徵召到北軍團「軍歌大隊」。我們的唯一任務是上華視的「軍歌大賽」唱歌。最主要的曲目是「蔣公紀念歌」。不只一首。
「總統蔣公,您是自由的燈塔,民族的救星。您是世界的偉人。」「蔣公!蔣公!您不朽的精神,永遠照亮我們,反攻必勝,建國必成。」諸如此類。大抵如此。
對了, 蔣公前面還必須像這樣空一格。以示超乎神祇的尊崇。對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觀世音菩薩或媽祖就都不必如此。那年代的學術界,和教育界真是夠受的。教育原是「天使之吻」。但在獨裁的年代,卻是「獨裁之鞭」。教育的最優先目的是貫徹統治者的意志。從業人員淪為「洗腦工具」而自得其樂。
「軍歌大隊」是個臨時編組,約有四十個服義務役的充員兵,成員來自北軍團各單位。不必出操,不必站衛兵。唯一的工作就是唱歌。最麻煩的是吃飯。因為,練歌時,四個聲部分部帶開,可以偷溜班。兵兵相護,不會出事。吃飯時,全員要到齊點名。
一位藝工隊的上尉擔任我們的直屬長官。練歌時,甚至中間休息,只要有人說話,他就對全體發飆。
他又飆了,命令全隊到連集合場集合,要罰跑軍團大操場。軍團操場有多大?沒量過。您就當作沒見過的大。想像可以集結數萬大軍、坦克車和大炮。
烈日當空,隊友們邊走邊耳語串連:
「等一下大家都不要跑。」眾人紛紛附和。
整隊完畢。
「部隊──向右轉!」
一聲令下,全隊向右轉。
「跑步──走!」
部隊動也沒動。
他再喊一次:「跑步──走!」
部隊還是不動如山!
氣氛僵住緊繃。我心中的感覺是:帶種。我喜歡。
沒想到,薑是老的辣。
口令突然換成:
「排頭四位!跑步──走!」
就這樣,排頭四個高個子跑出去,被個個擊破。
四個接著四個,等全隊跑光,現場只剩下一個人,直挺挺,孤伶伶地站著。
那個人就是我。
結局是這樣的:
1全隊罰跑軍團操場,改成只跑連集合場。
2我被理光頭。關禁閉室一週。
我不知道自己將面臨的後果嗎?當然知道。我只是「重價值」勝於「重後果」。
當時年輕的心,其實很單純:
「大家說好不跑的。這是團隊共識。要臨陣脫逃是你們的事。我說到做到。信守承諾。」
這是「個人英雄主義」嗎?英雄的誕生都源於捍衛團隊的榮譽。我只是在捍衛「自己在團隊中的榮譽」而已。
我在禁閉室天天唱歌。挑水肥澆菜時,都仍然覺得比任何隊友都快樂。我高興唱什麼就唱什麼。他們只能唱規定的。我不能去看他們。他們之中的幾個人,卻會偷偷摸摸,趁機偷渡稀有物資給我。
時到今天,我知道「價值堅持」不一定「價值正確」。但是,習慣於「價值堅持」,終會琢磨出一個「追求價值」勝於「追逐價格」的人。
培正似乎還沒有「堅持價值」的想法。但他基於「義憤」,卻是真的。接著,「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才讓憤怒脫韁而出。
您給培正的處罰是:「停學一天」。
我真的沒想到,在台灣的校園,竟然有另一種世界。您在「宣判」的那一刻,像個內斂公正的法官。沒有那種「在家自學一天」,「在家自習一天」的偽善。您的聲調傳達出,您很不忍心地,判了培正一天的「酷刑」。
受教育是孩子的權利。快快樂樂,免於恐懼地受教育,是孩子的天賦人權。以剝奪孩子一天的「受教權」做為懲罰,是教育思想落實台灣的革命性改變。
「安琦事件」讓我高度驚覺。孩子轉入後,看著他臉上的暴戾之氣,已逐漸消失,線條變得柔和。以為他能在新學校平順度過轉性的日子。沒想到,他的傷痕已沉,夢靨未除。
我決定要放掉所有預定的行程。陪他走一段不知會有多長的「心靈復健」之路。
我感到慶幸。有這樣的學校和您這樣的老師,孩子也許「有救」了。
4
「這是我為你轉的最後一個學校。」
從學校帶培正回家「停學」後,我讓他知道,他和我共同面臨一個既殘酷、又有希望的事實。他必須認明清楚。用不同於過去的心,珍惜這個特別的學校。
「這個學校如果你還待不下。台灣就沒有你能讀的學校。你只有出國一條路可走。」培正說他不想出國念書。
「從現在開始,我走到哪裡,你跟到哪裡。直到秋假結束。」他同意這個處置。他知道自己惹出大禍。媽媽笑笑地對他表達強烈不滿:「培正,請你幫媽媽一個忙,好不好?」他說好。「照鏡子的時候,幫媽媽看看鏡子裡面的人,是不是還是我兒子?拜託你囉。」
「安琦事件」很意外。因為,培正一直都很有「女生緣」。從小學開始,就不斷地有許多異性的「追求者」。滿抽屜不同筆跡的「情書」,證明他不是在吹牛。
「情書」是他的隱私。我們只能看信封。偶爾,不堪我的拜託,他才會網開一面,讓媽媽和我分享一二。「讓我了解你們小孩子怎麼告白嘛!拜託啦!」這是通常我博取同情的方式。「告白」是我聽他講電話時,學來的青少年流行用詞。
「情書」是隱私。「情話」是家事。孩子有講電話的充分自由。只是,房間裡不裝分機,要講就不要偷偷摸摸。全家人都公平,講電話誰都能聽。講大哥大?請便,自己付錢。
國中新生訓練才結束,培正就接到幾個女同學寫信給他,包括學姊。據他說,其中一個「品學兼優」。他是她的「初戀情人」。他們的交往被班導師發現,但沒有遭受處分。
「為什麼沒有被記過呢?」我問培正。這學校很特別。男女同校,男女同班,卻禁止男女同學私下交往。
「她跟我交往,功課也沒有變壞。還是好學生嘛。」培正說:「我的功課本來就很壞,也沒有變好。」
「可是,她很可憐。老師總找她麻煩。」他補充說。本來班上同學按程度不同,設有「標準分」。培正六十分就OK。她是八十分才可以免挨打。少一分打一下。
「妳成績很好嘛,」老師笑笑地損她,「提高到八十五分好了。不夠的罰雙倍。」
舉例來說,她考八十一分,過去是安全過關。現在少四分,加倍變成打八下。
每當她挨打時,許多同學看不下去。培正的幾個同夥都當場直接對老師嗆聲:
「老師妳太過分!」「不公平!」「不公平!」「老師,妳怎麼可以這樣!」甚至還有的小聲罵三字經。培正是「當事人」,也是「害人精」,不敢說什麼。
「看到她被打得那麼慘,我的心很痛。」培正說,「所以,我就跟她說,我們不要再交往了。」
「她喜歡你什麼?她不知道和男同學交往、寫信,會被記警告,甚至記過嗎?」媽媽問他。
「她知道我是怎樣的人。我一定不會讓她的信被學校看到。」培正說。
不守校規,終要出事。學務主任突擊檢查一○八教室,搜出違禁品。項鍊、手環、耳環、化妝品、手機、PDA、MP3、PS2都是「違禁品」。但,大家都知道,「信」才是真正搜查的第一目標物。
她寫給培正的信被搜出。學務主任不懷好意地笑看培正,一副人贓俱獲的得意之情。培正不斷地被激怒。
就在學務主任慢條斯里,信封即將被打開的剎那間,暴怒聲驚動四座:
「你敢看我的信。那是我的隱私!」培正咆哮著。他憤怒地重拍桌面:「有種你就拆開來看!」
按校規,這是「大過兩支」。「頂撞師長」一支。「男女不當交往」一支。培正在這學校念不滿一年,已經累計將近七支大過。沒被趕出學校,是一位好心的教官看不慣,暗中幫他「槓過」。故意不把記過單送出,放在抽屜存查了事。一直到重現微笑之後,他才主動對我全盤托出。
唉,我只知道他不適應,卻不曉得他的日子過得這般屈辱,榮譽感完全喪失。不過,他還是很勇敢。不會哭。不會訴苦。他還是我記憶深處中的那個孩子。
5
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獨具的「特殊」。
出生就是死亡的開始。孩子從脫離母體,就爬著,走著,跳著,跑著,奔向死亡之路。這麼短促的人生,誰能給他們耽誤?
櫃檯內站著兩位漂亮的小姐,語氣堅定得不像她們溫柔的氣質。
「不行。」「不行。」她們接著說。
「他還不到三歲,為什麼不行呢?」
「規定就是不行。很抱歉。不管是幾歲,只要是男生,就不能進浴室。」
媽媽牽著培正的小手。站在女子三溫暖的櫃檯前,正在為他「求情」。
「他這麼小,站在這裡,你們頭不伸出來看,根本看不到這裡有小孩。真的不能通融嗎?」
培正悄悄地鬆開抓緊媽媽的小手,默默地後退幾步,正好頂著牆邊。他轉過身,面壁而站,可愛的清式小辮子從後腦杓向外伸出。肥軟的小腿肚,委屈又無助。
媽媽放棄遊說,走到他身邊,探頭到牆壁前。培正嘟著嘴。
「寶貝,她們不讓你和媽媽一起洗。我們回家。」
培正當場放聲大哭,狂哭難止。此生第一次被無情地拒絕,自尊心受到屈辱。
幼幼班放學。媽媽脫下高跟鞋,走上木板地面的遊戲間接人。看不到培正。找來找去,他躲在遊戲洞裡。培正看到媽媽,沒有高興地迎向前。
「寶貝,要回家了。為什麼躲在這裡?」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他對著媽媽猛搖頭。「你不要過來。」
「為什麼不要過來呢?」
「放鞭炮。放鞭炮。」他紅著臉說。
「哪裡有人在放鞭炮呢?」媽媽聽不到鞭炮聲,也沒見到手拿鞭炮的人。
「放鞭炮。放鞭炮。妳不要過來。」
「沒有鞭炮啊?」媽媽鑽過去抱他起來。聞到臭味,碰碰尿布,發現是「培正拉肚子」。
聰明活潑的背後,培正害羞,怕出醜。
讀大班的早上。媽媽跟他配好衣服褲子,可愛大方。她打開家門。培正沒跟上,坐在樓梯口,一動也不動。
「為什麼不起來呢?要去學校囉。」
「我今天不能出門。」他憂憂地說。「不要上學,不要上學。」小手不斷地扯著腳上的襪子。
「為什麼不能出門呢?」
他說:「襪子沒有一樣高。」
襪子已經穿在腳上。大概匆忙間沒套齊整,媽媽就幫他把鞋子穿好。他的小手拉啊拉,扯呀扯,就是沒辦法讓兩邊的襪子一樣高。自力救濟不了,也不會求助。寧可不出門,不去學校。如此地好強,不願低頭。
幼稚園有節慶。媽媽幫他穿得彬彬得體,像個帥氣的小紳士。還打領結,連襪子都是精挑細選的黑襪子。小孩子的黑襪子很少。
他又不出門了。
「為什麼不上學呢?」
他才小手頻動,一直要把襪子扯掉。
「因為襪子太黑了。」
被這輛「培正號」重型機車撞到。誰能不昏倒?
這麼搞笑的孩子,進到嚴格管教的學校,不幸就從「襪子情結」開始。只是,沒人看到的小襪子變成眾目睽睽的頭髮。他對髮型重視的程度,媽媽這樣描述:「他的每一根頭髮都必須就定位。每天最少要照鏡子檢查二十遍。一根沒站好位置他都會發現。」
培正在學校裡,像個隨時會被逮到的犯罪者,到處躲。走在走廊怕遇上校長、主任、教官,和任何有權力記他過的人。頭髮太長,警告一支。在教室上課,隨時要擔心老師注意到他的頭髮太長。他養成新姿勢:頭永遠低低地,駝背走路,不敢跟人正面而視。
「培正,頭髮太長。要去剪。」連校長都認識他,總會有遇上的時候。
「謝謝校長,我知道。」這是他一貫打混的方式。只是應付。
「吳培正,上禮拜就叫你去剪頭髮,為什麼還不剪?」主任訓他。學校就那麼大,誰能保證哪個師長不會再次撞見他。
「主任,對不起,我忘記了。我會去剪,您放心。」這種言不由衷、自欺欺人的真相還能隱瞞多久。
培正被帶到學務處,主任手拿一把小剪刀。和他相同命運的還有一個個子很小、他不認識的學生。
「要我替你剪嗎?我替你剪,就必須記你過。還是你要自己剪,我剪刀借你。」那孩子不敢吭聲。
「我剪警告一支。你自己剪這次就原諒你。」
主任作勢要剪孩子的頭髮。他退後閃開。
「你不想要我剪,就不要留長髮嘛。還是要我叫教官帶你去外面剪?」主任大發慈悲地說:「我剪比較不好看,不記你。教官帶你去外面剪,才記你警告。」
那孩子就是不想被剪,又不知道該怎麼辦。流下眼淚,甚是可憐。主任再走近,按住他的肩膀,小剪刀拿到他頭上。
還在一旁靜待發落的培正,居然「正義感的老毛病」又發作。
「你會剪頭髮嗎?你憑什麼剪他頭髮!我就不相信你敢剪!」他又嗆主任。
主任竟然真的不敢剪。叫來教官,把他們帶去校外的理髮廳。他自己被記一支警告,也連累那孩子一支。
剪就剪,「隨便啦」。雖然很醜,「沒關係」,再留就有。一支警告「又不會死」。括號中的三個詞句,他越來越常掛在嘴邊。
上課喝飲料,被記警告一支。「又不會死。」
上課吃東西,被記警告一支。「隨便啦。」
穿耳洞,被記警告一支。「沒關係。」
上課睡覺,被記小過一支。「反正警告很多,加起來比一支小過多,沒差。」
週末回到家,連過去會做的家事都不想做。
「水槽裡的碗很多。」媽媽說。
「沒關係,不洗又不會死。」
「老師又打電話來家裡。」我提醒他。
「你就隨便她講嘛。她還能講什麼?想講就給她講,隨便啦。你們不要擔心,我自己有辦法應付的。」
我還能說什麼?他還能有什麼辦法?
小時候,他在客廳亂跑,又笑又叫。不小心撞到柱子。痛得瞬間靜音,馬上停下腳步。他想到院子裡找媽媽撒嬌。走沒三兩步,又走回剛剛撞到的地方。看一下,對著柱子說:「ㄟ,會痛耶。」
開門走出院子,厚實的門順風關上,很大聲。他馬上對門說:「對不起。」因為媽媽告訴他,關門不能太用力,門會痛。他一直就是這般乖巧貼心。
夏日的午後。培正剛和媽媽從社區內的游泳池回來。穿條泳褲,光著上身,手上拿著小游泳圈,邊走邊跳,隨性地亂轉小泳圈。社區內剛重新鋪好柏油路,新柏油在陽光下發亮,還有一些沒清理乾淨的給配小碎石子。
啪地一聲,培正突然踩到石子,腳步失穩,像滑壘般地全身俯衝,撲倒在地上。媽媽大吃一驚,還沒來得及反應。他已經坐起身,把雙手攤開在臉前,打量一番。發現雙手都破皮,手上黏著柏油和小石子,鮮血滲流著。他抬頭對媽媽說:
「媽媽,我受傷了。沒關係,回家擦藥就好了,對不對?」
母子牽手走在巷弄裡。雖然手很痛,他邊走邊仰頭對媽媽說:「媽媽,我很勇敢,摔倒不會哭。」「我很乖對不對?有聽媽媽的話。小孩子不要用哭的,用講的大人才知道小孩子發生什麼事。對不對?」他一直都是個能聽從我們教導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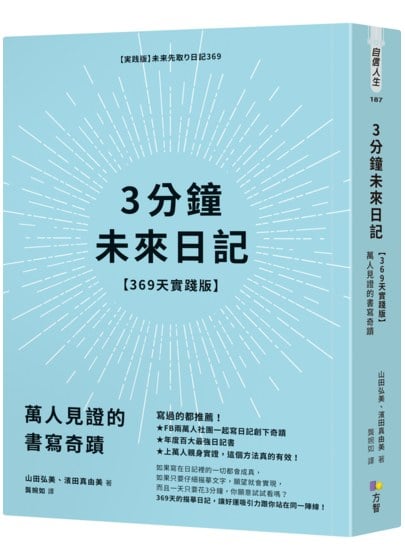






.png)
(1).jpg)